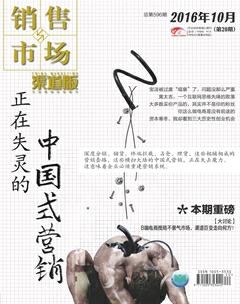向死而生,還是向生而生?
劉春雄
無論“向死而生”,還是“向生而生”,都是轉型時期的語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轉型思維,前提是都需要轉型。
“向死而生”的代表人物是海爾的CEO張瑞敏,“向生而生”的代表人物是學者兼管理者陳春花,兩個人都贏得了社會的掌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共鳴者。
我們很難說“向死而生”還是“向生而生”哪個更好,但兩套思路都有自己的一整套方法論,沿著任何一套邏輯都有可能成功。
向生而生
在施煒老師有關轉型的新書《重生》的序言中,陳春花老師詳盡地闡述了她稱之為“向生而生”的觀點:
“一是不要為轉型而轉型,要循序漸進地持續變革,盡量不要破釜沉舟,不要丟掉當前的市場和產品,始終要保證足夠的業績增長,只有存活才能成長;
“二是可以嘗試雙業務模式,維持現有業務的穩健經營,同時布局新業務,駕馭長期發展和短期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
“三是重視并建立多方位的信任關系,包括投資者的信任、員工的信任、客戶的信任和社會的信任,這在利益重構的轉型時期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到“向生而生”非常不易,因為這意味著變革和轉型要打“提前量”,不能等到“非轉不可”的時候再轉型,那個時候可能就不得不“向死而生”了。變革和轉型要打“提前量”,意味著必須要同時做好以下幾方面:
第一,有“以未來規劃現在”的超前視野。與多數人的戰略規劃是“以現在設計未來”相反,受德魯克影響的國內頂級管理專家,包括包政、陳春花老師等,都主張戰略是“以未來規劃現在”,“現在的積累構成未來”的戰略思想。那么,“未來是什么”就非常重要,這恰恰是這一輪戰略所難做到的。陳春花老師的思想中還是有不少傳統戰略的思想。
改革的最佳時機是什么時候?我認為是業務達到高峰的時候,這個時候擁有無限的改革資本。但是,誰能想到這個時候恰恰是最需要改革的呢?所以,一般企業是在業務走下坡路的時候才想到改革,或者被迫改革。
華為的任正非是個有超前預警能力的老板,比如像《華為的冬天》是在冬天并沒有到來的時候提出來的,等到冬天真的來了就已經晚了。所以,我認為華為的改革也是“向生而生”的思維。
第二,“雙業務模式”平穩過渡。所謂轉型的企業,不同于創業企業沒有包袱,轉型企業是有存量的,不可能置存量于不顧,所以就需要“雙業務模式”。我是同意陳春花老師這種觀點和做法的。一旦新業務模式取得了成功,傳統模式的轉型就不再是難題。
第三,置轉型于無形。轉型可以是革命,可以是變革,可以是改良,最終達到目的就行。好的轉型可以是無形的,不僅在業務模式上平穩過渡,在內部結構、人員調整上也可以是無形的。
所以,陳春花老師才說“投資者的信任、員工的信任、客戶的信任和社會的信任”非常重要。既然是轉型、改革,就必然涉及利益,就必然有掣肘,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或者對抽象的改革不反對,但對落實到具體措施上的改革是反對的。
當然,“向生而生”很難。陳春花老師以前在六和,這次在新希望,都是在踐行“向生而生”的轉型和變革。盡管它不那么高調,甚至還很低調,但這種轉型方式是震蕩最小、成本最低、成功率比較高的一種轉型和變革模式。
向死而生
有人說,中國歷史上幾十次改朝換代都成功了,但歷次改革卻以失敗居多。或者改革本身成功了,但改革者個人卻失敗了。于是有人說,改革比革命更難。
向死而生,就是革命式的改革。
向死而生,也有說是“自殺重生”,或者說“置之死地而后生”“先死后生”。只有過去的自己死掉,才有可能重生。
張瑞敏1984年上任時,面對的形勢就是“先死后生”,不是死到臨頭,誰會讓你改革。所以,那個時候的企業打上了“先死后生”的烙印。所以,我們看張瑞敏的改革思想,就是歷史印跡的。包括張瑞敏的語言體系,比如廣為傳播的“砸冰箱”事件,都可以看作對“先死后生”“破釜沉舟”思維的一種造勢。
這里要說明一下,“先死后生”與“向死而生”還是有所不同。“向死而生”同樣源于張瑞敏的超前思維。
“先死后生”,往往是傳統方式走不下去了,被迫變革。原來很多人是反對互聯網的,現在從心理上也是抵制的,但是,傳統的方式走不下去了,只有試試。其實,多數的變革可能就是這樣的。
“向死而生”則不同,是在經營情況很好的時候,預料到不改革就會出問題,而預先做出的改革,只不過做法上有點類似于“不成功,則成仁”的做法。
比如,張瑞敏這次的變革,“企業平臺化、員工創客化、用戶個性化”這三化主張,其實是建立在對信息時代的預測基礎上的,這樣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甚至未來是否真的如此還有極大的爭論。
但是,在張瑞敏的觀點里,“只有時代的企業,沒有成功的企業。”既然這個時代要來了,那就提前改變。所以,這也是有“提前量”的變革。
與“向生而生”不同,“向死而生”幾乎不留退路。特別在精簡1萬名左右的管理人員,“要么成為內部創客,要么離開企業”,這就是不留退路,真的“向死而生”。
當然,在具體措施上,也是要考慮存量的。以海爾內部的最小經營單元“小微”為例,海爾就有“創客小微”和“轉型小微”兩種。“創客小微”是全新的創業企業,是增量;“轉型小微”則是存量的轉型。
海爾的這套轉型,1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只不過決心沒有現在這么大。這套做法,在國內是有爭論的,在國際上也有專家評論很大膽的。或許,互聯網時代,到了中國向世界輸出管理的時候了。
“無人區”的生死“抓手”
無論是“向生而生”還是“向死而生”,其實隱含一句話:按老路走下去,死路一條。
整個工業文明時代,中國都是追趕者,前有路標。我們所要探索的是“中國式道路”。與宏觀上的“中國式”相比,微觀領域的“中國式”其實更少一點。
進入信息文明時代,中國突然走在世界前列,或者說并列在世界前列。按任正非的說法,我們進入了“無人區”,我們成了別人的“路標”。成為“路標”是有代價的,可能前面根本此路不通,或者死路一條。
此時,僅僅有“向死而生”的勇氣,或者有“向生而生”的理念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套“生的方法論”,這方面,我們太缺少思考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很欣賞任正非。他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發言,我認為很經典,我認為是“領先者的生存方法論”。
一是分布式的“多路徑、多梯次”戰略。任正非說:“內部對不確定性的研究、驗證,正實行多路徑、多梯級的進攻,密集彈藥,飽和攻擊。”
二是“藍軍戰略”。“藍軍”本來是檢驗“紅軍”的鏡子,但在“無人區”,“藍軍實體化”則成為華為一個重要戰略。
三是贊美“不完美的英雄”。“不以成敗論英雄,從失敗中提取成功的因子,總結,肯定,表揚,使探索持續不斷。對未來的探索本來就沒有‘失敗這個名詞,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
四是開放地從宇宙中吸收能量。“我們鼓勵我們幾十個能力中心的科學家、數萬專家與工程師加強交流,思想碰撞,一杯咖啡吸收別人的火花與能量,把戰略技術研討會變成一個‘羅馬廣場,一個開放的科技討論平臺,讓思想的火花燃成熊熊大火。”
變革方法論
互聯網時代的東西,爭論太多,難有定論。等到真的都弄明白了,或許機會也過去了。這個時代,需要新的變革方法論。以我的體會,有幾個關鍵點:
一是董事長與總經理分設。董事長與總經理,一個視角向外,一個視角向內。一個要引入新生力量,一個要負責穩健經營。固然有兼職做得很好的企業,但在變革時期,分設就很重要了。
二是要有長期穩定的“旁觀者”做顧問。“當局者迷”是常態,那么就需要清醒的“旁觀者”隨時提醒。我們很多企業需要的顧問,不過是企業有病時候的“大夫”。
三是要進入“新圈子”。一個圈子之所以成為圈子,就在于有很多相似性。進入“新圈子”就是要尋找差異性。在一個老圈子里,保守者可能更加保守,因為大家相互強化。
四是要有“自以為非”的心理。自信,往往表現為“自以為是”,是正向強化。對于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東西,不要本能地、想當然地拒絕,要深入進去了解。
五是要敢于嘗試。小規模地嘗試、局部地嘗試、不傷筋動骨地嘗試、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