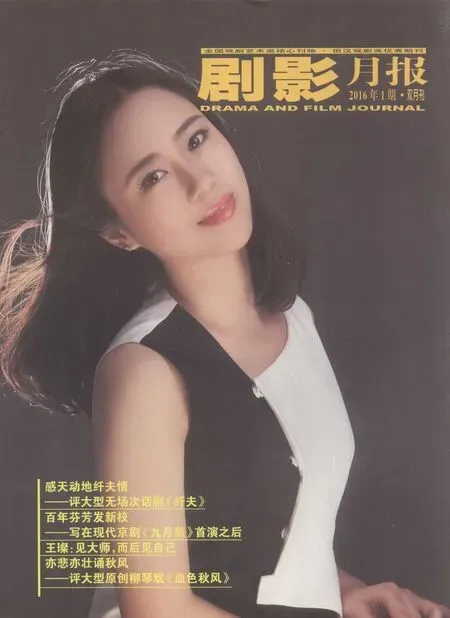長篇彈詞《描金鳳》的流派淵源
■夏夕燕
?
長篇彈詞《描金鳳》的流派淵源
■夏夕燕
長篇彈詞《描金鳳》最早又稱《錯姻緣》,分十二卷,四十六回。現(xiàn)存最早刻本為光緒二年(1876)重刻本及三十二年《馬如飛重譜時調》石印本。《描金鳳》說唱的是姑蘇書生徐惠蘭因家貧向叔父借貸,卻遭凌辱,憤而自盡,為江湖術士錢志節(jié)相救,并將其女錢玉翠相許。玉翠以家傳御賜描金鳳相贈,作為定情之物。惠蘭被姑母接去讀書,途中救了重病的書生金繼春,二人結為金蘭。惠蘭到河南后被冤下獄。臨刑前金繼春因與惠蘭貌相似,舍身替死,臨刑時被綠林好漢劫走。京中大旱,錢志節(jié)應詔求雨成功,得封高官,為惠蘭申冤,終于逮住真兇馬壽。冤情昭雪后,惠蘭應試,連中三元,授官與玉翠成婚。作品情節(jié)曲折,寫救人危難與真心相助,尤為感人。
光緒年間出版的《繡像描金鳳》卷首的一篇序言:“近年來彈詞歌曲,名作如林,舍湯臨川《四夢》傳奇之外,尚有范香令,袁籜庵諸名輩之作。流遍歌場,遂使青衣玉指,紅粉歌喉。當珠簾曉卷,綺席宵開,泛畫舫,抱銀筆,悅目娛情,唱彈不絕,然總不外乎旖旎風情,表出一段溫柔佳話,曾無忠孝節(jié)義中流傳音律,以鼓人情與志者也!獨《描金鳳》一書,節(jié)可歌,義可采,譜諸紫簫紅笛,固雅調琤琤,不啻霓裳一曲;而列諸黃卷青燈,亦復聲情侃侃,宛同荇菜一章。宜乎吟館詞魁,歌樓姹女,體味不置。余也情癡詞曲,覽是舊卷,而神情為之移。節(jié)短拍長腔,若欲博周郎之顧,遺誤不無。爰偕知音韻士,按節(jié)調弦,宮商合度,以付棗梨。想此后選曲亭中,更添鼓吹,歌喉新囀,是必有竊驚月中得來者矣!”
民國時期出的《彈詞畫報》第三十七號百批《書壇小常識》十六《五毒書》中這樣寫道:“昆曲中有‘五毒戲’,其實就是不容易唱做的重頭戲;各行各色,都有唱做繁重的‘五毒戲’。……彈詞中也有‘五毒書’,都是很不容易說唱。據我所知,那部夏荷生一唱而紅的《描金鳳》,的確是‘五毒書’。因為書中角色很多,而且都不容易起得相像,那個汪宣,原籍安徽,久居蘇州,開出口來,不倫不類,既不像徽州口音,又帶些蘇州土語,他們道眾叫做‘徽夾蘇’,那種不純粹的的徽蘇白,倒很難說,無非引人發(fā)笑而已。以前要推趙筱卿說得最流利動聽,自他死了以后,擅說‘徽夾蘇’的彈詞家,可說絕無僅有。夏荷生還可敷衍,可是并不算好;其他如錢篤笤、陳榮、董武昌、許賣婆等角色,也都難起的;在劫法場中,不要會說各地方言,每一個角色出場,都要念引子,唱的調門又很多;這不是比別的彈詞,更不容易說唱嗎?所以彈詞家說這部《描金鳳》的,便稱之謂‘五毒書’”。
蘇州彈詞最早說唱《描金鳳》是清代咸豐、同治年間的評彈后四家之一的趙湘洲。相傳他的《描金鳳》曾得到馬如飛的幫助,提高了藝術性,因而成為彈詞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書目,一直流傳至今。趙湘洲說書起初“板滯無生趣”,后收徐湘濤為徒,徐本為唱昆曲的藝人,將昆曲中的表演程式吸收到彈詞中,說書有生、旦、凈、丑之分,增強了說書的生趣,名震書壇。趙湘洲天生一副好嗓子,擅唱俞調,弦子彈得也很好。馬如飛在《雜錄》中寫道:“今吾輩中,弦子惟趙公首領。”
趙家《描金鳳》既傳子也傳徒,繁衍甚眾。趙湘洲的兒子趙鶴卿,孫子趙筱卿都是書藝高超,十分有名。特別是趙筱卿二十歲就成名,他說書既有剛勁,又有輕柔,是清末民初彈詞“三卿黨”之一。擅說“鄉(xiāng)談”,如汪宣的徽白,董武昌的山西話,說啥像啥,被人稱為“巧嘴小金鳳”。后來與其徒楊斌奎拼檔演出十多年,說遍江浙滬,均得佳譽。趙筱卿后與其子趙鶴蓀拼檔,趙鶴蓀的喉嚨清脆,琵琶技藝精湛,相得益彰,因此藝名更盛。可惜后來趙筱卿染上吸毒的惡習,糟蹋了身體,只活了四十多歲。他的弟子中以楊斌奎最負藝名。
傳趙筱卿衣缽者,首推楊斌奎及其子楊振雄、楊振言。楊斌奎說表條理清楚,口齒清晰,腳色生動,繪景狀物,甚為細膩,擅唱書調,質樸無華,不瘟不火。楊正雄九歲隨父上臺“插邊花”,出道后說唱長篇彈詞《描金鳳》。他在俞調的基礎上吸收的夏調和昆曲唱腔,發(fā)展成為了他的楊調流派唱腔。楊調響彈響唱,快彈慢唱,大小嗓交替,長短腔并用,高腔與低調相結合,演唱起來節(jié)奏自由,有強烈的抑揚頓挫;唱腔中感情變化豐富,有剛勁、雄渾、粗獷、挺拔的一面,也有委婉、柔和、悲切、哀怨的一面,深受聽眾喜愛。趙家《描金鳳》入室弟子中第二代的錢玉卿,第三代的錢幼卿、金桂庭、吳西庚與張步蟾、張步云昆仲等均蜚聲書壇,極一時之盛。而錢幼卿的弟子,第四代夏荷生更是登峰造極,無出其右。
提到夏荷生,評彈界誰人不知哪個不曉。他是上世紀30年代紅的山崩地裂的彈詞前輩。其父在嘉善城廂鎮(zhèn)開設夏廳書場,他自幼聆及各家演出,深受熏陶。14歲到上海商務印刷廠當排字工,因工傷回家。夏家的廳堂曾開設書場,使他從小就受到評彈藝術的熏陶。在養(yǎng)病時,隨伯父夏吟濤學說《倭袍》。16歲拜擅說《描金鳳》的名家錢幼卿為師,學習評彈藝術。秉性聰明,又有一副天賦的好嗓子,從師后虛心求學,不僅得到老師的真?zhèn)鳎€能吸取各家之長,唱腔吸收張步云的小陽調,以及俞調、馬調的特點;表演吸收王斌泉的特長,終于形成自己獨特的表現(xiàn)風格。夏荷生先后學唱過《三笑》《描金鳳》《雙金錠》三部長篇,以鉆研《描金鳳》一書功力最深。學習《描金鳳》時曾經與師拼檔數年。拆檔后,一度退出光裕社,加入上海潤余社,單檔奏藝于江浙城鄉(xiāng)。20年代初,某次蘇州會書,因說《描金鳳·俊巧戲主》一回一鳴驚人,聲譽日增,與王斌泉、陳瑞麟合稱“碼頭三巨頭”。1925年,初次到上海老城隍廟東方書場演出,說唱時大小嗓運用自如,高亢處有穿云裂帛之勢,細微處卻又如泣如訴,令人回腸蕩氣,贏得“金嗓子”的美稱,書場連日爆滿。各大書場、電臺、堂會競相邀請,一時名聲大振。
1929年,夏荷生參加蘇州評彈會書,說《描金鳳》中“汪宣上吊”一回,由于說表層次分明、嗓音高低相濟、遣詞用語得當、唱腔蒼勁纏綿而又飄逸,震懾了全場聽眾,并一再要求其說下去。從此夏調蜚聲蘇州和整個評彈界,被譽為江南“描王”,紅遍江、浙、滬地區(qū),成為評彈界一顆巨星。他說功火爆,精氣神尤為充沛,邊說邊演。所起生旦凈丑諸角,均能抓住特征,模擬角色之音容笑貌,惟妙惟肖。角色轉換靈活、深入。運用一頂瓜皮小帽,推前挪后,可現(xiàn)出多種角色。嗓音鏗鏘高亢,挺拔清亮,真假嗓結合,響彈響唱,節(jié)奏感特強,且頓挫顯著,高低強弱聲對比極為鮮明,富有表現(xiàn)力,世稱夏調。其唱腔脫胎于早期書調,與說表銜接緊密,說唱性較強,徐疾、長短、頓歇,服從于語言的表達,自由靈活。由于音域高,上半句都用假嗓,下半句轉用真嗓,轉換自然,對比鮮明。其真嗓力度和音高又與假嗓接近,唱腔更以遒勁挺拔,高亢激越為特點,對聽眾很能起抓神、提神的作用。落調處,底氣充足,余音不絕。代表住曲目有《描金鳳·汪宣扮假死人》、《換監(jiān)托三樁》等。張鑒庭、楊振雄、凌文君等早年放單檔時都唱夏調。后來,楊調、張調的形成也受到夏調一定影響。
由于演出繁重,經常咳血,每上臺演出必先吸食鴉片提神,日久成癮,有一次他彈唱得意唱段《描金鳳·托三樁》正想高翻,來個“海底翻”時嗓子開了花,聽眾給了個哄堂倒彩。他決心摒棄這種“上海生活方式”回到故鄉(xiāng)浙江嘉善休養(yǎng)。可沒幾年又被書場老板爭著拉回上海,又日夜趕場子,身體就更壞了。30年代有一位富商極為欣賞他的書藝,夏天請他到廬山避暑,名義是叫他唱長堂會,其實是助他戒除毒癮。說書藝人上廬山,當時乃一大盛事。報紙一登夏荷生知名度更高了,秋后回滬場東都來邀請,唱得太多,精神又搭不夠了,為擠出更多說唱時間,他把鴉片改為了白面,打了“海洛因”針,一天到晚處于興奮狀態(tài)。當他決心戒除毒癮時,肺病已經到了晚期,一病不起。1946年秋,一代“描王”因病逝世,享年48歲,他一身絕技,和高亢挺拔、一波三折的夏調唱腔,徒輩和當時彈詞界中,無一人接得上去。
夏荷生的弟子徐天翔1936年從師學唱《描金鳳》。曾與楊德麟拼檔。1956年至1957年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說唱團工作,1959年加入浙江曲藝隊(今浙江曲藝團),為該團創(chuàng)建人之一。除說唱《描金鳳》外,50?年代以后,還有長篇《白毛女》《寶蓮燈》《血碑記》等。他根據蔣調、薛調以及京劇的某些腔調,形成較為昂揚、明朗,較具時代氣息的唱腔,人稱翔調。擅唱九轉三環(huán)調,并將它融會于翔調的某些唱段之中。代表作有《東海女英雄·乘風破浪》、《描金鳳·董賽金策馬下山坳》〔三環(huán)調〕等。
我的太先生凌文君,師從朱琴香學說《描金鳳》,他出道很早,十七八歲就在上海的好幾家商業(yè)電臺上唱開篇,有時也說上一段折子書,博得聽眾好評。30年代在藝術上私淑“描王”夏荷生,因其嗓音瀏亮,有“江南小鐵嗓”之譽。再加長相脫俗,有股銳氣和秀氣,難免應酬也多了起來。就在那種春風得意、馬不停蹄的情況下,勞累了身體。不過,即使這樣他也沒有忘記要在藝術上繼續(xù)追求,他的書藝還是日見成熟。早年響彈響唱,1948年倒嗓后,改為真嗓為主,假嗓為輔。唱腔為夏調和自由調的合諧結合,飄逸明快。道中都知道,沒有天賦,要學夏荷生,門檻也踏不進。所以夏荷生自己沒有收過像模像樣的學生。倒是橫戳槍,弄來個私淑弟子。凌文君聰明人,自知本錢其實也不多,除了喉嚨喊得出,其他方面,功底欠缺,他于是廢寢忘食,刻苦鉆研。他說,學夏荷生的手面、表情,照式照樣搬得來,學不像;要學,學他如何觀察社會、觀察人物,如何體會,如何吸收,做到神似而不是形似,這樣,聽眾才會說凌文君有點像了。
我的恩師余瑞君從小因家庭開設書場(在臨頓路“九如書場”)而喜歡評彈藝術。1948年拜“小描王”凌文君學說《描金鳳》和《雙金錠》,先與師父拼師徒檔,隨后和湯秋君合作彈唱《描金鳳》。1950年參加蘇州評彈協(xié)會,1951年5月參加市文聯(lián)舉行的講習班并和曹嘯君合作創(chuàng)作新編抗美援朝的故事《母子英雄》,在新藝劇場演出獲甲等獎狀。1951年他和莊振華結婚并一起參加新評彈實驗工作團,余莊檔成為第一批入團的評彈演員。
余瑞君先生從藝五十余年,深得師祖凌文君的藝術精髓,他和莊振華合作演出的長篇彈詞《描金鳳》,夫唱婦隨,珠聯(lián)璧合,紅遍江浙滬,為廣大聽眾所喜愛。余瑞君先生在五十多年的藝術實踐中把《描金鳳》一書作了比較新穎的改革,就是抓住主線,以錢篤笤和汪宣兩個主要人物的恩恩怨怨展開書情,掛牌的書目干脆叫《錢篤笤與汪宣》,和其師其祖凌文君、夏荷生等的海派風格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說書更加顯得有蘇味和正宗感。他的說表風格自然親切、輕松質撲,非常有感染力,令聽眾和他一起融會在書情人物之中。先生說、噱、彈、唱俱佳,他的徽夾蘇堪稱一絕,人稱“活汪宣”。他以詼諧輕松的祥調來塑造玩世不恭的老江湖錢篤笤形象,一段余瑞君風格的朱耀祥調,在配以師母莊振華的“趙稼秋式”的琵琶伴奏,烘云托月,給聽眾留下深刻印象。先生為培養(yǎng)評彈事業(yè)接班人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收了蘇州評彈團、江蘇省評彈團、上海評彈團、上海東方評彈團、上海新藝評彈團等青年演員為徒傳授技藝。余瑞君先生熱愛評彈事業(yè),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評彈藝術。
綜上所述,長篇彈詞《描金鳳》代代相傳,名家輩出,流派眾多。從趙湘洲開始,傳趙鶴卿,傳張步蟾,傳張子祥,傳朱琴香,傳凌文君,傳余瑞君,傳到筆者已整整八代了。前輩藝術家為我們留下如此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隨著物質文明的發(fā)展,聽眾對文化、精神食糧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提高,歷史發(fā)展到今天,長篇彈詞《描金鳳》如何傳承?如何繼續(xù)在優(yōu)秀傳統(tǒng)書目中爭妍斗艷?如何在書中內容不失去理性的同時更加貼近現(xiàn)代?如何讓傳統(tǒng)書目與時俱進?這些都是我今后從藝生涯的奮斗目標,為此我將不斷努力,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