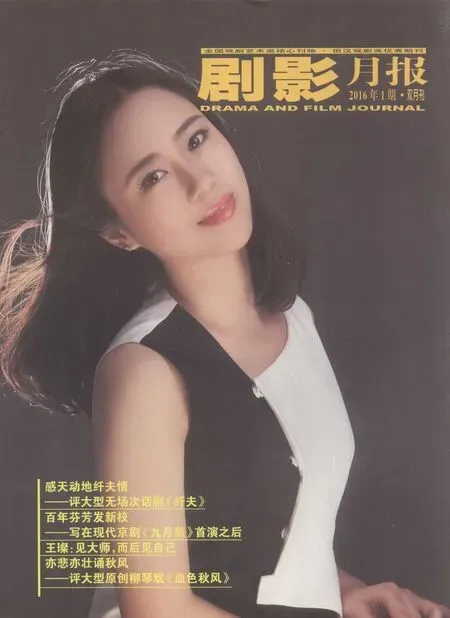二胡教學中的審美體驗
■唐飛飛
?
二胡教學中的審美體驗
■唐飛飛
中,我多半選以《二泉映月》《光明行》《賽馬》《江河水》等精品曲目為題通過示范性的演奏,偏于在技術層面上運弓、換把、揉弦等技術把握的闡述,想借此喚起學琴者持恒苦練奮力追尋的求藝興趣,最終達到運弓平穩、換弓連貫、揉弦滑潤自如的理想境地,僅此一點,使我體會到良好的素質體現,必須要有扎實的功底基礎作鋪墊,而技藝的純熟,方會讓你從艱辛的歷練中盡享二胡之美的無窮魅力。
在后期的淮胡教學中,我側重又換以啟示性的方式,采用跨界中淮劇固有不同特性曲牌、流派唱腔作對比,把學生注意力引入到注重戲曲聲腔內在音樂的美與實在情感表達的雙重體驗上,幫助學生樹立二胡的藝術表達,需是“藝術”、“美學”、“技巧”三者兼得的創新理念。
應該說,戲曲藝術包括它音樂聲腔,伴奏所潛藏著的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只有當你走近它去探求、去發現,你方會從對其美態有所新的識知后,獲得一次自我生命中真正意義上的審美。
近些年來,我幾度曾應邀參加了江蘇省淮劇團與鹽城市淮劇團《小鎮》《菜籽花開》等劇的樂隊伴奏工作,與其說是在操琴,不如說是在學習。劇中那諸多精美的唱段樂思的流暢,旋律之華美以及沿于對本土音樂元素的運用,突顯著一種濃郁而獨特的田野情趣,宛如一幅生動而靈秀的農家生態優美畫卷讓我心醉。由此,我手中二胡的律動,便也隨著平實的音樂語言和對劇中人物情感的體味,變得更加地舒展和輕柔,而此時二胡的美感也就自然而生。
帶著這種感悟,我也曾不時地親領學生走出課堂,邁向劇場樂池,實地的去體驗戲曲樂隊的演出狀態,感受二胡在戲曲樂隊中的作用與其所表現的音樂色彩。這樣,似乎便能較好地調動起學生的靈感,為他們今后的演奏生涯創造更多想象、發展的藝術空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品位二胡,亦即品味我的藝術人生。因二胡琴音之絕美,使我永不言棄地追求二胡藝術三十多年,回望這三十多年的學與教,我有著如下深切地體會:
一、演奏者要有感受美的悟性
以戲曲為例,淮劇,是一個充分顯示江蘇豐富的民間音樂語言和具有鮮明地域風格的地方戲曲劇種,其音樂唱腔無不獨有著高亢、粗獷、凄美、質樸的特點,而聲腔美的全部藝術價值,盡皆體現在它的“通俗性”和“人民性”上,倘若你非是抱著鄙視的眼光去看待它的粗放,那你便會以不一樣的情感讀懂它聲腔的純樸與醇厚,感受到它情韻的獨特,從而用你那高超的琴藝,再現淮劇音樂聲腔的悲涼與激越。
二、演奏者要有表現美的技巧
技巧是藝術呈現的基礎。通常關乎二胡音色的對比、音響的平衡、力度的強弱,全依賴于演奏者的運弓、觸弦是否適度的掌握之中,淮劇淮胡主奏大家潘鳳嶺、居樂之所以被人譽為淮劇“南潘北居”之琴王,就在于他們能熟練掌握淮劇各種板式、流派的唱腔規律與特點,擅于透過他們那用指肚拍打式按弦和無飄浮感的揉滑音勢,傳遞出一種溫柔、抒情,且又很有彈性和力度的琴音,給人以純然淮劇風味的聯想。由此不難想象,當你打開弓弦盡展你操琴技能時,那琴筒里所迸發出的每一個音符,都會沉浸在最美的旋線里,賦予給人們以最為精彩,最為快感的音樂享受。
三、演奏者要有鑒賞美的本領
從藝術層面來審視淮劇,它具有多種色彩性的聲腔曲牌和多樣個性化的流派唱腔,所有這些,皆是要通過多渠道的再創造來展現其藝術之美。諸如淮劇曲牌中的【淮調】豪放剛勁,那二胡的襯奏則多可用頓挫有致、強勁有力的短弓,以求與聲腔的粗獷之氣相吻貼;淮劇曲牌中的【拉調】纏綿俏麗,那二胡的托腔則可另以連弓、長弓為主,并輔以較多的揉滑技巧,突出其聲腔的華美與輕柔;淮劇曲牌中的【自由調】舒展明快,因而二胡的鋪墊自然便隨之換以中弓或快弓,以強化音色的清亮和旋律的流暢。
除此,再以淮劇流派聲腔為例,李派(李少林)的唱,蒼勁樸實,充斥厚重的老“淮味”,這就要求二胡的伴奏力戒漂浮而要渾然穩健;陳派(陳德林)的唱,舒雅灑脫,常把美的旋律,藏夾在頓挫音、倚音、滑音等各種行腔潤色之中,這便驅使二胡須采以“曲線多于直線”等各種技法的修飾,助推起演唱更加流暢、委婉、自然與平和;同樣,像裔小萍的“裔腔”,陳澄的“澄腔”,一是深沉細膩、圓潤柔美,一是華彩婉轉,韻味醇厚,同有淮劇唱腔經典范式之美。故而此時二胡的伴奏,必在“托腔保調”的前提下,做到“弓隨腔走”。“指隨腔行”,力盡用最大表現力的演奏技巧和最富感情色彩的完美音色,去托起淮劇聲腔的華彩與瑰麗。
四、演奏者要有創造美的能力
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戲曲二胡伴奏的教學上,試行以示范性和啟示性相結合的方式,作為自己相對穩定的教學特點與教學風格的定向,一周十八節課的流程全部用在如何順應演員的演唱,強化搞好二胡“托”、“裹”的跟腔伴奏。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教學內容的擴充,我也在不斷地探索著教學風格的創新,除了堅持演奏方法、手指技能、樂感、音樂表現的課程外,也在適度的增加審美情趣和對戲曲經典唱段解讀能力的培訓。
盡所皆知,戲曲音樂中的唱腔和伴奏均帶有濃重的社會性和傾向性,也就是說,二胡作品的寫作或伴奏皆無法避開劇種音樂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屬性。可是,在堅守劇種音樂本體最核心的韻味不變的前提下,能否在伴奏的處理上作相應地改變或調飾呢?我想,應該可以,也是必需的。仍以我接觸最多的淮劇為例,其淮胡紅木圓筒的塑制和介于1=B-D之間的調高,決定了其音色、音量、音質遠不同于民二胡,也不及京胡的“亮”和“脆”,而是以剛勁、寬厚展現其音樂的氣質和韻味的美。然則在這優長的背后,隱約可見,演奏者的拉奏,似乎多半停留在有限的兩個八度之內的律動,且呈有一定程度即興演奏成分,這樣,勢必缺少音響的靈動與開闊,據此,我們何不可以借助一些次下把位及弦上動作的練習,加強其手指音位的靈活應變,從而通過手指及臂重在弦體上的變化能力,達到增強其音樂表現上的抒情性。再說,淮劇唱腔旋律的構成,多有華彩性的柔板及“垛句”(亦即“疊腔”、“連環”)的結構形態,而眼下二胡偏重平拉的奏法,顯然又是缺少推力和活力。正是有了這種感悟,我在以感情為主線的表演性練習教學中,竭力推崇二胡演奏家閔惠芬所倡導的“二胡演奏聲腔化”的理念,啟示學生在實際體察淮劇聲腔腔韻形態的過程中,多作一些諸如跳弓、拋弓、斷弓以及顫指、揉弦等帶有高難度技巧的腔韻動作訓練,就這樣,不一樣的琴感和弦感,產生起不一樣的樂感和美感,進而使淮劇二胡的伴奏,變得更加細膩傳神,表現深刻。
面對當今音樂藝術高速發展的態勢,我心一片欣然,自覺二胡是一種精神的情感,因二胡而快樂。在長期的藝術教育中,我無時不在告誡自己和啟示我的學生,選擇習練二胡,不只是學一些技巧,更重要的是修煉自己的品質。作為一個用二胡說話的演奏者,不獨在藝術生活中展現自我,更要帶著美的琴音去感染你身邊的所有人。
二胡是屹立于中國民族藝術之林且具有鮮明民族風格和特色的一件普受歡迎的樂器,關注和重視它的發展,無疑是傳承和發展民族優秀音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酷愛二胡,并獻身二胡,愿在藝術教育這方天地里,繼續堅持長時間的藝術修煉,長時間的人格磨礪,以良好的心理素質負起教書育人的重任,用手中看似平凡的兩根琴弦,放手高奏,抒發當今時代人們那最美好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