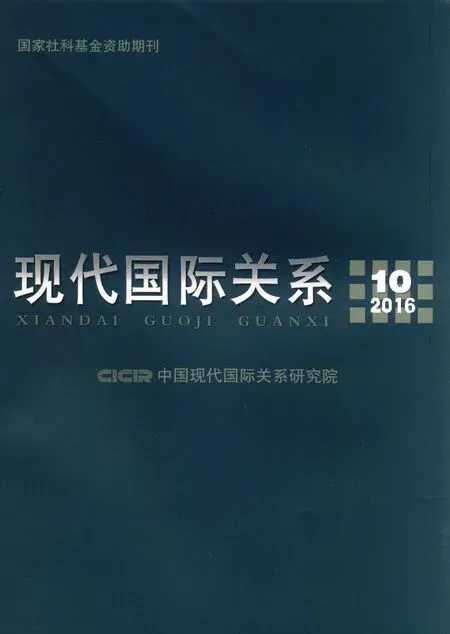全球大變局與世界新秩序
袁鵬
全球大變局與世界新秩序
袁鵬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化,舊的世界秩序破損,新的秩序則尚未建成。圍繞著未來世界新秩序的構建,世界各主要力量既有自己的盤算,也都面臨著各自不同的問題與困難。崛起的中國在國際影響力上升的同時,經濟減速的風險也客觀存在。基于歷史傳統與基本國情,中國對世界秩序、世界體系有自己的看法。新秩序的構建需要各國通力合作。
世界政治世界秩序美國中國外交
[作者介紹]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主要研究中美關系、中國外交戰略。
一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不管承不承認,這個世界已經變了。只是這種變化不是靠世界性戰爭實現的,而是一種改良式、漸進式、“溫水煮蛙式”的變化,在量變和質變之間甚至看不出明顯的界線。但是,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新的時代、新的世界。回溯過去,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一戰后華盛頓-凡爾賽體系以至二戰后雅爾塔體系,再到冷戰后漫長的過渡式“后后冷戰時代”,我們今天正面臨第四次歷史性變遷,我們正面對新的世界體系重構,正所謂近400年未有之變局!
前三次歷史性巨變都同世界性戰爭(熱戰或冷戰)直接相關,因此體系之坍塌或構建都是疾風驟雨、大開大闔式的,基本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我們正身處其中的這新一輪秩序之變,則既與一系列局部性戰爭(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地區性沖突(如朝核危機、伊朗核危機、烏克蘭危機、東海南海摩擦)相關,也同國際力量格局的自然變動攸關——所謂新興力量群體性崛起、西方世界整體性低迷、非國家行為體呼風喚雨、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等等,從不同側面沖擊既有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而更為根本的,則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威脅多元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時并存于世界,它們相互激蕩、互為因果、連鎖反應、推波助瀾,你方唱罷我登場,東邊日出西邊雨,剪不斷理還亂。對執政者來說,面臨的任務千頭萬緒,“機遇和挑戰均前所未有”,縱然使出百般武藝精忠報國,最終白了少年頭,也未必招人待見。對普通民眾來說,面對一天一變的網絡資訊和難以適應的氣候變化,面對日新月異的國事家事天下事,常常感嘆“時間都去哪兒了”?
而對善于冷眼看世界的戰略思想家而言,這個時代給他們思考、寫作提供了絕佳的素材。于是乎,一批高質量、有深度的作品接連問世,法國人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美國人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英國人克拉克的《夢游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戰爭》、臺灣學者朱云漢的《高思在云》等等,從歷史的縱深、政治經濟的結合部、人類政治的發展前景等多角度拷問我們的時代、探尋未來的秩序。然而,他們提出的問題比給出的答案多,他們的困惑似乎比蕓蕓眾生還更多幾分。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年屆90的基辛格博士依然活躍在國際舞臺,敏于思考,勤于著述,善于溝通,指點迷津。他的《世界秩序》一書悄然面世,似乎是一個閱盡世間滄桑的老人在告誡世人,我們所處的世界秩序真的已經變了,而我們卻都沒有做好重塑新秩序的準備。舊的秩序破損、瀕臨坍塌,新的秩序將建未建,還有什么比這更危險的事實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各國都忙于自己家里的一畝三分地兒而無暇靜下心來重振地球村這個共同的家園,則世界表面的經濟繁盛和技術進步到頭來恐怕只會帶來更具毀滅性的后果。
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重大歷史性時刻,各國都積極籌備、隆重紀念,紅場閱兵、天安門廣場閱兵、聯合國大會……人們似乎期待以這樣一個歷史節點為分水嶺,總結過去、正視現在、面向未來,內心其實都在呼喚一個更加與時俱進同時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來。然而,誰將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領者或締造者呢?
二
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同時也是既有世界體系的主要締造者,美國自然希望繼續主導這個世界。奧巴馬無論怎么“謙遜”,在繼續領導世界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來都不含糊,他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問題不在于美國是否繼續領導世界,而在于如何領導”,“美國決不當老二!”“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不管如何包裝,內核都是“實力”,美國追求的永遠都是實力至上,目標則是繼續領導世界100年。
問題是,世界已不是過去那個世界,美國也不是昨天那個美國。就軍事實力而論,美國仍占據絕對優勢,相較逐漸老化的俄羅斯軍力,美國的軍事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比冷戰時期更勝一籌。其他如科技力、網絡力、戰略力、文化力、情報力、同盟力、智慧力、地緣力等等,仍令他國難望其項背,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仍是“唯一超級大國”。但從經濟實力角度看,美國的絕對領先優勢至少面臨來自歐洲和中國的挑戰。就單個國家而言,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10.2萬億美元,離美國17.4萬億美元雖差距仍大,但全世界超10萬億美元GDP的畢竟不再只美國一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評價論,甚至認為中國經濟總量(17.6萬億美元)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17.4萬億美元)。①“China Surpasses US as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ased on Key Measure”,https://www.rt.com/business/194264-china-surpass-usgdp.(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9日)而更多的國際觀察者們認為,中國經濟超美只是時間問題。從政治和社會兩個維度看,美國面臨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內部問題,政治“極化”、“碎片化”和社會“分化”愈演愈烈,以至曾經高呼“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寫下《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公開表達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失望和無奈。制度優勢和社會活力一直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軟實力,也是其能夠對外行霸權的國內基礎,從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桑德斯現象”看,這個基礎正在出現麻煩,“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奧巴馬的對外政策屢遭批評或掣肘,絕非偶然,而他在應對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伊拉克危機、“伊斯蘭國”等等問題上的作為不力,實在是因為他不想管、不敢管也管不了。畢竟,2008年金融危機后被推上臺的奧巴馬,當務之急是經濟、經濟、經濟!結果,美國的經濟終于走出危機,再次步入復蘇增長軌道,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卻在無情下滑。在這種情況下,靠美國單極維持世界秩序的穩定,顯然不切實際,美國少數人仍在做著“美利堅帝國”的迷夢,但多數人對美國實力的限度是心知肚明的。
歐盟能否構成世界的另外一極姑且不論,但其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現代化水平程度最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最強的力量組合,是維護世界秩序穩定或重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習近平主席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訪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傳遞出一個非常鮮明的信號,那就是中國認同歐盟作為世界政治一極、文明一極的獨特分量,也希望通過深化中歐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秩序的穩定。然而,自冷戰結束后,“歐盟往何處去”就一直困擾著歐洲各國領導人,美國人所形容的“經濟巨人、政治矮子、軍事侏儒”狀況雖有所改觀,歐洲人在敘利亞、利比亞沖突中甚至沖鋒陷陣跑在美國人前面,但是,總體而言,歐盟要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還面臨不少困難。高福利制度和外來移民增多帶來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下的經濟復興問題,烏克蘭危機折射出的戰略安全困境,等等,顯示“后現代”的歐洲也免不了“戰爭與和平”、“發展與復興”等“現代國家”習以為常的那些煩心事兒。近兩年,歐洲驟然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和中東難民的集散地,更凸顯歐洲未來方向的不確定性。總之,歐盟作為國際政治事務中的整體性力量,如何整合實力、找準定位、明確方向,是個大問題。否則,歐盟主要大國只能各懷心腹事,勁有時并不往一處使。德國最具實力,但默克爾很有分寸感,不愿挑頭;法國有意在國際舞臺上一展身手,但作用有限;老牌帝國英國則如美國著名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所言,“正在放棄全球大國身份”,一場誰也不在意的“脫歐”公投竟然出人意料地弄假成真,讓人對“大”英帝國是否從此變成“小”不列顛開始認真思考。歐洲大國如此,中小國家能做何指望呢?
另一個堪稱一極的大國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最具爭議。中國人和美國、歐洲人在如何看俄羅斯這個問題上觀點就大相徑庭。中國人更多看到的,是俄羅斯廣袤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強大的軍力、厚重的文化,以及充滿魄力和魅力的普京,因此往往對俄羅斯高看一眼,一直將它視為另一個世界級大國而倍加重視。這背后,恐怕多少同中國與沙俄之間的歷史積怨、與蘇聯之間的恩怨情仇等歷史記憶有關,畢竟,中國曾是受害者、受傷者或弱者,因此容易放大對俄羅斯實力的認識。美國人看待俄羅斯,則完全是一種勝利者的心態。問起華盛頓的戰略界人士,十之八九會說“俄羅斯不會有什么用了”。一些學者甚至覺得,冷戰后的美國歷任總統總在試圖從羞辱俄羅斯的過程中享受某種快感。美國朝野彌漫的這種“俄羅斯不行論”其實蘊藏著巨大的危險。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鏡中的俄羅斯從來就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平庸者。在成功化解古巴導彈危機后,肯尼迪曾經心有余悸地告誡后任美國領導人:“核大國在捍衛自身利益時,應避免出現讓對手必須在恥辱的退讓與核戰爭間做選擇的情形。”不管怎樣,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使面臨巨大難關,俄羅斯畢竟是世界政治中誰也不能小覷的戰略性力量,更何況,俄羅斯擁有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能源、國土規模等天然優勢。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共同締造者之一,俄羅斯對當今及未來世界秩序有一套全面的看法和闡述,需要人們認真審讀和仔細聆聽。
在世界大國俱樂部里,不應忘記的還有印度、日本和巴西。三國雖各具特色,但在期待成為被人尊重的世界級大國方面則同氣相求,聯手“爭常”即是重要標志。但畢竟,印度崛起的光芒不如中國閃亮,目前合縱連橫多意在經濟發展,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缺乏必需的意愿和能力;日本安倍政權雖無日不在“俯瞰地球儀”,但志大才疏、心胸狹隘、缺乏擔當,在美國的羽翼下尚難稱得上一支完全獨立的戰略性力量;巴西雖不甘偏安南美,但與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帶相距遙遠,且自身面臨嚴重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世界杯、奧運會的光環掩蓋不了巴西深層的矛盾,巴西的再度崛起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三
相較于歐、俄、印、日、巴等諸強,中國的優勢是明顯的。不僅經濟發展態勢最好,而且政治社會總體穩定,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堅持正確的戰略選擇,中國不僅實力迅速崛起,而且國際影響力日盛一日。正因如此,中國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視為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下一個超級大國。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它標志著中國人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步伐。這是繼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之后又一標志性事件。除日本之外的幾乎所有美國重要盟國都積極參與其中,這似乎印證了一個饒具諷刺意味的新現實,那就是,美國的經濟在復蘇,國際影響卻在下降;中國的經濟在減速,但國際影響力卻在上升。綜合評估,國際力量對比中升美降的總趨勢沒有改變。
然而,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集中體現在所謂“老二綜合癥”。盡管中國只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列第二,但國際社會傾向于中國在綜合國力方面也是“老二”,于是中國終于“被老二”了。問題是,這個“老二”與“老三”、“老四”、“老五”的差距沒有實質性拉開,卻與“老大”的差距依然巨大;既要面臨來自“老大”的擠壓,也要適應來自“老三”之后諸強的羨慕嫉妒恨;既要繼續跨越新興大國崛起進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與既成大國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防范在中亞、西亞、北非一度上演的“顏色革命陷阱”,還要處理一系列國內、周邊問題交織混雜的“成長中的煩惱”。習近平主席講,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越接近走向光明的時候,面臨的問題、困難、風險、挑戰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始終強調自己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而不會成為顛覆者。
但是,在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亞投行”、“一帶一路”、東海南海強勢維權……凡此顯示,中國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既有國際和地區秩序,在表面維護既有體系的同時打自己的小算盤,搞自己的小體系。同樣,在中國部分學者眼里,美國無節制無原則地偏袒日本、菲律賓,公然插手東海南海爭端,濫用“量化寬松”和貿易保護主義等等,也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顛覆自己一手打造的戰后國際秩序。于是乎,中美關系走到今天,秩序之爭越來越成為凌駕一切之上的核心問題。不止如此,世界各主要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修復、改革世界秩序。
四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什么是世界秩序?
對于各國的決策者、執政者而言,所謂世界秩序、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國際體系等等,無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勢的另類表述,而不太在意這些概念之間的微言大義,更多是一種不求甚解、大而化之。對于學者或研究者而言,上述概念的區分不僅意義重大,而且直接影響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看法,為此往往不遺余力,甚至皓首窮經。①近期閻學通教授對此作了專門且系統的研究,有助于人們對包括世界秩序在內的相關概念的學理性把握。參見閻學通:“無序體系中的國際秩序”,《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1期。
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傾向于基辛格的態度,既有一定學理闡述,又不過多糾纏于概念本身。在他看來,世界秩序其實更多是一種理念、一種構想、一種愿景,與既有的國際秩序不盡一致。理由很簡單,因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并沒有存在過。②參見[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序言。我們今天絕大多數的國際政治學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現代國際體系的起點,主要原因在于它確立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本準則,比如,主權獨立、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這些準則雖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過,但并沒有像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那樣被明確地規范,進而具有超越區域而成為所謂的普適性的準則。但從歷史的大視野去看,一方面,這個體系所規范的相關國際關系原則是不全面的,更多的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和經驗之下的。另一方面,它規范的更多的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準則,而對非國家行為體則沒有做明確的規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是國家行為體加非國家行為體共同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歐洲各國1648年簽署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同時,世界還存在幾個并行的體系,比如中國的朝貢體系,以中東為核心的伊斯蘭體系,而此時的非洲、美洲、澳洲板塊則遠居這些體系之外,尚未全面覺醒。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規范的只是歐洲部分板塊,對世界并沒有廣泛的約束力。
從中國的視角看問題,中國傳統體系出現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其中1592年的中日壬辰戰爭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這一年,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公然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對日本而言,這是其發動海外侵略戰爭的起點;對中國而言,則是自唐朝以來一直學習中國的“好學生”——日本,開始動手打“老師”了。③楊海英:“歷史意識與現實交響”,《光明日報》,2015年6月3日。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將日本的這種戰略意圖當作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戰略轉折,而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國的幻象中;及至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人依然還在半夢半醒之間;再及至日本人在1894年重演壬辰戰爭的那一幕,通過甲午戰爭將天朝大國的尊嚴打得體無完膚,中國才“猛回頭”完全驚醒。中國被西方堅船利炮和歐風美雨裹挾進現代所謂文明體系,再被當年自己的“學生”羞辱得顏面掃地,華夏體系也就無法維系了。但亡羊補牢,為時已晚,百年屈辱,由此開端。此后,中華民族開始了漫長的救亡圖存、民族獨立、國家建設進程,并最終走上通過改革開放邁向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
中國人的秩序觀、體系觀與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爭的事實。中西之間在所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發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沖突和隔閡由此而變得更加深刻,也是源于兩種不同秩序在不同軌道上的自我演進。而等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尤其是跟美國、歐洲主要國家在一戰、二戰戰場上并肩作戰,兩種體系才得以正式地正面互動。然而,這種互動對西方是主動的,對中國則是被動的。雖然中國也以戰勝國身份參與了華盛頓—凡爾賽體系的共建,但僅分得西方列強的殘羹冷炙,遭受的卻是更大的屈辱。二戰后構建的雅爾塔體系,中國終于能與美、英、蘇等列強共建,并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這是建立在西方對中國未來政治方向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國的國內政治方向出現另一種面貌,西方的臉色即為之一變。新中國仍然被西方視為舊世界,被孤立在美國主導的所謂國際體系之外。
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曾一度給美國和西方人再次帶來期望,認為中國從此走上融入西方體系的不歸路。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的命運始終還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幾十年之后,中國既沒有“西化”,也沒有“分化”,中國雖不再是那個封閉的中國,但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另一方面,中國不是蘇聯,雖在崛起,卻堅定地奉行和平崛起;雖堅持獨立自主,卻不全面挑戰既有國際秩序;雖沒有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卻在市場經濟經濟、自由貿易、對外開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堅決。對于這樣一個中國,美國人和西方人既愛又怕,想全面接納既放不下身段又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既難以做到又投鼠忌器,想放任自流則自覺風險太大承擔不起。怎么辦?奧巴馬在思考,希拉里在思考,特朗普也在思考,美國戰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卻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不論怎樣,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將世界各國歷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開始思考共建一個所謂既建立在國與國平等基礎之上,又必須思考非國家行為體;既要應對所謂“高政治”的政治、經濟、安全問題,又必須面對所謂“低政治”等非傳統全球性新問題的世界新秩序,構建所謂真正意義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歷史性地擺在人們面前,且首次成為可能。
五
如何構建新秩序?既然沒有一家能主導新秩序的構建,就只好依賴國際社會的再度合作。毋庸置疑,中美在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是合作者還是競爭者抑或對抗者,將直接攸關新秩序的成敗。為此,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伯格斯滕、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等在內的國際戰略家們紛紛建言獻策,從不同側面勾畫中美合作的藍圖。也有不少學者、政客以舊的思維預測甚至鼓噪中美沖突的未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提出“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議,體現了在世界秩序重構進程中中國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氣、主動、自信。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探戈需要兩個人跳,全球共同的事業需要世界各國共建。○
(責任編輯:黃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