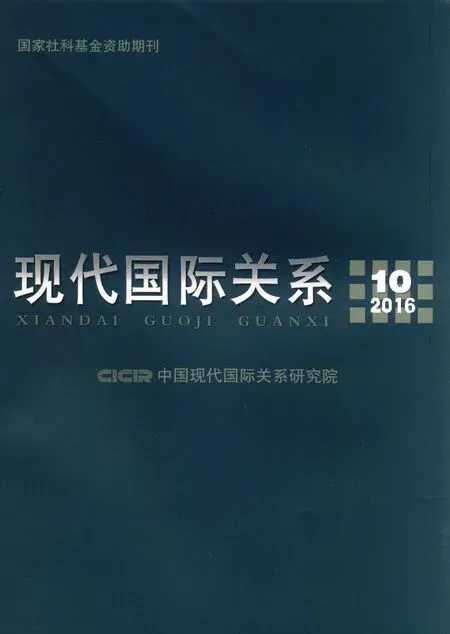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途徑及中國的應對
——從南海仲裁案說起*
王生張雪
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途徑及中國的應對
——從南海仲裁案說起*
王生張雪
中國一直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這種和平手段主要分為政治與司法兩種并在全球化時代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更傾向于運用司法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在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出于本國國家利益的考慮、結合爭端本身的特點選擇最適宜的爭端解決方式,是國際爭端是否能夠和平解決的決定性因素。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化趨勢不影響國家依據國際法所賦予的合法權利、自身偏好自主選擇國際爭端的解決方式。中國對“南海仲裁案”的“四不”立場,完全是由于仲裁案本身嚴重違反國際法,并不能由此否認中國參與和支持國際司法的積極立場和態度。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中國想要成功實現和平崛起,必須把握運用政治、司法手段處理國際爭端的“黃金分割點”,提升在國際公約的制定等議題上的話語權、爭端規則的動議和談判能力等,以在國際司法程序中增加勝算。
國際爭端司法途徑南海仲裁中國立場
[作者介紹]王生,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和吉林大學國家治理與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韓國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系和朝鮮半島問題;張雪,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東北亞國際關系和國際組織問題。
在全球化與區域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國際爭端的誘因不斷增多、形式日趨復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日益成為國際社會成員的一項重要任務。伴隨國際交往的全面加深,國際司法機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不斷深化,①Ernst B.Haas,Beyond the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85-205.國際爭端的解決機制呈現出明顯的司法化趨勢,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秩序導向規則化的重要表現。但是,國際司法程序本身的結構性缺陷使得其在不同時期、對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作用。每個爭端當事國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對所適用的司法程序都有一種理性的評估,無論是政治手段還是司法手段在處理國際爭端時各有利弊。孟德斯鳩式“法律統治世界”的理想還如星辰般遙遠,而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夠在最大程度保障本國利益的前提下為國際關系中的矛盾和紛爭提供一種解決方案,這就需要主權國家在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時候秉持理性審慎的態度,加大了選擇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的概率。
一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成為國際社會成員的一項重要任務和普遍選擇,協商、調解等政治手段在國際爭端的解決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國家間合作的加深,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更傾向于正規化和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彌補政治解決方式的局限性。早在20世紀60年代,國際上就有專家提出運用仲裁手段解決非法律性爭端,并提議設立常設仲裁庭專門管轄非法律爭端。①[英]J.G.梅里爾斯著:《國際爭端解決》,中國法律出版社,2013年。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聯合國國際法院為代表的國際司法機構不斷涌現,而冷戰期間人們對法律手段的信心增強與政治保障的減弱形成鮮明反差。據不完全統計,全球范圍內約有超過4000個雙邊或多邊條約中規定了將爭端訴諸仲裁或司法解決的條款,有100多個國際司法機構,其中包括國際法院(ICJ)、國際常設法院(PCIJ)、常設仲裁法院(PCA)等常設國際司法機構約20個。②王林彬:“試析國際爭端解決之司法化傾向”,《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蔣德翠:“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新發展——CAFTA爭端解決機制的法律與實踐”,《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為滿足國際社會的現實需求,國際司法機構正朝著多樣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其受案率不斷提升,表明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的需求不斷增加。
解決國際爭端的司法方式與傳統政治方式區別很大。政治方式主要有談判、協商、調查、和解、斡旋與調停等,沒有嚴格的程序規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靈活性、及時性,但所達成的結果往往因為缺乏約束力而難以執行。司法方式則是依據一定的原則規則和嚴格的程序規范做出有約束力裁決的第三方審判機制,主要通過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以及準司法機構(仲裁庭)等固定第三方司法機構實施,比政治方式更具專業性和合法性。一方面,司法解決爭端的主體是依據國際法或國際公約成立的司法機構或準司法機構,這些司法機構的法官、仲裁員等司法人員都是由國際范圍內公認的國際法專家和學者構成,它們更加具備專業性和國際法權威。另一方面,國際司法重程序而輕實體,國際司法機構在處理國際爭端案件的過程中往往預先制定公開的程序并適用其視為應當適用的國際法或國際公約,因而體現出較強的程序正義價值。當前,國際司法機構都沒有凌駕于程序規則之上的立法,幾乎都是以程序規則來指導自己的司法活動,國際法院曾在“西南非洲案”③1960年,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就南非聯盟有關西南非作為委任統治地繼續存在和南非作為受委任國因此而負的義務和職責向國際法院提起的訴訟。中提到“依據程序法的一般原則”,也就是說在很多國際司法機構中,關于程序的規范都是不證自明的。因此,以司法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更加符合當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正規化與法制化的發展方向。
然而,國際司法手段或方式運用于處理國際爭端時仍顯示出不成熟。盡管司法手段相比政治手段更加體現出國際法的權威和約束力,但就執行狀況而言,當事國對司法裁決并不比對政治手段樂觀。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國際司法環境不同于國內法,對于當事國的約束力較低,主權國家參與國際司法程序的自愿性大于強制性。司法裁決的執行主要依賴當事國的意愿履行。例如,1946年英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科孚海峽案”在國際法院的判決就沒有獲得阿爾巴尼亞的執行。此外,以司法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也會顯現出國家之間在實力與規范適用性上的政治博弈,因而司法過程和裁判結果常常體現出明顯的政治意涵。縱觀國際司法制度的發展歷史,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化趨勢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選擇的結果,因而國際司法也不可避免地顯示出當事國的利益訴求和政治目的,法庭和仲裁庭在對爭端案件的事實以及適用法律進行認定和選擇時,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干預。④何志鵬:“國際司法的中國立場”,《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第46頁。只是國際司法突出的程序價值和專業性優勢使其擁有比政治手段更加值得期待的進步空間。正如美國國際法學者路易斯·亨金所說:“在國際關系中,文明的進展是一個從武力到外交,從外交到法律的過程。”⑤[美]路易斯·亨金著:《國際法:政治與價值》,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
可見,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化趨勢是越來越多國家選擇司法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結果,這一趨勢也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國際司法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從而使國際爭端解決的主要方式逐步由權力導向轉變為規則導向。
二
國家是否會選擇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取決于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實力、對爭端解決能力的預期以及對利害關系的權衡。主權國家考慮到本國利益與爭端本身的特點選擇最適宜的爭端解決方式,是決定國際爭端是否能夠和平解決的關鍵。正如鄭永年教授所講:“主權國家都會在國際舞臺上追求自己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①鄭永年:“習近平與‘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替代”,[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9月29日。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動力之一,國際爭端的產生自然是因為爭端國家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但如果爭端國家雙方都試圖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那就難免陷入囚徒困境和避免失利困境(Dilemma of common aversion)②國家作為自私的理性主體,都希望能夠在合作中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得對方實現利益的最小化,這種狀況往往使得雙方本可以在博弈中實現帕累托最優解,即雙方通過合作實現集體最大利益,但出于對對方不合作或者欺騙行為的擔憂,最終只能夠實現帕累托次優均衡解,即合作失敗。。當今世界,國家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程度不斷深化,國際關系呈現出國家間的利益沖突和利益趨同共存的狀態。③參見秦亞青:“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41~43頁。因此,在爭端解決過程中,一國所要實現的是相對利益的最大化。國家的實力決定它是否有能力引導爭端解決朝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發展,在實力對比中占優勢的國家有更多的選擇主動性。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尼加拉瓜訴美國武力和準武力措施一案中,美國為了使其國家利益最大化,反對通過國際法院來解決爭端,并在判決后采取了不執行的立場。美國主張該案件實質為政治糾紛,只能通過雙邊和多邊談判解決。④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erbatim Report 2718,S/PV.2718,October 28,1986,p.40.無奈之下,尼加拉瓜將案件的執行事宜提交至第41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大會以多次一致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立即執行前述判決,但該決議由于缺乏強制力而無果告終。但是,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美國十分關注并支持通過仲裁庭解決爭端。美國對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方式所持的“合則用,不合則棄”態度,正是運用國際法的非中央化形態⑤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7th ed.,Revised by Kenneth Thompson and David Clinton,McGraw-Hill,2005,pp.285-286.實現本國利益的一種體現。
然而,作為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國際社會的一員,主權國家在表達和實踐本國利益訴求的同時,必須盡可能地使之符合國際社會的一般期待和普遍原則、履行其所做出的國際承諾等。國際法具有雙重法理基礎,一國在國際法律秩序中所享實證法意義下的權利往往可以使其國際行為具有更高的合法性⑥參見黃志雄、范琳:“國際法人本化趨勢下的2008年《集束彈藥公約》”,《法學評論》,2010年第1期。,在其軟實力超越其他國家時其國際行為就會更加具備道德權威和合法化優勢,在國際社會中的現實權力往往影響到其法定權利的獲取。國際法所具有的身份認同功能使其成為國際行為體在國際社會交往過程中的“共同語言”。⑦何志鵬:“國際法治的中國表達”,《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法律與生俱來的公正性使得解決爭端的國際司法途徑享有良好的國際聲譽,而一國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國如果能在解決國際爭端時訴諸司法機構,運用規則解決爭端則會獲得廣泛認可,否則可能使其國家形象受損。2002年7月1日,有史以來第一個永久性國際刑事法院正式在荷蘭海牙成立。但是,美國始終以國際刑事法院應給予豁免權相要挾而不買國際刑事法院的賬,因為它在全球范圍采取的許多戰爭或軍事行動并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它擔心國際刑事法院不按美國的標準辦案,最終會“損害美國的形象”。此外,國際慣例也對國家選擇司法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有一定的影響。在國際社會這樣一個平權系統當中,每個國家都有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這些傳統會左右當事國在處理國際爭端上的觀念。同時,國際社會一些成功的爭端解決司法案件會被總結成為系統性方案,作為國際慣例指導當事國對爭端解決方式的選擇和處理。例如,國際法在西歐國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因此西歐國家比較善于運用國際司法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東歐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國際仲裁和司法方面的經驗不足,因而更傾向于通過談判、協商等政治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問題。當事國爭端解決慣例的形成還受到該國在運用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方面技巧和能力的影響,如果一國在國際法領域有足夠的話語權,并能夠有相當的把握將爭端裁決導向有利于自己的結果,那么它會傾向于采用更具有說服力的司法途徑來解決國際爭端。
同其他解決國際爭端的途徑相比,司法途徑既有優勢但也有結構性缺陷。以南海仲裁案為例,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為依據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組成專門的仲裁庭就中菲南海“管轄權爭端”進行強制仲裁,并向中國發出《關于西菲律賓海的通知與權利主張聲明》(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中國外交部則于同年2月19日向菲方發出照會,申明“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拒絕接受菲方的仲裁請求。①國際海洋法法庭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的獨立的司法機關,總部設于德國漢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于2013年2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馬克卿于當日約見菲律賓外交官員,表明中方拒絕菲單方面提出仲裁申請。2013年4月24日,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應菲律賓的請求完成對中菲南海仲裁案5名仲裁員的任命,啟動了關于中菲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程序。2014年12月7日,中國外交部授權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再次聲明中國不接受、不參與仲裁的立場。仲裁庭2015年10月29日就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管轄權問題做出《管轄權及可受理性裁決》(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下稱《管轄權裁決》),2016年7月12日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做出最終裁決支持菲方要求。海牙國際仲裁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司法機構,不具有完全司法權,只有準司法權,因此其法律效力中有水分,②金燦榮:“南海仲裁案后中國面臨的壓力與應對之道”,《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7期。且它的南海裁決結果嚴重違反了司法需秉持的程序正義,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綜合看來,運用司法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的確有其優勢。首先,不同于運用政治手段需要爭端各方的相互妥協但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司法手段則因為其程序性而使爭端的解決過程滿足形式正義的要求,進而體現出一種公正性和效率性。南海仲裁案有明確的國際公約可作為實體和程序的指導,而程序則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司法途徑最重要的價值體現。正如伯爾曼所總結的那樣:“法之所以為法并與其他社會制度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相區別,在于它的形式化和程序化,正是法律程序的形式使得法律關系成為一種特殊的和獨一無二的社會關系。”③Bimal N.Pate,l“The World Court Reference Guide and Case-Law Digest:Judgements,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2001-2010)and Case-Law Digest(1992-2010)”,Martinus Nijhoff Press,2014,p.201.南海仲裁案所依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了仲裁的過程必須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例如對仲裁庭的設立必須由海洋法庭庭長根據《公約》第287條和附件七組織設立。④《公約》第287條規定:“一國在簽署、批準或加入本公約時,或在其后任何時間,應有自由用書面聲明的方式選擇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方法,以解決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a)按照附件六設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b)國際法院;(c)按照附件七組成的仲裁法庭;(d)按照附件八組成的處理其中所列的一類或一類以上爭端的特別仲裁法庭。”對于仲裁庭的組成,《公約》附件七第三條規定,爭端當事方可以各自指定一名仲裁員,剩余三名仲裁員則由當事方以協議指派,由此各方均可指定一名傾向自身立場的仲裁員,同時可以協商確定三名持中立立場的仲裁員,以便雙方在仲裁員任職上達成某種平衡,使解決國際爭端的司法途徑體現出程序上的正義。其次,司法途徑在處理國際爭端方面具有相對高的效率性。國際司法通過特定的設計體現出正義的制度安排,而效率則構成正義的一個價值標準。這種效率價值具體表現在對司法人員的配置、分工以及程序規則的設計上。例如,在南海仲裁庭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制定仲裁程序規則,且對于仲裁員也有明確的職能設定,包括制定仲裁程序規則、傳喚證人或專家作證以及視察涉案地點、查明事實和法律、發表意見。⑤吳慧、商韜:“國際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員因素——以中非南海仲裁案為例”,《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57頁。根據這一規則,整個仲裁過程有序進行,盡可能減少程序外的資源浪費,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程序的效率。
當然,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途徑具有松散、不成熟的缺陷。這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首先,司法作為國際爭端解決途徑的法律依據存在適用性瑕疵。南海仲裁案所適用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在全球海洋權益斗爭達到巔峰的時代背景下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最終結果。①為調解國際范圍內頻頻發生的海洋權益爭端,1958年和1960年分別召開了兩次國際海洋法會議,但這兩次會議所達成的四項公約在國際范圍內接受程度不高,尤其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于是1973年召開第三次會議,有168個國家參與,最終達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它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但在細節上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為當事國根據本國利益解釋適用其規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因而缺乏法律規范本應具備的法律邏輯和操作性。②參見羅國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立法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云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第126頁。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就試圖利用這一缺陷,將與中國的主權爭端包裝成《公約》項下的訴求。例如,菲律賓訴求第四項要求仲裁庭對美濟礁、仁愛礁、渚碧礁確定為《公約》所指的低潮高地,并確定其不可被國家通過占領取得。因為從法律上講,如果它們屬于“島”,那么按照以陸定海的原則,中國可享有12海里領海和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如果它們是“礁石”,那么就只有領海沒有專屬經濟區;而如果它們屬于“低潮高地”,那么中國就沒有相應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換言之,如果仲裁庭支持菲方訴求,那么菲方就成功排除了中國對這三個礁巖的主權。這正是利用了《公約》在確定島嶼、島礁、礁巖和低潮高地等海洋中不同地質特征土地主權和歸屬規則上的空白和缺陷。
其次,解決國際爭端的司法途徑仍然具有政治性,這很容易使其淪為霸權國家推行對外戰略的工具。③Rebecca Wallace and Olga Martin–Ortega,International Law,7th Revised edition,Sweet&Maxwell,2013,p.333.國際法是主權國家之間相互協商、妥協的產物,是一種帶有協議性和平權性的弱法,政治主導性幾乎貫穿全部環節中并會對國際司法的判斷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最終結果或是實力較大的國家之間通過政治方式爭取各自利益,實力較弱的國家唯有在大國政治的夾縫中生存,同時試圖通過法律尋找空間。在南海仲裁案的整個過程中,利益相關方的政治干預痕跡隨處可見。南海問題由來已久,之所以在國際上受到廣泛關注并發展成為國際爭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南海地區的重要地緣戰略位置和豐富海洋資源,雖然各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開始爭相搶占南海島礁,但南海問題直到21世紀前10年也未進入相關國家的外交政策重心而致成為國際關注的重大爭端。新加坡國立大學王雨江教授認為,中菲南海仲裁案產生的的導火索可以說是各國按規定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對自己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主張,中國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的主張存在沖突;但其根源主要還在國際政治方面,因為南海也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大利益所在,南海仲裁案是美國“巧實力”的一種體現,其背后是中美之間的政治博弈。中菲南海仲裁案啟動后,為了聲援菲律賓,美國國務院在2014年12月5日發表了《海洋界限第143號——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質疑中國使用南海“九段線”的“可能”海洋主張的合法性。④Office of Ocean and Polar Affairs,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Limits in the Seas No.143—China: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上網時間:2016年7月12日)同日,越南外交部也就南海仲裁案向仲裁庭提出聲明,支持菲方在此案的立場。可見中菲南海仲裁案并非只關乎中菲兩國的利益,其他利益相關方也會通過各種手段參與案件的走向。此外,仲裁庭對于仲裁員的選定也體現出政治傾向性。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的五名仲裁員包括由菲方選定傾向于其自身立場的仲裁員、四名由海洋法法庭庭長與日籍法官柳井俊二代為指定的仲裁員,而柳井俊二曾在日本外務省任職并參與釣魚島問題、日美安保條約問題等敏感政治事件,其政治立場難免會有明顯的傾向性。
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國際司法的這種結構性缺陷在很長時期內不會改變,此間人們既無法對國際司法抱有良法善治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將其視作強權政治的附庸。國際關系中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悲觀循環之間的矛盾在這里顯現得尤其明顯。因此,主權國家在選擇適用國際司法手段以解決國際紛爭時需要更加全面和謹慎的考量。
三
司法方式日益成為與政治方式并行的國際爭端解決方式。世界各國無一能夠超然于外。中國必須順應這一國際大趨勢。南海仲裁以及由此引發的惡意炒作和政治操弄向崛起的中國拋出了怎樣應對國際爭端解決司法化趨勢的新課題。的確,南海仲裁案本身存在嚴重的合法性問題,中國有權拒絕參與,且考慮到自身在國際司法中的影響力、技術和能力,如果貿然參與其中則很可能帶來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的后果。但是,在國際秩序規則化的進程中,中國對南海仲裁的態度和立場很容易授人以柄、遭遇一些國家惡意炒作,以致極大地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積極推動國際格局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所主導的一極格局現實相互沖突,中美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安全困境以及零和博弈難以避免。一些雙邊和多邊的國際爭端就折射出中美間的這種矛盾和博弈。
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給中國的海洋安全與穩定埋下隱患,為許多與中國存有海洋爭端的國家向中國提出無理主張制造了某種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傳統的、單一的國際爭端解決途徑根本無法滿足中國的實際需求。而司法途徑作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多元化的一個方面,為消解爭端各方之間的誤解、緩和局勢提供了歷史性契機,也為促進交流和溝通提供了平臺和對話機制,降低了爭端各方之間摩擦升級為戰爭的風險。因此,中國在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多元化、司法化趨勢有客觀的“認知”的基礎上,需要多方著手,積極應對。
首先,中國應努力走向全球治理的中心地帶,在國際司法舞臺上爭取與國家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樹立負責任的法治大國形象。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目前最大的挑戰都與其國家形象有關。”①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形象”,載于[美]喬舒亞·庫珀·雷默等著,沈曉雪等譯:《中國形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頁。而長期以來,中國在應對國際爭端時傾向于使用談判、協商等政治手段,這是由于受到歷史文化以及國際司法能力和技術水平的局限。中國要想改變這種局面,要在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途徑中變被動為主動、構建多元化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需要積極參與到國際法從立法、司法到執行的各個環節中,并切實提升參與的能力和技術,逐步從規則遵守者成長為規則制定者。目前,國際社會中多數的司法人員是來自歐美國家,國際法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從西方國家的傳統和價值取向,許多國際司法機構的裁判方式也傾向于英美法系、裁決結果往往代表傾向西方國家的政治立場,而中國在國際司法中的影響力則明顯薄弱。因此,中國必須盡可能廣泛地參與國際法的規則制定和決定執行過程中,在對國際議題的設置、國際規則的設定以及國際司法的實踐方面爭取應有的話語權。中國應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協商和立法過程,主動宣講本國的立場和理念,爭取國際社會更多的了解、更深的理解和更有力的支持。同時,中國應當更加主動地參與國際司法程序,創造條件使自己盡早成為國際法強國及具有良好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的大國,并使國際司法的程序設計體現出本國的觀點。另外,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中國在國際司法知識普及和人才培養方面都比較薄弱,這是中國國際司法能力和技術的短板。以南海仲裁案為例,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庭長是日本籍的柳井俊二,而日本與菲律賓都是中國周邊海洋爭端的當事國,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很可能對中日東海爭端產生影響,因此柳井俊二很難排除本國利益而在案件中秉持公正。菲律賓在南海仲裁案中所聘請的律師則是其盟國——美國的著名律師保羅·賴克勒,他在尼加拉瓜訴美國準軍事活動案中一舉成名,被譽為國際法領域“巨人殺手”。②江河:“國際法框架下的現代海權與中國的海洋維權”,《法學評論》,2014年第1期,第98頁。但是,中國一直奉行不結盟政策,在國際爭端案件中很難聘請外籍律師,這也是中國難以高效參與國際司法活動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必須大力培養并大量向國際社會輸送高素質的司法人才,提升國際司法機構里中國法官和仲裁員的數量和質量,以幫助在中國和國際司法之間實現信息共享,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升中國在國際司法案件中的勝訴率。在專業化高素質的國際司法人員和涉外律師的人才支持下,中國才能在國際司法程序中運用法律手段充分表達本國的立場、維護國家利益。
其次,中國應當順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多元化發展大勢,積極探索、整合各種爭端解決方式,實現“善治”和“法治”的目標。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爭端的主體不斷增加,所涉問題日趨復雜。司法方式雖然是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多元化的體現,但所勾勒出的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并非完美無缺。這從南海仲裁案等國際司法案件中可見一斑。其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國際司法途徑往往被用來作為小國應對大國的工具。一些小國在國家實力無法與大國相抗衡的現實條件下,借助國際組織和國際司法機制,將雙邊矛盾升級到多邊的國際層面,通過第三方向大國施加壓力,從而試圖達成在雙邊談判中難以達成的結果。二是國際司法解決爭端的結果有可能非但不利于國際爭端的解決,反而進一步激化矛盾、惡化爭端。國際法和國際公約的有關具體規定常常被一些國家濫用,比如臨時選定的仲裁員在公正性、專業性等方面都令人質疑。在南海仲裁案等案件中,仲裁結果具有十分明顯的傾向性,嚴重激化了矛盾、加劇了局勢緊張。對于中國而言,雖然解決爭端的司法途徑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但在選擇解決國際爭端的途徑時必須對可得的利益(包括可衡量的物質利益和不可衡量的無形利益)與需要付出的成本做出全面的理性評估并審慎抉擇。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爭端解決機制是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單一的司法手段或者政治手段都難以達到最佳的解決效果,中國應當主動調整應對措施,積極了解、接受或參與完善國際規則,整合包括談判、協商、仲裁、司法等在內的各種爭端解決方式,使各種方式相互補充,實現爭端解決機制的多元化發展。
總而言之,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是國際秩序建設的重要步驟,也是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多元化的表現,為爭端解決提供了一種更加規范的方式。但是,在國際關系很大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的條件下,國際司法本身存在結構性缺陷,尤其是在大國政治博弈下具有突出的政治意涵,難以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國際爭端解決的司法途徑所具有的這種松散性、不成熟性很容易使國際司法淪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工具,對當事國國家利益造成不利影響。因此,主權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理性行為體,在選擇爭端解決途徑時必須充分考慮各種途徑的成本與收益,審慎決定。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各相關部門需要盡快理順在以司法途徑解決國際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使得中國未來能夠盡可能做到既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又關注國家形象,在法治方面樹立起大國形象,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對于南海仲裁案這種爭端個案,中國應充分吸取經驗和教訓,確立以話語權為落腳點的國際爭端解決之宏觀戰略,提升國際司法參與的專業技術水平和能力。此外,中國還應當積極整合各種爭端解決方式,順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多元化趨勢,更好地應對崛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
(責任編輯:黃昭宇)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國朝鮮半島政策的挑戰與對策研究》(16BGJ03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