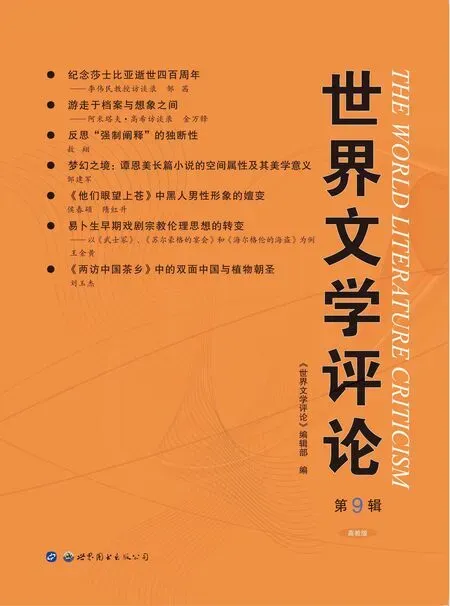對“強制闡釋”基本特征的疑惑
楊 子
對“強制闡釋”基本特征的疑惑
楊 子
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論》從發(fā)表以來就引起了文學理論界學者們的高度關(guān)注。“強制闡釋學”不僅在文論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guān)注,而且很多學者都參與了有關(guān)“強制闡釋”的討論。很多學者對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學”表達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并對張江先生的觀點表示贊同。本文分三個部分對《強制闡釋論》進行探討:筆者就“強制闡釋”產(chǎn)生的三點疑惑,《強制闡釋論》對中國文論的啟示以及“強制闡釋”的解決方法。
強制闡釋 疑惑 文本
自2014年在《文學評論》的第六期上發(fā)表《強制闡釋論》后,張江先生接連發(fā)表了多篇關(guān)于“強制闡釋論”的文章。那么,究竟何為“強制闡釋”?用張江先生的原話來說就是:“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jié)論的闡釋”[1]。自張江先生“強制闡釋”的觀點提出以來,引起了眾多學者的討論。這些討論中有對張江先生的觀點表示贊同的,例如姚文放就在《“強制闡釋論”的方法論因素》中對張江先生在《強制闡釋學》中提出的“場外征用”表示認同:“應(yīng)該說,不同學科、不同理論的交叉融合總是給文學理論提供豐富的營養(yǎng)和不竭的動力。但關(guān)鍵之處還是如張江所說,這種借用、沿用和移植必須文學實踐的內(nèi)生動力,必須達成與文學經(jīng)驗的強力碰撞和深度融合。否則這種‘場外征用’就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剝,不僅傷害了文學,也傷害了引進的理論。”[2]當然有些學者對強制闡釋學也提出了疑問,其中比較代表性的文章就是朱立元先生的《關(guān)于“強制闡釋”概念的幾點補充意見——答張江先生》。
雖然文論界對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論”的看法意見不一,但筆者認為在當今中國文壇上確實存著這種“強制闡釋”的問題。所以“強制闡釋”問題的提出值得眾多文論家、學者進行反思,反思自己在文學創(chuàng)作或是論文寫作的時候是不是也出現(xiàn)過“強制闡釋”的現(xiàn)象。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對強制闡釋學展開分析,一方面雖然筆者對張江先生提出的強制闡釋學大體認同,但筆者對《強制闡釋論》這篇文章中的部分觀點仍然存在困惑;另一方面,針對當代文壇出現(xiàn)的“強制闡釋”現(xiàn)象,筆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意見。
一、對《強制闡釋論》的疑惑
《強制闡釋論》可以作為張江先生提出的強制闡釋學的綱領(lǐng)性文章,文章中張江先生將強制闡釋的特征分為四個:場外征用、主觀預(yù)設(shè)、非邏輯證明和混亂的認識途徑。雖然作者對這四個特征的解釋比較清楚,但是筆者對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觀點仍然存在疑惑。
首先,在《強制闡釋論》中張江先生寫道:“從20世紀初開始,除了形式主義及新批評理論以外,其他重要流派和學說。基本上都是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建構(gòu)自己的體系。許多概念、范疇,甚至基本認知模式,都是從場外‘拿來’的。這些理論本無任何文學指涉,也無任何文學意義,卻被用作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基本范式和方法,直接侵襲了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本體意義。”[3]在張江先生說的這段話中筆者比較認同他說的前幾句話,除了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外其他的理論和學說都是基本借助于其他的理論和方法。但是,筆者對張江先生認為除了這兩種理論外的其他理論沒有任何文學意義,而且這些理論還侵襲了文學的本體意義的論斷存有疑惑。
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完全理解一個理論就在文章中生搬硬套,為了證實一個理論的正確性而扭曲作者本意,對作品進行歪曲解讀等現(xiàn)象的確是強制闡釋,但是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礎(chǔ)上運用一個或幾個與作品相適用的理論進行批評并不屬于強制闡釋。雖然,很多理論起初是在其他領(lǐng)域中提出來的,但是與文學完美地結(jié)合之后,這些理論也能運用在文學中去。就拿女性主義批評來說,最先提出這種思想的是女權(quán)運動,后來這種思想被文學借鑒并與文學結(jié)合形成了女性主義批評。用這種批評方式來解讀一些作品的確屬于強制闡釋,例如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解說雨果的《悲慘世界》,我們的確可以懷疑這是一種強制闡釋。但是當我們用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解說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的話,卻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簡·愛是生活在英國的19世紀的女性,當時的英國社會認為完美的女性應(yīng)該體現(xiàn)在家庭中,這種女性就像天使一樣照顧孩子和丈夫,但與英國當時其他的女性不同的是,主人公簡·愛走出了英國當時的社會給女性設(shè)定的三“C”世界——教堂(Church)、孩子(Children)、烹飪(Cookery)。她對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束縛進行了反抗:“《簡·愛》體現(xiàn)出了女性意識和女性主義觀點,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無疑是男權(quán)文化的犧牲品,孤女簡·愛強烈的獨立意識則是小說世界的一個標尺。”[4]我們從《簡愛》中主人公簡·愛公開和舅母對抗、離開孤兒院當了家庭教師、在知道羅徹斯特有妻子后毅然出走等一系列舉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簡·愛身上閃動的女性主義力量。例如在與莊園主羅切斯特的第一次對話時,簡·愛就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女性主義思想,羅切斯特先生問她覺得自己漂亮嗎,但是簡·愛的回答是:“不,先生。”①從簡·愛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意識。在她看來自己和羅切斯特沒有什么不一樣,他們的關(guān)系也不是所謂的主仆關(guān)系,因為他們是平等的。
再比如我們用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同樣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身上也閃現(xiàn)了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與當時其他的貴婦人不同,安娜追求真正的愛情,為了愛情她拋下了一切。雖然當時很多貴婦人在外面都有情人,但與安娜不同的是,她們絕不敢離婚,像安娜一樣為了愛情而拋下一切的做法在她們看來可謂是離經(jīng)叛道。當沃倫斯基為了自身的利益漸漸遠離安娜的時候,她并沒有選擇回到卡列寧的身邊,相反,她用臥軌自殺的方式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從安娜的這些舉動上面都可以看到安娜身上閃現(xiàn)的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因此,用女性主義批評的方式對《安娜·卡列尼娜》進行解讀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沒有好好地理解一本書之前就用某種方法套用的做法屬于強制闡釋,但是看完并理解完一部作品之后再用與之相適應(yīng)的理論方法來對文本進行解讀并沒有侵襲文學的本體意義。而且,雖然很多文學理論是從別的學科的理論上借鑒而來,但是只要這些理論與文學能夠完美結(jié)合的話,還可以從別的角度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品。
筆者的第二個困惑是:張江先生在“場外征用”這一章節(jié)的敘述中認為場外理論進入文論場內(nèi)的方式大致為三種,這三種方式分別是挪用、轉(zhuǎn)用和借用。筆者在對這三點反復看了幾遍后仍然不明白這三種方式的區(qū)別。在對這三種方式分別進行解釋說明的時候張江先生對這幾種方式本身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這樣對閱讀者就會造成閱讀困難。在論文中張江先生是分別用一些例子對這些方式來進行解釋說明,比如他用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文論家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來解釋“挪用”:“任何一部敘事作品,其內(nèi)部元素都可以被分解成四項因子,納入這個矩陣。矩陣內(nèi)的四項因子交叉組合,構(gòu)成多項關(guān)系,全部的文學故事就在這種交叉和關(guān)系中展開。”[5]在解釋“轉(zhuǎn)用”的時候張江先生是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文論來敘述的。在解釋什么是“借用”的時候,張江先生用空間理論的借用來進行解釋說明的。其中,在對“轉(zhuǎn)用”進行解釋的時候,張江先生說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文論史從其哲學解釋學擴展而來:“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為了建立與十九世紀方法論解釋學相區(qū)別的本體論解釋學,伽達默爾把目光轉(zhuǎn)向了文學和藝術(shù)。”[6]根據(jù)文中的這個例子筆者有兩個疑惑。第一,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轉(zhuǎn)用”就是將某個人在另一領(lǐng)域提出理論來用于文學,而且在文學上這種形式的“轉(zhuǎn)用”還應(yīng)該是為了印證這個理論的正確性,其目的本不在于文學本身?第二,在強制闡釋理論中“轉(zhuǎn)用”的范圍是不是必須限定為這個人在其他領(lǐng)域的理論,而不能用其他人的理論?而且,張江先生對場外理論進入文論場內(nèi)的這三種方式?jīng)]有一個標準的定義,如果再出現(xiàn)一個其他的例子就很難分辨出這到底是挪用,還是借用、轉(zhuǎn)用。
筆者的第三個困惑是:“強制闡釋”是不是當代西方文論所獨有?中國文論自身是不是也存在這種強制闡釋呢?雖然張江先生在《強制闡釋論》中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針對20世紀的西方文論,但是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我們也可以想一想中國文論本身是不是也存在這種問題。如果中國文論也存在這種問題的話,我們應(yīng)該如何學會規(guī)避這種問題呢?在筆者看來,中國古代文論也是存在這種“強制闡釋”的問題的。例如,在解釋《關(guān)雎》的時候《毛詩序》的解釋是:“是以《關(guān)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其大概的意思是《關(guān)雎》說的是后宮嬪妃的品德,這首詩是為了給大家呈現(xiàn)一個貞淑無妒、顯家興國的道德模范。但是,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認為《關(guān)雎》體現(xiàn)“后妃之德”的觀點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關(guān)雎》出自《詩經(jīng)·國風·周南》,而《國風》中的詩篇幾乎全是來自于民間,民間的詩歌中又怎么會出現(xiàn)“后妃之德”呢?其實,細想一下,很多中國古代文論都出現(xiàn)過“強制闡釋”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產(chǎn)生從很大一方面來說是與政治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者們希望用前代文學大家們的經(jīng)典之作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為了鞏固統(tǒng)治,對一些經(jīng)典之作進行曲解就成為很多君王的統(tǒng)治手段了。在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再對古籍進行閱覽和品鑒的時候,除了查閱那個時代的古籍之外,我們更應(yīng)該從文本本身入手,只有先從文本入手才有可能不會曲解作者的本意。
二、《強制闡釋論》對中國文論的啟示
自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論”產(chǎn)生以后,文學界也因此掀起了一股關(guān)于“強制闡釋”討論的熱潮。很多學者就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論”也在和學者們的不斷討論中得到豐富和發(fā)展。但是,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們不能只看到問題而不想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對于如何應(yīng)對我國學術(shù)界出現(xiàn)的這種“強制闡釋”現(xiàn)象也應(yīng)該成為文學研究者們討論的內(nèi)容。
我們應(yīng)該立足于中國文論自身的建設(shè),立足于中國民族文學的探索。我國學者之所以用20世紀西方文論進行強制闡釋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文論自身的成就不顯著。相比20世紀的中國文論,20世紀的西方文論可以說是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各種文論層出不窮,很多文論都是在反對另一種文論的基礎(chǔ)上提出自己新的意見和看法,而后一種文論也在反省前一種文論所出現(xiàn)的問題的時候完善自己的理論。所以,20世紀的西方文學才能得到如此飛速的發(fā)展。和20世紀的西方文論相比,20世紀的中國文論仍舊停滯不前,大多數(shù)中國的文論家們所做的就是把西方的文論引中國并采用這種西方的理論研究問題。當然,西方20世紀所出現(xiàn)的很多理論都是很有建樹的,也是很有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但是,我們不能一味地引進而不知道創(chuàng)新。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不能只知道“拿來”而不知道創(chuàng)新。
那么,中國文壇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筆者認為這與某些中國學者喜好“空談”有關(guān)。很多學者離開文學的實際情況空泛的討論問題而不付諸于實踐:“我深知自己做不成,想也不敢想。連固守學院院墻的學術(shù)型批評家也自感不配,更何況做那敢于挑戰(zhàn)文學媒體、文學產(chǎn)業(yè)、文學作品、新聞消遣型批評以及學術(shù)型批評自身的詢構(gòu)批評家?于是,我就只能發(fā)出這種可能會被嘲諷為坐地沖鋒的呼喚了。”[7]針對這種現(xiàn)象,我們應(yīng)該反省自己,我們是不是應(yīng)該在思考問題的同時付諸于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而且,我們在對西方文論引進的時候也應(yīng)該大力發(fā)展中國文論,讓中國文論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注意不能走民族主義的道路。就像羅宗強所說:“讓國際文論界能聽到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這樣一個目的,不能說它不對。但我以為,這著眼點似乎有點錯位,理論建設(shè)的目的,應(yīng)該首先想到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需要什么。文學理論的建立是為了解決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中的現(xiàn)實問題。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創(chuàng)作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tài),有些什么樣的問題有待理論的探討: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都有些什么問題需要解決,這才是我們的文學理論賴以建立的主要依據(jù)。”[8]中國應(yīng)該是世界文論這個大花園中的一部分,在“引進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應(yīng)該注意要“走出去”。因此“民族化可以作為中國文論建設(shè)的基本方向,但不能把它最終目的化,更不能由此陷入‘文化原教旨主義’的泥淖而將他者文論‘妖魔化’或‘政治化’。”[9]
因此,我們在不走民族主義的道路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中國文論,并在將中國文論不斷地完善更新的基礎(chǔ)上將理論建設(shè)與實踐相結(jié)合的話對于避免自身對文本進行“強制闡釋”有著極大的幫助。只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才會對中國文論、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有所幫助,也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走出張江先生所說的“強制闡釋”的泥淖中去。
三、重視文本:“強制闡釋”的解決方法
張江先生“強制闡釋學”的提出不僅讓很多作家學者認識到自己可能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存在的問題,并且還能讓更多有識之士關(guān)注這個問題,同時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如何避免“強制闡釋”現(xiàn)象發(fā)生的討論中去。這不僅僅能加深我們對自己的了解,還能對今后的創(chuàng)作,對中國文論的發(fā)展有著極大的推進作用。
那么,我們應(yīng)當如何避免自己進入“強制闡釋”呢?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創(chuàng)作中可能出現(xiàn)“強制闡釋”的問題時,我們也應(yīng)該更加重視文本的作用,將文本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從“強制闡釋”的角度來看,很多學者在進行論文創(chuàng)作的時候,都是先想好了理論,再用理論對文本進行套用。還有的學者,純粹為了證明一個理論的正確性而對某個文本進行解說。這種現(xiàn)象在如今的文壇上并不占少數(shù)。為了避免這一類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就應(yīng)該從文本本身出發(fā),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礎(chǔ)之上再選用與文本相適應(yīng)的文學理論來進行闡述。一部好的作品的確可以從多個方面對其進行解讀,從不同角度對文本進行解讀的同時也應(yīng)該采用與之相對應(yīng)的批評方法。例如當我們解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的時候,我們既可以從他所提倡的“硬漢精神”對文本進行解讀也可以從生態(tài)主義批評的角度對這部作品進行分析。實際上,一部好的文學作品的確有著多重主題,作者在對文學作品的時候可能主要只是針對其中一個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但是,文本中除了作者花很多筆墨寫得這一個主題之外還應(yīng)該有其他的方面值得我們?nèi)ヌ接憽.斘覀儗@些方面進行研究和探討的時候應(yīng)該在理解文本的基礎(chǔ)上采取與之相對于的理論方法,這樣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文本的了解還可以從一個嶄新的視野對文本進行解讀。除此之外,我們在重視文本的同時也應(yīng)該注意將作家與作品相結(jié)合。因為一部好的作品,無論是從構(gòu)思還是遣詞造句等方面來看都與作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沒有作家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話又怎么會有一部好的作品呢?而且,一個作家在其生命的每個階段也有著不同的思考,就拿巴金來說,他的前期作品如《家》就與其后期作品《寒夜》、《憩園》在風格和思想等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熟悉文本之前了解作家的思想、情感經(jīng)歷、以及作家自身的轉(zhuǎn)變對于更好地理解文本來說是十分必要的。更加重視文本并把文本提高到一個更重要的位置不僅對走出“強制闡釋”的困境有著極大的幫助,也對更好的研究文本、更加深刻地了解作家的思想大有裨益。
注解【Notes】
①參見夏洛特·勃朗特《簡·愛》,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頁。
引用作品【W(wǎng)orks Cited】
[1]張江:《強制闡釋論》,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第5頁。
[2]姚文放:《“強制闡釋論”的方法論因素》,載《文藝爭鳴》2015年第2期,第65頁。
[3]張江:《強制闡釋論》,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第5頁。
[4]張翠萍:《簡·愛的女性意識新議》,載《名作欣賞》2005年第24期,第37頁。
[5]張江:《強制闡釋論》,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第6頁。
[6]張江:《強制闡釋論》,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第6頁。
[7]王一川:《通向詢構(gòu)批評——當前文學批評的一種取向》,載《當代文壇》2009年第1期,第8頁。
[8]羅宗強:《古文論研究雜識》,載《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9頁。
[9]魏建亮:《關(guān)于“強制闡釋”的七個疑惑》,載《山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第43頁。
Title: Questions abou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Author: Yang Zi 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d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which is written by Zhang Jiang has been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of literary theorists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current academia,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has not only draw wide attention, but also trigger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Many scholars have come up with his own original ideas and agreed with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o discuss A Discussion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my three questions about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the inspirations that A Discussion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gives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lutions to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question text
楊子,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