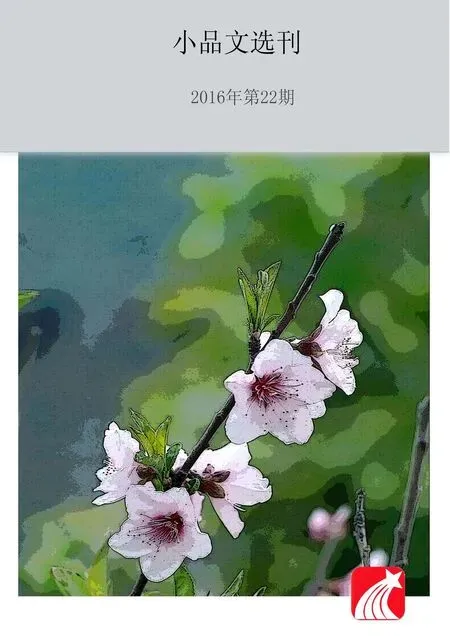從薩特的“存在主義”看逆境中成長的安東尼亞
郭學超
(西安外國語大學 陜西 西安 710000)
從薩特的“存在主義”看逆境中成長的安東尼亞
郭學超
(西安外國語大學 陜西 西安 710000)
薇拉·凱薩筆下處于逆境中的安東尼亞,努力為獲取獨立和幸福做出的抗爭體現了薩特“存在主義”提倡的“存在不應該只停留在想象和觀念中,人應該采取行動以實現人生的價值”。無論安東尼亞在何種境遇下抗爭求存,都從未磨去她的初衷和本真。體現了薩特“存在主義”的精髓:人的本質是人通過自己的選擇和造就的,人在事物面前,如果能夠按照個人意志保持自我,就能更加堅定地秉持自我超越和自我擔待的精神,實現生存的意義和價值。
安東尼亞;薩特;抗爭
1 引言
薇拉·凱薩是美國著名的現代主義作家,主要以自然、美國西部草原為題材,突出女性形象。她的著作《我的安東尼亞》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從上世紀四十年代起,評論家認為《我的安東尼亞》是一部逃避現實的作品,將薇拉·凱薩標簽為對現實失去希望的懷舊作家。此后,批評家們的視角開始轉到女權主義,女權批評主義,同性戀中吉姆的敘事特點等。到21世紀國內學者主要從超驗主義,生態批評主義,文化批評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移民生存策略,以及安東尼亞的成長主題視角評析。關于安東尼亞的成長主題,學者主要從安東尼亞與環境(尤其是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為切入點探討安東尼亞的成長,忽略了安東尼亞自我意識對其成長的意義。本文主要從薩特的“存在主義”看逆境中成長的安東尼亞。從薩特的存在主義看安東尼亞為生存,為獲取獨立、幸福的抗爭其自我意識的覺醒對其選擇和行動的意義。
2 從薩特的存在主義看逆境中的安東尼亞
安東尼亞與家人從歐洲的波西米亞移民到美國西部的內布拉斯加州,正值漫長嚴寒的冬季,無法耕作,沒有糧食收入,初到一個與家鄉風俗完全不同的地域,還不懂得如何謀生,生活異常窘迫。安東尼亞的父親沒能熬過冬天,他是自殺的。大雪,寒冷,生活的艱難,對家鄉的思念,藝術生活的失去導致精神的乏味和空虛,使他徹底散盡了活下去的勇氣,內心的苦儼然到了無法承受的境地。
安東尼亞一家在承受了比生存更大的苦難——父親的離去后,迎來了春天。安東尼亞一家在土地上拼命地勞作,吉姆驚訝安東尼亞在父親死后的八個月里竟成長到這般:十五歲的生日才過,她從一個剛剛還是孩子,瞬間成長為一個高高、壯壯的女孩。穿著父親自殺前脫下的靴子和皮帽,整天里卷著袖口,嗓子和手臂曬成了棕色,像一個水手,脖子硬挺挺的,像個樹干。安東尼亞告訴吉姆,她不想比杰克干的少,她想在秋天里收獲更多的糧食。時間沒有讓安東尼亞出落成一個溫婉、恬靜的少女,歲月的艱難讓她選擇勞作起來像是一個男人,為了一家人的生存,在土地上付出自己能力范圍內的所有勤勞。安東尼亞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在土地上頑強的抗爭求存,她從移民到內布拉斯加州,就不再是吉姆眼里或吉姆爺爺奶奶定義的美麗、優雅的少女。她選擇讓自己的意志、態度符合環境的需要,她始終知道為了家人更好的生存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為了家庭的生計,安東尼亞不得不選擇與土地為伴而放棄上學。在吉姆看來她選擇的是一條粗俗之路,但從安東尼亞對父親的尊重與敬仰來看,她內心對藝術,對知識的渴求是非常強烈的,但是為了生存,為了保障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她不得不將對藝術和知識的向往留在心底。安東尼亞始終將父親視為一種信仰,作為自己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物質的保障是她顯性、外在的追求,精神和藝術才是使她真正生活下去的內在支撐。薩特說,人的本質、人的各種特征都是后來由主觀性自行選擇和造就的。人的選擇和行動是自己意識的一種映射,因為別的事物不能夠去決定、定義他的意識,因此他就需要去決定自己、自己選擇、自己造就自己。安東尼亞無論處在何種境地,身處家鄉還是異鄉,接受與不接受教育,以及后來的城鎮生活和被第一個愛人拋棄,都未能改變她最初的本質——純樸,真實,鮮活,進取。這是她的選擇,她始終遵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受外界干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的本質,造就自己的人生。安東尼亞的本質、經歷和人生與薩特的思想是共鳴的。德國諾貝爾獲獎作家赫爾曼·黑塞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途徑,人只應服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屈從任何外力的驅使,并等待覺醒那一刻的到來,這才是善和必要的行為(黑塞2013:71)。
安東尼亞在“第二次”婚姻里獲得了最終的獨立和幸福。當吉姆最后一次去看安東尼亞的時候,吉姆感覺安東尼亞存在感很強,一股品質的力量浸漫全身,幾經歲月的磨折卻未見任何屈服過的痕跡。安東尼亞告訴吉姆她和她的丈夫來到這個新的鄉村,她的丈夫對農耕幾乎一無所知,她挑起了全部的重擔,并讓她的丈夫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安東尼亞始終感謝上帝讓她有一個健康,強壯的身體支撐她在土地上每次的播種和收獲。上帝的這份賜予源于安東尼亞自我意識的造就和靈魂的救贖。她的孩子,雖然出生在鄉下,但是在安東尼亞的培養下,舉手投足中流露著涵養和優雅,更有一顆美好、善良的心。這,應該是上天賜予安東尼亞最好的回報。
在薩特看來,人像一粒種子偶然地飄落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的本質可言,只有存在著,要想確立自己的本質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安東尼亞通過自己的行動,得到了丈夫的尊重、認可和支持,獲得了最終的獨立和幸福。這是詮釋她本質的最好的方式。
3 結語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論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識、概念、本質的傳統哲學,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安東尼亞經歷了父親的自殺,吉姆的離開,也經歷了如男人一樣在土地上勞作,“第二次”婚姻里的獨立和堅強。面對磨折,她選擇直面痛苦,隱忍和內在的強大;面對希望和機會,她選擇的是把握和創造。安東尼亞的選擇造就了她的人生。安東尼亞的腦海里沒有自我意識形態可以影響人生的哲學觀念,然而她的所作所為卻時刻體現、詮釋了意識與行動的哲學理念。所以,她才能走向自己的成功,獲得最終的獨立和幸福。
[1] Willa Cather.My Antonia[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11.
[2] 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譯文.2011
[3] [德]赫爾曼·黑塞.彷徨少年時[M].張念秋,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
[4] [法]薩特.存在與虛無[M].陳宣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5] 蕭紅.商市街[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
郭學超(1991-),女,漢族,河北省承德市興隆縣,碩士,西安外國語大學,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B086
A
1672-5832(2016)10-0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