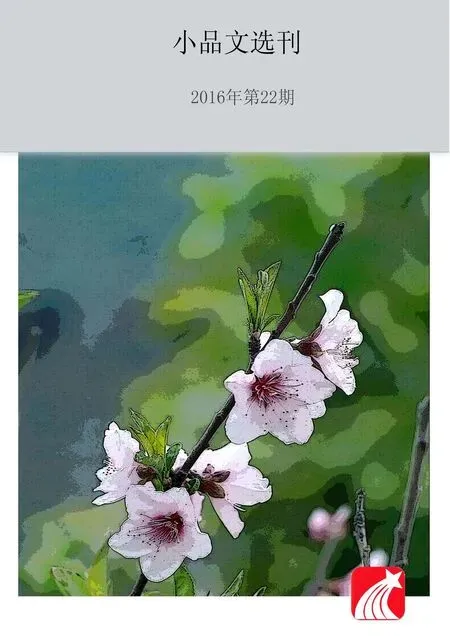人心泯滅的現實批判與不失本心的文學訴求
——評千夫長中篇小說《汗的羔羊》
潘佳麗
(江西師范大學 江西 南昌 330022)
人心泯滅的現實批判與不失本心的文學訴求
——評千夫長中篇小說《汗的羔羊》
潘佳麗
(江西師范大學 江西 南昌 330022)
白巖松在《幸福了嗎》中曾寫道:我終于明白,自殺的不是我,而是這個時代,是人心。人心的泯滅、道德的淪喪讓國人的生存狀態顯得更為焦灼,正如千夫長在創作談中說道:“人心都壞了,世道更壞。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壞中如何好一點活著。”對社會現實批判的無力感讓千夫長寧愿選擇對這種壞進行呈現,這種呈現卻是那么的觸目驚心。
人心泯滅;現實批判;不失本心;文學訴求
1 人心泯滅的現實批判
《汗的羔羊》是賀新年于2012年在北京創作的中篇小說,小說立足現實、合理構想,向讀者推演了地球生命的未來遭遇,讓讀者在閱讀中感知人類未來的明天可能天道崩壞、人心不古。作者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向我們生存的時代敲響了警鐘。
《汗的羔羊》向讀者呈現出的是一個經濟亂世,在這個經濟亂世中不管朝哪個方向眺望,總感覺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了親人。親人之外,皆是理性而陌生的“經濟人”。以經濟理性為核心的生存秩序取代了原有的生存秩序,民族共同體的軀殼和心靈在這個經濟亂世中一同被埋葬。那種人心與人心的赤裸相見,人情與人情的直接碰撞在此難覓蹤跡。醫院的經濟化早已將正義掩埋。交警的經濟世故也隱射出了金錢至上的價值理念,這種價值理念早已荼毒世人,作家正是借此來批判民眾,批判社會。但這種批判似乎還不夠墜地有聲,無論是醫院的所作所為還是交警的逢場作戲充其量只能說是道德的淪喪、社會責任感的缺失,距離人心泯滅的批判還有一定差距。作品真正震動讀者的是對汗的秘密的最后揭示。
汗是D國留學回來的畜牧博士,在國外從事研究,如今帶著研究成果回國興辦羔羊養殖場,可最后科技養殖出來的暢銷各地的羔羊肉只不過是形體變異的老鼠肉,而和“我”一同前往的鳥兒因發現并公開了汗的秘密被汗利用科技變異成了一只羔羊。此時“我麻木的腦子像冰一樣凍結了”。汗的行為已不是道德淪喪可以指責的了,此時的汗已是一個喪心病狂、人心泯滅的惡魔,他利用科技毀滅人類,毀滅生命,用生命之間互相變異的制衡來為地球生命重建秩序,這是多么的令人毛骨悚然。作者正是在小說結尾處以這種意想不到的結果來批判現實、警醒世人。
科學是第一生產力,但科學失去道德標準,接著就會喪失認識力量和實踐活動,于是科學就變成偽科學。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來殺人。于是乎,主宰工具的人便是關鍵,人的心純凈,行才能至善。作者正是借此來批判現實社會,警醒世人。為了強化作品的現實批判性,作者虛實結合,將已然的事實和意想的故事交叉于作品情節之中,“我”既是文本中的“我”又是現實中的我,如“我”寫作之前是做酒的商販與作者的經歷如出一轍。作者正是采取這種虛虛實實的敘事方式來強化作品的現實感,增強讀者的危機感,讓讀者意識到倘若人心不向善,那么文本中描述的人心壞了,世道壞了之后的生存狀態便會得到印證,到那時就真的是啥也沒有了,一片黃沙,人心的荒漠,寸草不生。
2 不失本心的文學訴求
莫忘初衷,不忘本心,勿迷自性,以向善之心行至善之事,這是一個民族的落腳點,也是一個國家的落腳點。生命之間新的平衡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暴力,不是依靠異化的能力,而是依賴于生命群體的共同創造。文學是人學,文學應以人為對象,文學的題材應該是人,應該是時時在行動中的人,應該是處在各種各樣復雜關系中的人。正如錢谷融所認為的那樣“一切都是從人出發,一切都是為了人。”千夫長的中篇小說《汗的羔羊》在批判社會現實的同時,也流露出了不失本心的文學訴求,以求得未來更好的生存狀態。
《汗的羔羊》中汗的行為讓人驚悚,但千夫長并沒有將汗徹底的魔化,而是為其存留了一點人性。千夫長舉動無非是給自己一點希望,給讀者一點光亮,而這也正是千夫長期待世人不失本心的訴求。在這個金錢至上、情感廉價的經濟亂世,千夫長還刻意為讀者灑下了一縷陽光。
千夫長在小說中多處呈現出了人性的冷漠。醫生、交警不分對錯,只看利弊,對自己的職業沒有責任感,表露出來的只是經濟利益。養殖基地中人情的冷漠更是升溫到了極致,“巴根哥倆說話的語氣和表現,讓人有一種顫抖的感覺”,“純樸的友情再也找不回來了”。與之形成反差的便是“我”和鳥兒之間殘存的情感,“我”和鳥兒之間的情感沒有性別和年齡隔閡,雙方特別信任和認可,這種情感被稱為混情,在這個不認親情,不談愛情的,不交友情的經濟亂世,混情顯得彌足珍貴。千夫長在這個無情的世道為讀者殘存了這點人類情感既是其自身的情感寄托,也是其對世人不失本心的殷切期望。
作品中汗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他對生命沒有敬畏之心,憑借自己的科學技術肆意踐踏生命。在他身上,讀者看到的是人心扭曲表態的禽獸。但作者并沒有一棍將其打死,也許并不是其不能,而是其不愿意,他不愿意讓讀者陷入無盡的黑暗和無望之中,他要給讀者存留一絲光亮。“我”得知鳥兒和巴根被汗變形成羔羊和馬后,感覺自己的境遇也即將和他們一樣。“我想汗一會就把我變成一只羔羊、一匹馬或其他什么動物了。”但最后的結局是汗沒有這樣做,他放過了我,沒有將我變形。我很驚愕,詢問汗為什么這么做,汗的回答是“我不會把你變成羔羊的,你是我的兄弟”。至此,讀者才似乎在汗的身上感受到了作為人的溫良。
文學是人學,文學家應是社會的締造者,是社會主流思想的表現者,探索者,引領者,因為真正的文化道德或者說文學道德是存在于廣大人民群眾當中的,作家們開拓發掘并把它表現出來,這就是作家的責任。千夫長在《汗的羔羊》中以細膩的筆觸展現了社會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以強烈的責任感進行寫作,敢于說真話,敢于揭露社會、批判現實,這是一個作家最為寶貴的文學情懷。正如他的《紅馬》一樣,他是我們靈魂深處的紅馬,在他的靈魂深處,仍躁動一個文人的使命,正是這種使命驅使他在作品中訴求人心的歸位、人心的向善,而這也正是文學的旨歸所在。
[1] 白巖松.幸福了嗎.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
[2] 千夫長.汗的羔羊[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3(12).
[3] 崔殊.靈魂的高度——讀千夫長的小說《紅馬》[J].CHINA PUBLISHING JOURNAL,2003(3):60.
[4] 李緋.靈魂在高處看著我——訪著名作家千夫長[J].新青年,2003.8:42、44.
潘佳麗(1990.2-),女,漢族,江西宜春人,學生,文藝學碩士,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文學理論與批評。
U279.3
A
1672-5832(2016)10-002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