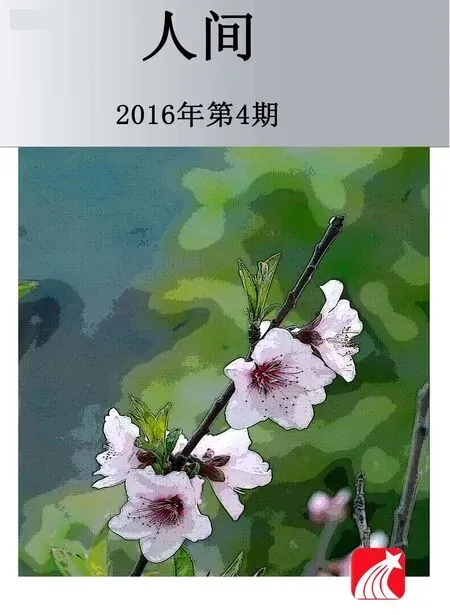關于影片《奇遇》反映出的現代性的思考
李思遠(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重慶 400044)
?
關于影片《奇遇》反映出的現代性的思考
李思遠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重慶 400044)
摘要:影片《奇遇》作為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的代表作之一,在歐洲藝術電影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影片所展現出的對于傳統敘事的顛覆,對于人物關系的凝視和追問,都展現出影片區別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走向新的藝術創作領域的傾向。《奇遇》這部影片展現出十分明顯的現代主義電影的特質。本文將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影片《奇遇》所表現出來的現代電影的諸多特征,以及現代主義框架下的作為一種工具的“電影”的意義。
關鍵詞:安東尼奧;敘事;歐洲藝術電影;現代性
一、《奇遇》作為現代電影的敘事表達
影片的開始,似乎是一個帶有希區柯克式的偵探片的樣式。看似作為影片敘事中心的安娜莫名失蹤了,按照舊有的邏輯,安娜的去向應該就是整部影片敘事的結點,也應該是影片情節發展的最主要的推動力。但是當影片過半,隨著男女主人公突然跨越心里障礙走到一起以后,安娜作為情節發展的動力從影片中消失了,男女主人公的行動與電影的前半部分相比不再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正因為這樣,影片的后半部分,特別是克勞迪婭,表現出一種茫然和不知所措,盡管她與桑德羅的愛情看上去似乎已經水到渠成,觀眾也逐漸適應安娜已經消失(或者說安娜被觀眾遺忘在劇情中),但失去目標之后,劇中人物同觀眾一樣,都不知道接下來需要做什么,或者會發生什么。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無形的焦慮和壓迫感。
這樣的敘事方式顯然是不同于我們習慣的故事模式的,但是它卻代表了一種藝術電影的敘事方法:
藝術電影不受因果敘事策略的主宰,情節提供的故事關系多半是不和諧的、混淆的,而不是解釋清楚的;人物并不是特別主動,往往是情節分配了很長的影片時間給一些場景,但故事卻少有進展;往往規避那種閉合式的結局,反而偏愛未決未定之感。①
導演安東尼奧尼植根的土壤便是歐洲藝術電影,在此基礎之上,得出的名為《奇遇》的果實依舊延續了藝術電影在敘事和拍攝技法上的實驗和嘗試。
安東尼奧尼在《奇遇》一片中試圖將他認為不重要的情節省略,然而這些“不重要”的情節恰恰是傳統敘事的一般邏輯。反之被展現的更多的是安娜失蹤的小島,空無一人的城市和街道廣場等景物,人物被放置在被高樓或峭壁擠壓的空間中游蕩,不管是劇中人物還是銀幕前的觀眾都不能獲得關于傳統意義上“故事”發展的任何有效線索,我們姑且把他當做一種藝術手法上的實驗,但是創作者真正想要傳達的確是這樣的空間中人物的狀態以及情感。
反傳統的敘事不僅僅是導演的實驗性嘗試,這樣的敘事方式所呈現出來的破碎的故事和焦慮的情緒才是《奇遇》在國際上備受關注的原因。非常規的敘事方式沒有將觀眾“縫合”進完美的故事世界里,相反,它用時時刻刻跳脫地,不連貫的故事,將觀眾推出故事的情節和人物的情感之外。安東尼奧尼通過《奇遇》呈現出來的狀態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卻恰恰是生活本來的樣子。克勞迪婭和桑德羅沒有傳奇的相識,沒有凄美的相愛,更沒有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安娜作為這個故事的開端在影片中段消失在敘事中,但卻以一種道德枷鎖和焦慮的方式存在在克勞迪婭和桑德拉的愛情上空,就如影片中大量的陰影一樣。安東尼奧尼承襲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以來的客觀的鏡頭和人物與空間的關系,但卻符合一般現實邏輯的故事省略,只留下人物的內心狀態,并將這些狀態外化為空曠的街道和壓抑的構圖。以此來表達人物如何在空間中生存,情感如何在空間中發酵或枯萎。
二、《奇遇》中的溝通問題
如果說影片《奇遇》的敘事方式,使得焦慮和迷茫的情緒躍然紙上,那么影片中人物關系的處理和設置,就極為鮮明的指出了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失效和生活中那些含糊不清的存在。
首先是影片中主要人物之間的溝通問題,安娜作為整部影片的一個引子,她的失蹤,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她與男主人公桑德羅之間情感的不順暢。所謂“鯊魚”的出現,表面上看似乎是安娜的一個惡作劇,但對于安娜來說,預感到長期分居即將要消失的情感上的焦慮便是她的鯊魚,無處不在。(在這之后,安娜便成為克勞迪婭與桑德羅感情之間兇惡的鯊魚,成為克勞迪婭的噩夢。)桑德羅并不理解安娜不安的原因,很明顯,桑德羅也并不想理解,甚至在安娜失蹤以后,桑德羅還是認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爭吵。這樣的障礙并不是有意為之的,雙方都不明白為什么對方不能理解自己的感受,也不能通過話語有效的讓對方感知,這種天然的,存在在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溝通障礙是無解的,因此安娜消失了。
在她消失后,同樣的問題被克勞迪婭繼承,在影片中集中的表現在火車上克勞迪婭和桑德羅的對話中。克勞迪婭漸漸被桑德羅吸引,但卻越來越痛苦,桑德羅依然不能理解她的焦慮不安,他只對自己的“一見鐘情”感興趣。影片中的人物在表達內心困苦的時候常常背對鏡頭,這樣拒絕直接交流的方式給觀眾感知角色的情緒設置障礙,劇中人物在少有的傾訴時也常常相互背對著,比如安娜在船上對克勞迪婭坦誠鯊魚是假的時,兩人都背對著鏡頭面對著墻壁進行交流,而不是選擇采用面對面的方式。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痛苦源自于交流和溝通的無效,沒有人試圖去解決溝通的問題,只是不斷的向他人闡述自身的痛苦。
三、看似無關緊要的人
很有意思的是,影片省略了許多推動故事發展的情節,卻也增加了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和對話,在這里有三個例子,但是恰恰是這些例子,補充了情節留下的空白,更加直白的表達出創作者想要表達的關于人的社會的本來樣子。
第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便是小島上的牧羊人。他的出現為人與人之間不對等的對話提供了范本,還有就是人下意識對自我的關注:牧羊人是個局外人,他根本不關心安娜是誰。其實不僅僅是他,所有的人在面對與己無關的人或事時都表現出相當的鎮定和冷漠,這也就是為什么克勞迪婭在牧羊人說安娜有可能從屋后掉落懸崖后表現出的悲傷會顯得很突兀,從這個角度出發,桑德羅的表現如同牧羊人一樣,像個事不關己的陌生人。這樣我們也能夠明白為什么克勞迪婭在這一階段表現的對桑德羅那么的不滿那么的憤怒。
第二個例子便是克勞迪婭和桑德羅在火車上。在尋找安娜的過程中,二人的感情逐漸發展,克勞迪婭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焦慮不斷上升,她試圖向桑德羅解釋為什么她不能就這樣接受桑德羅,但桑德羅并不能理解。克勞迪婭走出車廂,看到一對年輕的旅客在交談,男性旅客正在搭訕女乘客,這一段落的插入看上去很不協調,克勞迪婭的情緒被這一段分成兩半,但又是合理的,就像我們的生活中,悲傷和快樂也都不能一氣呵成,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隨心所欲的發泄自己的情緒。女性們對于愛情看得如此神圣和復雜,但無奈的是男性們更關注自身的狀態和自我的需求,因此男人和女人在這部影片中表現出的對立和溝通上的障礙那么明顯。
影片中第三個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人物就是一位裙子破掉的女明星。這是一位引發全城男性騷動的女明星。她的出現與整個影片的劇情沒有任何關系,但是她的存在,或者說她作為一個被所有男性“觀看”的存在,表達了《奇遇》這部影片中最根本的兩性關系。在影片在第100分鐘左右的時候,克勞迪婭和桑德羅在一起以后來到一家旅館尋找安娜的蹤跡,克勞迪婭在門外等候,此時的她變成周圍所有男性觀看的對象。
克里斯蒂安·麥茨在一篇名為《現代電影與敘事性》的文章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安東尼奧尼以及直接電影中的佼佼者的最大功績顯然是把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切失掉的涵義網羅到一種更精細的戲劇中。②
不管是牧羊人、火車上偶遇的年輕人,還是引發全城轟動的美女,他們或許與影片中的主要情節和人物關系不大,但這些關乎每個人生活的瞬間片段,卻從側面揭示出更為廣泛的涵義,這些涵義不僅針對電影中的克勞迪婭與桑德羅,也直指我們生活當中與之相似的片段和情感。
這些涵義并不是每一個都非常明確,它同我們的生活一樣,具有相當的模糊性,與傳統的以敘事為主的影片不同的是,安東尼奧尼并不致力于將故事講的完整清晰,他嘗試保留這些在生活中同樣具有模糊性的“涵義”:
其功績還在于善于保留那些含義,同時又不把它們有意堆砌在一起,也就是說,不剝奪它們閃爍不定的含糊性。如果沒有這種閃爍不定的含糊性,它們也就不再是失掉的涵義:既保留他們又未復現它們。③
在這里,麥茨反復強調了“失掉的涵義”,應該就是指在類似于好萊塢傳統劇作中嚴密的邏輯結構和緊張刺激的快節奏故事之外的生活的真實性,相對于《羅馬假日》等經典愛情片中的才子佳人,克勞迪婭和桑德羅之間的悲歡似乎才更貼近我們生活中喜怒,以及人類在情感上的彷徨和復雜性。吸取了歐洲藝術電影的養分,安東尼奧尼接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接力棒,卻將電影引向了新的領域:
在他創作生涯的最初十年,他促使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轉向私密的心里分析,形成了一種嚴肅的、反情節劇的風格。④
這些看似與影片整體敘事并不相關的橋段恰恰構成了《奇遇》這部影片作為一部現代電影的特征。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底層真實的生活狀況已經不再是安東尼奧尼所想要表達的重點,他更關注在這樣的環境和狀況下人的改變。《奇遇》只是一個開始,隨后的《夜》、《紅色沙漠》等影片都采用了極富現代性特征的敘事手法,展現出被困在既有的生存環境中的人的變化,包括外部的形態,更重要的是人的情感變化。
四、關于現代性電影
現代主義的概念在電影發展的過程中并不好界定,它沒有一個明確的開端,在后現代主義開始興盛以后,它也沒有完全被取代,現代主義的興起于大眾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而電影的現代性問題與作者論的研究形影相隨。安東尼奧尼作為電影作者中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電影不可避免的被拿來放置于現代性的框架下研究。
在《電影研究關鍵詞》一書中對于現代主義有著比較復雜的解釋,其中一段是:
現代主義的重要面向是滲透于這場運動的異化情緒和存在主義的焦慮,它根源于兩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的悲觀主義思想。異化情緒產生于一種在社會場域中自我分裂的感知,以及相隨而來的無法有效和他人溝通。反過來,自我分裂提出了身份問題:“蕓蕓眾生中,我是誰?”……現代主義再度表現出高度的自反性。⑤
這一段解釋很明確的指出了關于現代主義電影的一些明顯特種證:對于異化情緒的關注和對于存在主義的焦慮;對于無效溝通的探討和高度的自反性。顯然,這些特質讓我們能夠更加合理的解釋《奇遇》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思考。
影片結局的處理非常明顯的表達出《奇遇》作為一部現代性質電影的特質,桑德羅的出軌成為這段本來就帶給克勞迪婭焦慮和道德上不安的愛情的一個歸宿,影片的結尾克勞迪婭和桑德羅背對著鏡頭,在只有一半天空的鏡頭中哭泣,這樣的結尾沒有解決任何故事中留下的問題,比如安娜的去向,克勞迪婭和桑德羅最終會怎樣等等,但卻提供給觀眾一個思考的場域,和對生活的反思。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電影的場景和敘事經過變成了一個場所,用來收納現代社會被忽略的那些“失掉的涵義”,也用來重新建構人類自身的意義和價值。電影本身不僅僅是一個講故事的工具,同時也是一個審視自我表達不安情緒的途徑。
在安東尼奧尼的創作中,“電影”有了新的身份和價值,這不單是安東尼尼奧尼一個人的功績,這里包含了現代主義作者導演以及先鋒派和實驗派作者導演們的無數嘗試和努力,而安東尼奧尼在這其中無疑是佼佼者。《奇遇》的價值也不單單是一部新穎難懂的實驗性嘗試,更是一個表達創作者對于當下社會中人的狀態的一種思考途徑和探討空間。
參考文獻:
[1]《世界電影史》(第二版),[美]大衛·波德維爾 克里斯汀·湯普森著 范倍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電影理論讀本》楊遠嬰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2012年1月第一版
[3]《電影研究關鍵詞》[英]蘇珊·海沃德 著 鄒贊/孫柏/李玥陽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4]《電影研究導論》,(英)吉爾·內爾姆斯(Bill Nichols)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11月第1版
[5]虞吉、何曉燕,霧與影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世界[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7,05:11-15.
[6]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一次訪談[J].世界電影,1999,01:241-249.
[7]關雅荻.自我的消失:對安東尼奧尼兩部作品的分析[J].當代電影,2004,06:94-98.
[8]杰弗里·諾威爾—史密斯 ,郝大錚.安東尼奧尼:三部曲[J].當代電影,1987,01:116-122.
[9]Jackie.窺視安東尼奧尼的《奇遇》[J].電影文學,2004,07:61+60.
注釋:
①《電影研究導論》(英)吉爾·內爾姆斯(Bill Nichols)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11月第1版,P83、84。
②《電影理論讀本》楊遠嬰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2012 年1月第一版P281頁。
③《電影理論讀本》楊遠嬰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2012 年1月第一版P281頁。
④《世界電影史》(第二版),[美]大衛·波德維爾 克里斯汀·湯普森著 范倍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⑤《電影研究關鍵詞》[英]蘇珊·海沃德 著 鄒贊/孫柏/李玥陽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P311頁。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2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