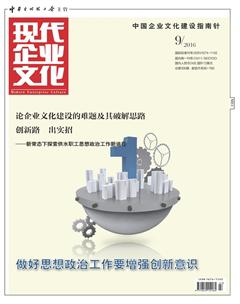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中的文化內應力研究
王一諾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1145(2016)09-000-03
摘 要 家族企業的文化問題,是相關領域研究的重點課題。在當前“企業文化管理”向“企業文化治理”轉型的環境下,更是增添了企業在理解與執行層面上的歧解性。為此,本文嘗試提出文化內應力的概念,論證文化內應力在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中的表現特征及其應用,并以案例分析形式指出文化內應力是企業生命力的出發點,也是現代企業經營的客觀要求;它不僅具有文化邏輯的內容,還具有作為管理手段的內涵。本文認為,文化內應力的內部差異會導致企業截然不同的發展狀態與結果,它已經成為決定企業發展空間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 家族企業 傳承 轉型 文化內應力
引言
文化與管理的關系及作用,在管理學中歷來不乏諸多的論述。家族企業作為企業中的一種組織形式,由于其特有的“家文化”背景,使其成為企業文化研究中的重點領域。它一方面使家族企業具有著天然的文化依附性,并成為傳統文化路徑依賴下的一個必然選擇(趙紅梅,2003);另一方面也使家族企業的文化建設處在一種若隱若現或單一固化的境地之中。尤其當“文化管理”這一術語躍升為“文化治理”時,更是增添了企業在理解與執行層面上的歧解性。
現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文化因素在家族企業治理結構、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中的重要性、開放性和局限性,并與日本、德國等家族企業文化進行比較,這無疑豐富了我國家族企業研究,并對其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和現實借鑒意義(郭躍進,2003;楊玉秀,2011;馮建平,2012;劉森林,2015,等)。還有研究者從系統論和演化角度提出,文化因素作為家族企業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必然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并具有復雜性和自組織的演化特征。因此,家族企業文化的研究,不能過多地停留在某一時點的階段性分析上,即靜態視角研究,而應考慮企業文化的系統觀,考察并分析整個企業文化產生、發展的動態過程(甘德安,2010)。
針對以上情況,本文嘗試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深入挖掘和總結文化在家族企業治理中的實踐意義,分析文化因素在家族企業結構中的開放性、局限性及其張力。同時,通過提出并研究“文化內應力”概念,從文化根基上夯實家族企業轉型發展與代際傳承中的思想基礎,嘗試不同以往從經濟學和管理學角度來論證家族企業治理模式與興衰問題的常規研究范式。
二、“文化內應力”概念的提出與作用
文化內應力是由“文化”與“內應力”兩個核心詞構成。其中,內應力(interior stress)原是材料力學的專用名詞,它指當外部荷載去掉以后,仍殘存于物體內部的應力。文化內應力(Culture interior stress)借鑒了相關構詞思想,它指的是關于企業自身價值觀、信念、工具和語言的一種發展內部驅動的力量。
文化內應力是企業文化范疇里概括力較強的一個概念。它出現的背景即是家族企業面臨延續困境,家族企業文化的負面作用日益凸顯,并亟需創新家族企業文化才能既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又能保證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內應力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文化內應力是家族企業運轉正常的“潤滑劑”,用來表示企業內部管理存在著明顯的文化促進因子。它能潤滑或磨平家長文化的殘余之物,使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關系順暢無阻滯,工作氛圍愉悅無壓抑,工作指令落實到位無抵觸。
第二,文化內應力是家族企業使用方便的“工具箱”,指家族企業在經由他人力量完成工作時所不可或缺的稱手。文化內應力不是企業的副產品,而是企業的正產品。它不是體現雞肋性質的軟性工具,而是體現聚財性質的硬性工具。
第三,文化內應力是家族企業和諧團結的“聚光燈”。“聚光燈”的概念結合了兩個相關的主體:家族與企業。這一方面體現了家族的利益與感情,也體現了企業的發展與利益。進一步說,文化內應力在感性與理性、眼前與長遠、股東與職業經理人間發揮著一種平衡的力量。
三、家族企業中“文化內應力”的內部結構
文化內應力就是闡釋圍繞經濟組織內外部產生的文化現象,既包括企業管理主體意識的系統,又囊括企業實踐行為的集合,既體現企業主及繼任者的領導力,也體現組織成員全員參與的回應力,這也構成了文化內應力的四維特征。
四維特征之一:文化人格的主導性。這就是企業文化的基因。如果以生物遺傳學“基因”概念來解釋家族企業的生成形態的話,可以認為企業基因是決定企業生成形態與成長過程的內在的根本因素。而企業基因的核心是創業者的DNA,即創業者的DNA決定了企業戰略、行為與結果,也決定了企業的核心價值觀。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說:“一切文化將最終積淀為人格”。也就是說,企業主及繼任者的文化背景、知識結構、性格特征、做事方式等文化人格,深刻決定著家族企業的發展方向及前途命運。這在家族企業代際傳承和轉型發展中顯然表現得更為直接,甚至可以稱之為文化基因。
案例1:中國東星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星集團)曾經是一家集航空、餐飲、住宿、旅游等為一體的超大集團。2005年因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籌建而名聲大噪,然五年后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已不見蹤跡,并演繹了一場從狂妄自大到銷聲匿跡的造神運動,其創辦者也經歷了一場由“從天庭俯視世界”最后卻通往“地獄”的旅程。其間,企業主的性格表現,不能不說是導致這場造神運動,并連帶東星集團失敗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因。李秉成、朱慧穎(2012)曾詳細分析了東星集團企業總裁的過度自信膨脹與企業價值和企業財務困境間的邏輯關系和影響機理。甘德安(2015)也以東星航空破產事件為例提出創業者基因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與傳承的觀點。
四維特征之二:義務跨域的平衡性。在家企同構的架構下,家族企業所包含的情感成份顯然要高出或濃烈于其他企業許多。家族情感顯然成為了家族企業建立、維持和發展內外部關系的一種媒介,包括“有義務的給予——有義務的接受——有義務的回報”的人情粘連性過程。而這必然導致企業核心人員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融為一體,并成為跨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模糊者,筆者稱其為“義務跨域”。尤其在家族企業代際傳承過程中,第一代管理者會不可避免地將私人領域的“家文化”與企業公共事務牽連起來。兩者如何有效的平衡、互融、傳承,管理者的文化人格自然起了決定性的主導作用。
案例2:德國漢高與傻子瓜子。有學者以德國漢高百年成功傳承為例提出,中國家族企業傳承困境之本質在于缺乏愛的傳承,并認為富二代接班不僅是血緣的延續、財富的承接、更是愛的傳遞。愛的傳遞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特別在孩子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刻,創業者要到位、要跟進,做有責任,懂得愛、可信任的多向度的人,但我們的創一代很少能做到。傻子瓜子創辦人年廣久雖曾被鄧小平三次提及,以肯定其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但從年廣久的婚姻、家庭與家族企業傳承看,其所呈現的則是家不穩(四次婚姻)、父子關系不順(對簿公堂),兄弟不恭。顯然,年廣久的“家”早已變形,“家文化”幾經斷裂,甚或早已丟失,不復存在。可見,在家族企業傳承過程中,創一代、富二代均要接受愛的教育,因為愛的教育和傳承連接并關系著家族私人領域與企業公共領域的長遠發展。
四維特征之三:利益主體的博弈性。這主要指在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兩位主體以至多位主體之間的博弈。其中,企業內部的博弈主要是兩代人間的代際博弈。
案例3:方太傳承中的代際博弈。寧波方太廚具有限公司是生產吸油煙機的企業(下文簡稱方太)。有關方太企業的關注和研究主要集中于茅氏家族在代際傳承中沒有延襲傳統主流的“子承父業”的應對模式,而是采取了共同創業的傳承模式。這正如茅理祥所說:“交接班的過程是企業變革的過程,是企業二代建立自己管理思想的過程”,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最佳時機。”
四維特征之四:權力差距的彌合性。企業內擔當職務的不同,則意味著掌握權力大小的不同,以此形成了權力差距。處于權力頂層的人,強調強制力和指示性權力,而處于權力底層的人則看重權力的運用是否合法、合理、合情,即重視合法性權力。在家族企業內,體現更多的是權力差距的支配性,而非彌合性。而家族企業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填補彌合性這一短板上。或者說,權力差距的彌合性,其實指向了一種共享經濟結構,也指明了一種發展趨勢。
案例4:國美電器轉型之困。2009-2010年的國美電器集團之爭表面上看是創始人黃光裕與職業經理人陳曉間的利益之爭,實質上是傳統家族企業治理模式與現代企業治理模式之爭,更觸及對傳統家族式管理思維、模式、問題,以及人的現代性問題的追問與反思。2015年初,國美采用了“蜂巢式變革”的模式,支持小團隊孵化項目,鼓勵每一個員工都開設微店,這是對家族企業權力差距的一個有效彌合,尤其顛覆了家族企業的封建家長制思維與職業經理人的家丁思維。可以說,家族企業轉型之困不僅是治理結構之困,創業者與職業經理人博弈之困,也不僅是傳統電商向互聯網+的電子商務的轉型之困,還是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企業員工向現代化的人的轉型之困。
綜上所述,“文化內應力”的四維特征和結構關系如下圖1所示:
四、“文化內應力”在家族企業傳承和轉型中的應用
囿于篇幅,這里僅提供一種框架性的應用或規則性的把握。
(一)感性和理性、情商和智商的平衡
人的理性與感性本應均衡搭配、平衡發展。但在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中,家族往往會偏于感性,而企業會偏向理性,由此出現了此高彼低、搭配不均的情況。這同時也考驗著企業創辦者的智商和情商。
案例5:鷹鳥紛爭。某湖北一家在北京開創了“九頭鳥酒家”,飯店生意大火,后因家庭內部紛爭和經營理念不同,分道揚鑣,各起爐灶,并引發了商標之爭。新招牌為“九頭鷹酒家”,言外之意是要鷹吃鳥,但分家后的兩個企業的規模和效益都大不如前。同時,原飯店內部人又創建了“九頭鳳酒家”,“九頭鳥”一分為三,這些雖經法律程序最終解決,但“九頭鳥”的聲譽和發展在京城餐飲業至此一蹶不振。
可見,在家族企業治理、傳承和轉型上,家族感性與企業理性是一對相生相長的矛盾體,不乏相互沖突碰撞的例子,如何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無疑考驗著創辦者的文化人格和辯證思維能力。
(二)謀勢布局的戰略運籌
企業謀勢布局的戰略重點,不僅要關注企業內部的產權和治理,更要關注企業外部的產業發展和全球化進程。
案例6:當1956年5月小沃森接過IBM家族企業的權杖時,就進行了一個偉大的布局。如果老沃森代表IBM機械時代的話,那么小沃森就代表了IBM一個新的時代,即IBM將從機械時代走向電子時代。1956年底,小沃森召開了高層經理會議,制定了著名的威廉斯堡計劃,決定投資發展計算機。小沃森最終成了這場賭局的贏家——1964年4月7日,“IBM 360系統”橫空出世。正如IBM公司的廣告詞一樣:“無論是一小步,還是一大步,都是帶動人類前進的腳步。”可見,“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功,也考量著企業決策者謀而后動的眼界、敏銳與膽量。
(三)品牌形象的正向塑造
品牌形象是家族企業的“顏值”和重要資產,是企業品牌、產品品牌、團隊品牌與個人品牌的協同與總合。
目前,中國家族企業在產品研發和品牌建設的理解和實踐上,還處于初級階段。大量基于仿效而問世的“中國制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人善模仿、喜跟風的文化心理。這種“山寨”之風是企業飲鴆止渴的投機行為,而這種停留于短期“山寨”行為層面的企業永遠成長不起來,這已被大量事實所驗證。
案例7 前述方太企業的新產品品牌“方太”,意為“方便太太”,因為吸油煙機是廚房電器,廚房多由太太打理。“方太”一名則指向精準且具親和力。其廣告語“方太,讓家的感覺更好”,明了上口,具有傳播效應,并達到了企業、產品、品牌的有機統一。可見,家族企業品牌形象的建設,不僅賦予了企業新的產品品牌,也體現了繼任者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和市場開拓力。
(四)仁心善行的統領
在傳統觀念中,商人似乎是善人的絕緣體,所謂“無商不奸”。然而,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企業的仁心善行不僅僅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強大營銷工具,還應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項常規。從中國傳統士大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可知,中國人本就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文化基因。因此,仁心善行不僅僅是一個道德選項,而是一個統領著企業發展方向的文化利器。
案例8“李錦記”的第一次出現,是在1888年的廣東省南水縣一個名叫李錦裳的自家店鋪上。在“李錦記”百年發展史中所提煉出來的“思利及人”的治家和經商信條,反映了其對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一個清醒認識和初級表達。家族第四代又進一步將“思利及人”解讀為“換位思考”“關注對方感受”和“直升機思維”(承擔家族、企業和社會責任)三個要點。新加坡萬邦集團主席曹慰德也曾以自己家族的成長歷史為例說明:真正的家族企業是希望世代延續下去的企業,他們所持的觀念必須是持續發展的,而持續發展就離不開責任感。他認為,家族企業超越家族本身承擔社會的責任是家族企業延續發展的應盡之義。這也是企業家由“經濟人”向“社會人”“道德人”超凡境界轉變的一個必經修煉。
五、結語
本文認為,在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的進程中,文化智慧的精粹不應當缺席,并須以此為樞要來治理。文化內應力是企業生命力的出發點,也是企業理念客觀存在的必然;它不僅具有文化邏輯的內容,還具有作為管理手段的內涵。企業文化內應力需以企業日久天長的文化治理為基礎,這即是文化內應力及其應用的全部意義。
該文是武漢研究院《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關系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趙紅梅.家族企業的文化解析和發展思路[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3(9).
[2] 甘德安.復雜性家族企業演化理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3] 甘德安.家族企業復雜性理論深化研究[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4] 李秉成,朱慧穎.管理者過度自信、企業價值與企業財務困境的關系——基于東星集團的案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2012(5).
[5] 甘德安.創業者基因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與傳承——從東星航空的破產談起[J].中國慈善家,2015(12).
[6] 余向前.家族企業代際傳承與制度創新[J].學術月刊,2007(5).
[7] 甘德安.從方太傳承看兩代人之間的博弈雙贏[J].中國慈善家,2015(6).
[8] 張正良.方太父子間的另類傳承[J].企業觀察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