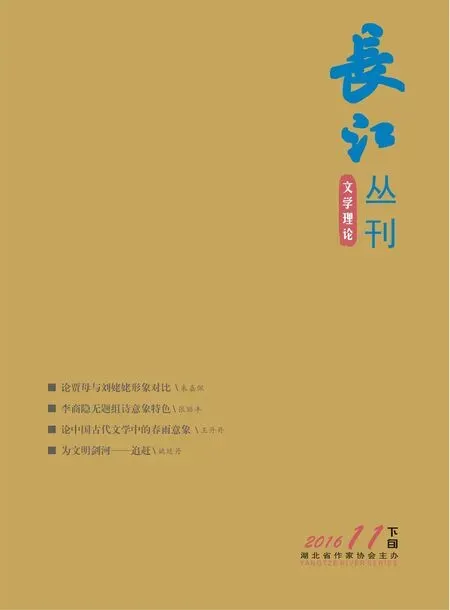邊緣視角下的華夏構建詮釋——讀王明珂《華夏邊緣》
李瑞峰
邊緣視角下的華夏構建詮釋——讀王明珂《華夏邊緣》
李瑞峰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一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該書在臺灣允晨1997年版、大陸社科文獻2006年版基礎上,除了少量文字修改外,對于本書主旨、觀點均無明確修改。因此,該書可以直觀反映王明珂先生所提而趨成熟的“華夏邊緣”理論。通過對該書整體的梳理整合,以此來探討王明珂先生對于“華夏族群”形成的研究與思考,以期能更深的理解這一族群詮釋理論,對華夏族群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并對其近代變遷有所反思。
《華夏邊緣》 王明珂 華夏族群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以下簡稱《華夏邊緣》)是一本主要研究“華夏邊緣”來探討華夏族群形成變遷歷史的著作,由在歷史人類學領域成就卓著的王明珂先生所著。王先生多年從事羌族、西南少數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會的田野調查研究,故而使得該書的寫作理論豐富,方法充足,不僅應用歷史學文獻法,還應用人類學族群理論和社會學社會記憶理論,以及考古學理論知識。多學科融合交叉的寫作方法和視角也使得該書說服力充分。這本書不同于以往以核心內涵來詮釋華夏族群的方法,而是從華夏邊緣這一獨特視角入手,通過探討分析華夏邊緣形成邊緣的過程,來反映華夏族群的變遷。該書開創了新的華夏族群形成變遷方法,出版后獲得較大的反響。因此,該書有著較高的學術價值。
通過對這本著作的閱讀,對書中的方法和思想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理解;因此我將以讀書報告的形式,對該書做一介紹。首先,對于《華夏邊緣》這本書做一內容的梗概介紹;其次,將對本書做一些簡要評價,作為對該書的一些理解和思考。最后,將結合對于本書知識及其理論框架體系的理解,對本書中最為啟發的社會記憶與歷史事實的話題,談談自己看法。
一、內容摘要
本書共分四部分,即《邊緣與內涵》、《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二、本書內容評析
首先,我將對本書主要內容做一簡要介紹,談談本書的理論方法貢獻。
第一,提出民族研究的新理論與新方法。以往的民族研究多采用一種典范觀點來描述一民族“核心內涵”,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逐漸反思這種漸生流弊的研究方法,意圖展示“真實”的歷史過程,從而推動了民族史研究由核心內涵到邊緣的轉移,由“事實”轉移到“情境”,由識別、描述“他們是誰”轉移為詮釋、理解“他們為何宣稱自己是誰 ”。這標示著對以往理論方法的突破。王明珂先生以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和社會記憶理論,對以往界定族群的客觀特征論提出質疑和反駁;最后,王先生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 “族群邊緣研究”的觀點,他說到“當我們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個圓時,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便是畫出一個圓的邊緣線條。在這圓圈之內,無論如何涂鴉,都改變不了這是一個圓圈的事實”。所以,族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
第二,王明柯先生以豐富的考古學資料,駁斥之前諸多考古學說法,將族群的認同劃分解釋為氣候變化的緣故。站在考古學的角度系統分析考察青海河湟地區、鄂爾多斯及其臨近地區、西遼河地區這三個地區之考古遺存。王先生以為,這三地區人們生活方式的游牧化,是其人類生態會對細微的環境變化所做出的反應,說明了其游牧化是生存的必然選擇結果,此轉變進而導致地區人類生態體系的社會組織與意識形態跟黃河中游中原地區農業定居生活的人們漸行漸遠,這對華夏的中原而言意味著“邊緣”在各方向邊界的形成,這個漸進的過程大約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成為極力維護自身族群邊界,以保護共同資源的人群,與北方游牧人群的互動化接觸,又進一步促使華夏鞏固及擴張北方邊緣的政治軍事行動,華夏邊緣由此被具體化、政治化。
第三,王明珂先生考察了周人與戎人關系的變遷,和對比西周與戰國至漢時所留有關周的遺存,來說明周人的“華夏化”及其周邊戎狄的“邊緣化”過程;其次,更是以“太伯奔吳”傳說記載的解構和重構,來解釋邊緣人群的“華夏化歷程”,即以改變、創造新的集體祖源記憶達到認同變遷,已有集體失憶改變原有認同,新的集體記憶塑造新的凝聚意識;再次,以各時期文獻記錄中“羌”名詞的指定用意進行了辨析,指出“羌”地理人群概念是不斷隨著華夏的西擴過程而漂移的,華夏西部邊緣的最終確立也得之于所能到達的人類生態極限;至此,王明珂先生依據邊緣地區人類生態與社會組織,提出四種性質的“華夏邊緣”,并指出根據性質的不同,華夏對其有著不同的政治與軍事策略,并以對內的文化功能解釋了以往所忽略的“邊緣維持”功能。
第四,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王明珂先生舉出木桶的例子,形象解釋了歷史上華夏維持其邊緣的必要性動機。但隨著近代以來世界局勢的變動,傳統的華夏及其邊緣均受到沖擊,邊緣的再造就顯得極為必要,王先生以此介紹了此間的時代背景,并以“歷史語言研究所”黎光明、王元輝的川康民俗考察和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考察兩個早期田野考察活動為例,說明學術和學者在此變遷中所扮演角色;再則以王先生在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研究,對“華夏邊緣”的近代變遷有了更直觀認識理解,實際上王先生以為“近代國族構建”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在我看來《華夏邊緣》也存在一些小的疏忽,將在此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其一,本書理論方式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史研究思路,而是提出新的解釋角度。即人類生態的詮釋方法,把人類的歷史活動很大程度上歸于“資源競爭”。王銘銘就對此批評說,王明珂論述存在一個很大問題,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基礎上,表現出很強的物質主義傾向,采用“資源競爭”這樣說法,雖描述了人類生存發展歷程,但似未能充分說明歷史運動內在機制。
其二,巴菲爾德提出中原王朝和草原部落“帝國”共盛共衰的周期史,王銘銘則指出了在秦漢以后的中國,中國歷史表現為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力量相互消長拉鋸期,這都是對王明珂先生論點的有力補充。但也暴露出王先生另一個重要的視角的缺失,即他忽視了傳統華夷強調文化差別,并不以經濟關系或族群區分為重點。
三、啟發性思考:社會記憶與歷史事實
社會記憶由人群當代的經驗與過去的歷史、神話、傳說等構成,借由文獻、口述、行為儀式(各種慶典、紀念儀式與討論會)與形象化物體(如名人畫像、塑像,以及與某些記憶相關聯的地形、地貌等)為媒介,這些社會記憶在一個社會中保存、流傳。在一個社會中,社會記憶被不斷地集體創造、修正與遺忘。王明珂先生也正是通過這樣的理論觀點來質疑依靠傳統文獻與片面化考古資料進行歷史研究的方式。
事實上,一些西方史學家也多采用這樣的理論方法,通過盡可能的還原歷史記憶資料,來探尋歷史事實。比如何偉亞在其著作《英國的課業》一書中,試圖尋求一個不受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性約束而更接近歷史原狀的學術陳述,通過考察義和團運動歷史,就認為以往的西方社會通過記憶塑造的手段(如戰爭紀念碑、戰爭回憶錄),將在華與義和團所沖突的西方人銘記成為受害者和英雄,模糊了其侵略者的本質。柯文也在其著作《歷史三調》中表達了類似觀點,“我們用來解釋歷史的觀念,往往與直接創造歷史的人們的觀念有很大的差異,其結果是不可避免曲解了真實的歷史”。
不能否認的是,近年來在西方學術后現代主義學風影響下,以往的歷史書寫多被視為近代建構的產物從而加以解構再詮釋,從而否定了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本身,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歷史虛無主義”風潮的蔓延,這是值得警惕的。
[1]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李瑞峰(1992-),男,漢族,寧夏固原人,碩士研究生,寧夏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