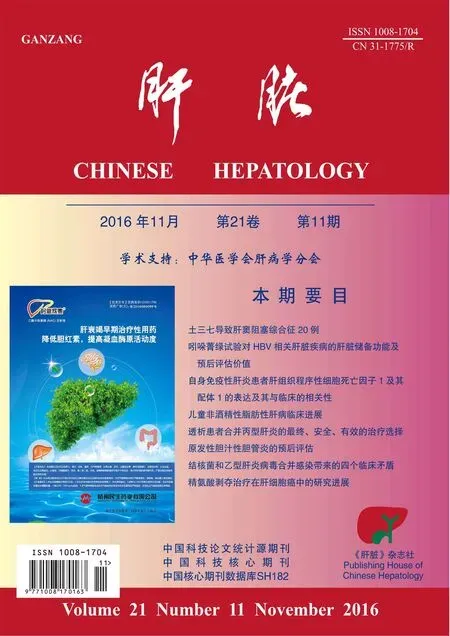166例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肝損傷患者臨床特征分析
朱飛燕 黃德東 莊建文 施潔 來(lái)曉維
?
·臨床與基礎(chǔ)研究·
166例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肝損傷患者臨床特征分析
朱飛燕 黃德東 莊建文 施潔 來(lái)曉維
目的 探討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藥物性肝損傷(DILI)的臨床特征。方法 回顧性分析我院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166例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DILI門診患者的性別、年齡、基礎(chǔ)疾病、肝功能、治療及預(yù)后等。結(jié)果 166例患者中男86例(51.8%)、女80例(48.2%),平均年齡(48.3±13.0) 歲。123例(74.1%)DILI 由抗風(fēng)濕藥物聯(lián)合應(yīng)用所致。DILI分型:肝細(xì)胞損傷型157例(94.6%)、膽汁淤積型7例(4.2%)、混合型2例(1.2%)。預(yù)后:治愈126例(75.9%)、好轉(zhuǎn)30例(18.1%)、無(wú)效10例(6.0%)。結(jié)論 抗風(fēng)濕藥物聯(lián)合應(yīng)用易致DILI,多數(shù)為肝細(xì)胞損傷型,經(jīng)治療多數(shù)預(yù)后較好。
肝炎,中毒性;藥物;抗風(fēng)濕藥物
藥物性肝損傷(DILI)是指使用藥物過(guò)程中,由藥物本身或其代謝產(chǎn)物引起的不同程度的肝臟損傷。隨著抗風(fēng)濕新藥的大量研發(fā),聯(lián)合用藥的增多,由抗風(fēng)濕藥物引發(fā)的肝損傷發(fā)生率逐年增高[1]。本文綜合分析了我院近3年來(lái)門診患者中發(fā)生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DILI的臨床資料,探討其臨床特征,為臨床醫(yī)生合理用藥提供依據(jù)。
資料和方法
一、資料
收集我院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166例抗風(fēng)濕藥物導(dǎo)致DILI門診患者的臨床資料。
二、方法
回顧性分析肝損傷患者DILI可疑誘發(fā)藥物、開(kāi)始用藥至出現(xiàn)肝損傷的時(shí)間、血常規(guī)、生化指標(biāo)、凝血酶原活動(dòng)度、病毒性肝炎病原學(xué)、自身免疫性肝病自身抗體、甲狀腺功能、腫瘤標(biāo)志物、銅鐵代謝標(biāo)志物及腹部B超等相關(guān)檢查。
三、DILI診斷標(biāo)準(zhǔn)
(一)參考2007年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制定的《急性藥物性肝損傷診治建議(草案)》[2]: (1)有明確的服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