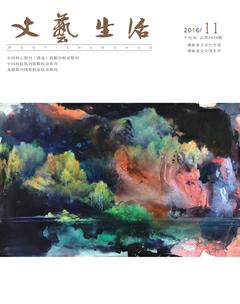平行的個體與垂直的世界
楊雅雯
摘 ? 要:《平行》這篇小說,以老教師短暫的游歷經歷為表象,以現代社會當中每個個體的碎片化生活以及個體與群體的關系為深層內涵,進行了一系列的描述和探討。
關鍵詞:現代性;碎片化;個人化
中圖分類號:I207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33-0010-01
弋舟于2015年第六期的《收獲》雜志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平行》,這個短篇,所講述和探討的究竟何在?是作家所強調的約束與自由?是評論家所強調的空巢老人?還是有其他的闡釋的可能性呢?
文章講述了一個退休的大學教師在罹患中風之后,在肉體收到了“老去”的信號之后在精神至上追尋著“老去”的意義的故事,在追問的過程中,他自己并不認同在身體上和物理上對“老去”這個詞所下的定義。于是他拜訪了曾經的老同事一位哲學教師,哲學教師通過一組數字給了他“老去”的涵義,而后,他又約會了前妻,前妻在從過去的故事當中給了他老去的涵義,在他因有老年癡呆被送入養老院的時候,同屋的老年人在老年的身體的展現上給了他“老去”的定義,而他在從養老院穿越了半個城市之后,在家中忽然發現終無可失去時獲得了精神上“老去”的定義。
原來老去是這么回事,作者在文章的結尾寫到:“如果幸運的話,你終將變成一只候鳥,與大地平行”而促使這些想法產生的原由就是他在公交車上欣賞著城市的變化和車外的景致,文中說道:“他在這陌生的、周而復始地運行當中猶如劃入了母親的產道,一次重生似乎就在不遠的地方等著他。回到家中,他覺得落日余暉下的防盜柵欄灑在木地板上的影子,像一只鳥巢。”
現代性的世界當中,片段化,流動性和中國明清小說的綴段性表現方式有著某種質的區別,從波德萊爾筆下的各種巴黎百態的人、事、物開始,現代性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生活的快節奏和明確的社會分工,使得碎片化場景普遍化,人被要求著每天大量重復著相似或相同的工作,工作的專業化和重復性使得碎片化的生活場景變得無趣且蒼白,工作之余,追問生活的意義以及追問其中的內涵,變成了現代人們的精神疑惑,究竟這個世界上自己被賦予了什么,而自己又賦予了這個世界什么。
在宏大的生活場景和歷史背景之下,意義是容易被賦予的,因為這種宏大往往是因為被賦予的某種意義而顯得宏大,更或者是因為某種意義而產生。宏大敘事在綴段性的敘事中是可能發生的,但在碎片化中是不復存在的,生活場景的平淡性和相似性使得現實主義的小說在廣度上受到了限制只能向深度進行探尋,越來越多的心理小說的出現,正是在與外界活動的蒼白貧乏和內心的活動的豐富多彩相對應。
現代性表述下的人的生活平行且獨立,但關于意義的渴求和解釋卻又各異。
這篇文章的平行是無處不在的,地理學教師,哲學家,前妻,小保姆,養老院的同屋老人,公務員的兒子和讀高中的孫女,故事在同一個平面化的時空當中發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軌跡和故事,地理學教師在妄圖尋找著某種精神上的探究時,從與這些人的平行空間變成了交叉的空間,在他罹患中風的同時,哲學家死了太太,并在面對他的精神性疑惑時,以數字的方式來表達著交叉時產生的抗議,前妻在離開他之后發生的際遇在幾十年后的重逢時才有了表達的可能,而小保姆生活本來與他有交集,但也是因為偶爾的平行,造成了他去養老院的結果,養老院的同屋老人與他雖同在一間房中,卻各活各的,沒有任何交流的可能,公務員兒子只有在他的需求之下,才從自己的世界當中與他的世界發生聯系,而讀高中孫女與他也只有每周電話上的交集。
人們滿足于這個獨立的世界,人們平行于彼此,卻無法逃離這個世界,于是他們與世界保持著垂直的狀態。
人與人是平行的生物,地理學教師的探尋,在交流當中開始出現了垂直,但卻無法打破這個平行。唯一的兩次關于平行的打破是強制性的集體生活的時期“下放時期”中地理學教師和哲學教師的辯論,以及他以為的在下放時期所蒙受的一切困厄用哲學分析“行之有效”這也促成了他詢問哲學老師關于老去意義的原由,另一段就是“養老院”生活這種他已經無法習慣甚至害怕的集體生活,整齊劃一與四列縱隊在地理學教師的心理已經“有悖于人的天性。”
作者自己博客當中強調著他所想表述的是一個中國人的困厄與自由的可能。他在最后講,人如候鳥般與世界平行而非垂直于世界。而事實上,我在文章看到了某種對現代性的悲觀態度,人們如此的形單影只,孤獨且彷徨,尋找著卻無所得,只有在瀕臨離世與苦苦追尋當中,才能脫離著這孤獨又平行的世界,這并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困厄與自由,平行、孤獨與追尋是世界人的困厄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