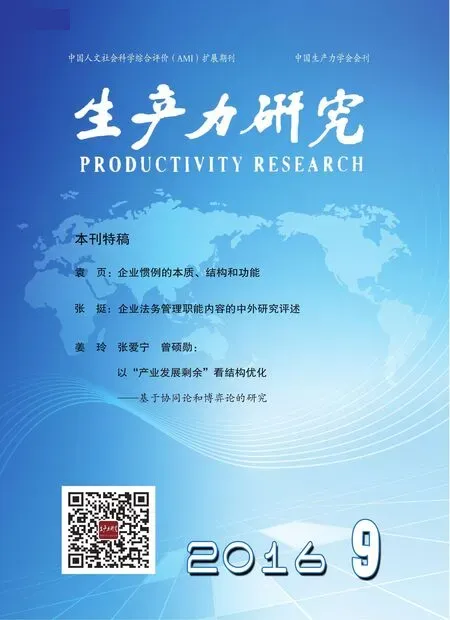飛利信并購影響企業績效研究
吳圓圓,于謙龍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飛利信并購影響企業績效研究
吳圓圓,于謙龍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文章通過對新時期高新技術類的上市公司和飛利信并購前后的財務數據為基礎作為樣本數據加以檢驗,利用因子分析法通過表現各項能力的指標對2011—2012年度期間發生并購行為的創業版上市公司和飛利信在并購前后的整體績效變化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分析發現,以現付和股權共同支付相結合的并購方式下其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行為使得公司在資產運作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有所提升且幅度較大,而償債能力明顯有所下滑,企業成長能力在短期內趨勢變化并不顯著。
企業并購;因子分析;上市公司;績效
一、引言
本文通過發生并購行為的上市公司在該行為發生的前后各報表期的經驗財務數據為基礎,通過選取創業板股(飛利信)作為案例的主分析對象,來分析以飛利信為代表的上市公司并購績效波動情況。創業板股多以高新技術產業類公司為主,與主類上市公司不同的是這些公司的特點相較于其來說上市政策更為寬松,操作更加靈活快捷。在日新月異的今天,科學技術仍是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北京飛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代碼300287)是一家典型的高新技術類的創業板上市公司。而國內的技術環境具有變化快、變化大、影響廣等不同的特點。目前飛利信無論是技術水平還是市場占有率方面在國內都處于上游地位。因此,在創業板上市公司中,選擇飛利信作為研究對象具有普遍性。通過研究這類公司與主板上市公司的不同之處,就能為此類創業板上市公司提供相對應的公司并購的建議,同時也為監管部門制定相關法律條例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現有理論與方法述評
(一)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在于以飛利信(A股代碼300287)為研究對象探究我國上市公司企業并購與公司績效的關系,以此更加有效的建立對上市公司是否能夠進行有效并購提高資本利用率的行為,使其行為符合所有者的目標,從而降低增需擴資的成本。
(二)文獻綜述
企業努力創造一個靈活的組織系統,因為它需要三個實現能力的發展:反應快、決策靈活、迅速調配資源。高新技術產業的收購可以進一步分離成產品收購,另一方面,也是教育,技術或人才收購。這些不同形式的收購可以增強戰略靈活性,如果管理得當,收購可以增強潛在的戰略靈活性的能力逐漸積累。企業并購和公司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并購(M&As)所表現出的復雜現象已經吸引了大量管理學科的巨大興趣。在戰略型和行為學的文獻中可以辨別出三個調查的主要數據流,他們都把目光聚焦在戰略配合、組織配合和收購過程本身的問題。近期每個調查的數據流的成果都被簡要評審過。然而,平行于這些研究的進展,并購的失敗率一直持續增高。對這種一分為二可能的原因進行了討論,反過來也強調了保持對未來并購研究的重要意義。Palepu(1986)[1]較早采用了多個會計指標以利用運籌學模型來預測目標企業有多大的比率被并購;Luann J Lynch(2002)[2]在“AnExamination of Pre-Merg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in Merging Firms”中通過實證分析指出了目標企業大小、成長性、績效、產業等互補結構在并購中的作用。此后,大量國內外學者開始對上市公司并購對于公司績效影響的研究。
Kitching(1994)[3]在他對歐洲收購的原創作品中顯示出了接近一半的失敗率。Agrawal and Jaffe(2000)[4],Saunders(1997)[5]也披露了并購會給收購方短期績效帶來明顯的改善。Jensen和Ruback(1983)[6],Loughran和 Vijh(1997)[7]等學者在其的著作中均表明并購重組能為并購方帶來比較豐厚的利潤。然而外國學者在使用會計指標研究法所得出的結論和關于并購的實證研究結論均與“并購重組能為并購方帶來比較豐厚的利潤”這一觀點相左,其中Moeller和Schlingemann(2004)[8]在其研究中發現,并購后收購公司和目標公司經營業績既未惡化也沒有得到預想中的改善。之后Finkelstein(2009)[9]在基于并購后的整合中也指出,并購方整體績效在短期內將有明顯改善。
國內學者在基于事件研究法的方法下其研究結論各執一詞,并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張新(2003)[10]、高雷和宋順林(2006)[11]的研究表明并購重組后出現了正向的累積超額收益率,而陳玉罡和李善民(2002)[12]卻得出了想反的研究結論。吉永峰(2014)[13]表明了技術并購是收購方企業獲取并購方核心技術的重要外部途徑之一。葛結根(2015)[14]在其選定的大量樣本研究中指出采用現金支付和股權支付結合的并購方式并購后績效會有明顯的改善。
從國內外學者對并購績效的研究來看,在選取事件研究法研究其績效變化趨勢時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調查的樣本數據且其實證研究往往并不盡如人意,而基于會計指標的研究方法雖然在可行性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研究高新技術類的上市公司并購績效中仍然可圈可點,且其研究大部分以行業或同類業務的眾多個體合并研究其變化趨勢,就個案而言代表性相對較弱。本文選取創業板高新技術產業的上市公司飛利信為研究對象,通過選取相應的會計比率指標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個案在并購前后短期內的績效變化。
三、研究設計
(一)影響企業并購的因素
陳昆玉(2006)[15]的研究表明兼并和收購可以創造價值的主要動機正在形成,通過協同效應的成果,通過提高市場力量或更換低效的管理團隊新實體經濟表現的改善表示。然而,現實表明,這些操作并不總是對的。劉磊(2004)[16]在其研究中指出企業并購是一種重要的投資活動,其動機主要是通過提高競爭力進而達到資本最大化的目標。然而對于獨個企業的并購行為來說,其并購動機、具體的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就飛利信而言,在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下,就并購行為產生的相應費用水平、企業成長性、企業規模和節稅等微觀因素來看,都同時作用于企業績效的變化。相關研究表明,后三者與企業并購績效呈不同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反之費用水平與績效呈相反的變動趨勢。那么,在企業為了獲取更多的戰略機會并且能夠在日新月異的當今社會最大限度的發揮并購的協同效應的計劃下,并購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的呢?
(二)因子分析法
王敏(2004)[17]在因子分析法在上市公司績效評價中的應用中指出因子分析主要是通過降維來解決自變量過多而造成分析困難不方便的問題。以飛利信一期并購前后相應數據進行分析,通過確定相應的指標以此觀察企業財力、經營力和資金流以及付現力在并購行為發生前后的波動范圍,確定績效波動走勢。
四、案例分析
(一)樣本數據指標的確定
研究選取2011—2012年滬深上市公司典型的并購事件剔除與飛利信業務范圍相差較大的并購事件后的并購公司在并購行為發生前后各期的相應數據為基礎,按照科學性、系統性、重點性、可表性和可用性等原則選取了表1中的數據,對企業并購績效的變動情況進行分析,樣本中所使用的相應財務比率數據源自國泰安和同花順。以飛利信2014年一期并購前后財務報表數據為基礎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幾個財務指標進行了因子分析。田磊(2013)[18]在飛利信收購資產資不抵債存疑中指出飛利信于2014年第三季度末收購東藍數碼和天云科技全部股權,飛利信并購前業務比較單一,通過技術性并購行為,實現了進軍智慧城市和數維系統的業務布局。考慮到指標定義的可變換性本文選取表1所示的分析指標。這些指標可以從企業的相應能力等各方面反映飛利信并購的績效,李蕾、宋志國(2009)[19]。

表1 綜合指標體系表
(二)建立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的因子分析模型
采用因子分析法用SPSS軟件經過可行性檢驗、有效性檢驗、主成分提取因子后將提取的三個主因子旋轉得到三個主因子的得分系數,根據主因子得分系數表得出各因子得分函數和各年綜合得分函數,劉芊、藍國賑(2008)[20]在基于SPSS軟件的因子分析法及實證分析中指出SPSS能夠根據各因子得分系數表和原始變量數據,自動生成各因子的綜合得分,根據綜合得分函數和各因子得分,進而計算得到各公司的綜合得分,再將得到的綜合得分輸入SPSS中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可得到不同并購方式的并購績效在并購前后各期的綜合得分及排名。

表2 得分情況表
(三)建立飛利信并購的因子分析模型
利用SPSS數據分析軟件對飛利信并購前后各期的相應數據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關矩陣
由表4可知,各主成分基本上都反應了表1中相應比率指標的信息,那么這三個主成分就可以分別用來描述該企業相應的償債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

表4 解釋的總方差
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解釋貢獻即變量的共同度大小,袁曉燕(2010)[21]在其并購研究中指出一個公共因子的旋轉平方和載入越大說明因子包含的原始變量信息量越高。由主成分法提取的初等因子荷載矩陣進行旋轉,得出旋轉后的因子變量累計方差貢獻率表明提取公共因子后對原始變量總體的刻畫情況,如表5所示,如果提取3個因子,以飛利信2014年并購前四期和并購后四期樣本數據旋轉后的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5%,因此可以認為提取3個公共因子能夠基本反映原始數據的絕大部分信息。
最后經過一系列的數據處理得出各變量指標在主成分1、2、3上的得分然后以各主成分對應的平方和載入即方貢率作為各主成分的權重構造總得分模型如下:

表5 旋轉成份矩陣
F=42.167/96.150*f1+(69.505-42.167)/96.150*f2+(76.150-69.505)/96.160*f3
再將總得分排序,即可得到飛利信并購前后各四個季度的總績效變化趨勢,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并購前后各期績效變化
五、結論
(一)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選取的數據表明2011—2012年期間橫向并購的上市公司并購沒有像預想中的那樣為企業績效做出相應的貢獻;同理也可以看出縱并和混并都使企業的績效有一定的提升,但縱并的績效波動較大說明縱并具有一定的風險。雖然建立了合理的數學模型對不同并購模式下企業數據做了分析并得出了相關結論,但是不能認為該結論是絕對準確的,首先影響企業績效的有諸多宏觀上和微觀上的因素,在研究過程中,并沒有對所選取的財務指標進行修正,剔除無關因素,再者,研究時選取的樣本數量有限,使研究結論代表性不夠,得出的結論還需進一步檢驗。
(二)飛利信并購結論
本文利用飛利信并購前后財務報表數據和相關的會計資料,建立了一系列以財務比率指標為主的績效測評方法,通過對比研究,有下面幾個考慮因素:首先,盡量使用了較少的主因子來代替原來較多的指標,王靜(2015)[22]研究表明該操作有效的避免了各項財務指標之間存在相關性而造成的信息嚴重重疊的問題;其次,在計算綜合得分F時,權數是以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來加權確定的權重顯現出了對于績效評價的公正和客觀。再者,因子分析剔去了不同量綱的干擾。最后,操作簡便易行。本文數據分析選取了SPSS這一數據分析軟件來進行相應的數據挖掘的。根據數據分析可知:應收賬款周轉率等在主成分1上有較高的荷比,說明主成分1大體上體現了這些指標的信息;同理主成分2、3也反映了相應財務比率的信息,同時,根據主成分代表的指標確立了相應能力因子。由并購前后各能力因子的變化可知,飛利信2014年一期在以現金支付和股權支付方式下的并購在資產運作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有所提升且幅度較大,而償債能力明顯有所下滑,企業成長能力在短期內趨勢變化并不顯著,本文通過對創業板上市公司飛利信的并購績效予以實證分析證明收購可以增強潛在的戰略靈活性驗證所選擇的評價指標體系以及由因子分析法建立的評價模型相契合,分析結果表明大多數交易動機都是價值創造機會符合評價的要求,表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Healy P M,Palepu K G.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future earnings performance:the case of initiating dividends[J].1986.
[2]Lynch L J,Perry S E.An examination of pre-merg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in merging firms*.[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2,14(September):279-295.
[3]Kitching J.R.Lucas(1994).Industrial Relations Discourse,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rvice Industries:Are Hotels and Catering Merely a Case of Oversight?Department of Hotel,Catering and Tourism Management,th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1995,13:81-85.
[4]Agrawal A,Jaffe J F.The Post Merger Performance Puzzle[J].Advances in Mergers&Acquisitions,2001,1:7-41.
[5]Berger A N,Saunders A,Scalise J M,et al.The effects of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small business lending 1[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7,50(2):187-229.
[6]Ruback R S,Jensen MC.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The scientific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3,11(11):5-50.
[7]Loughran L,Vijh A M.Do Long-Term Shareholders Benefit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Finance,1997,52(5):1765-90.
[8]Moeller S B,Schlingemann F P,Stulz R M.Do Acquirers With More Uncertain Growth Prospects Gain Less From Acquisitions?[J].General Information,2004.
[9]Finkelstein S,Cooper C L.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erformance revisited-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post-[J]. Advances in Mergers&Acquisitions,2009,8(2009):1-17.
[10]張新,2003.上市公司收購的立法和監管——我們為什么不能采取美國模式?[J].證券市場導報(8):12-17.
[11]高雷,宋順林,2006.上市公司控制權轉移與市場反應[J].財經科學(3):30-37.
[12]李善民,陳玉罡,2002.上市公司兼并與收購的財富效應[J].經濟研究(11):27-35.
[13]吉永峰,2014.企業技術并購績效現狀與提升研究——以蘇州為例[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6):43-46.
[14]葛結根,2015.并購支付方式與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以滬深上市公司為收購目標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9).
[15]陳昆玉.中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實證研究綜述[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6,22(5):15-19.
[16]劉磊,2004.關于我國企業并購動因的分析[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4-85.
[17]王敏.因子分析法在上市公司績效評價中的應用[D].石油大學(北京),2005.
[18]田磊,2013.飛利信:收購資產資不抵債存疑[J].股市動態分析,(11):58-59.
[19]李蕾,宋志國,2009.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實證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6).
[20]劉芊,藍國賑,2008.基于SPSS軟件的因子分析法及實證分析[J].科技信息(學術研究)(36).
[21]袁曉燕,2010.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分拆上市公司績效評價[J].開發研究(3):121-124.
[22]王靜,2015.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分析——基于不同并購方式的典型并購案例[J].財會通訊(綜合)(1):46-48.
(責任編輯:D 校對:T)
F271
A
1004-2768(2016)09-0128-04
2016-05-30
上海市科技發展基金軟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大飛機產業配套服務的價格機制研究”(16692108300)
吳圓圓,女,河南信陽人,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研究方向:財務會計;于謙龍(1977-),男,河南新野人,管理學博士,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講師,研究方向:財務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