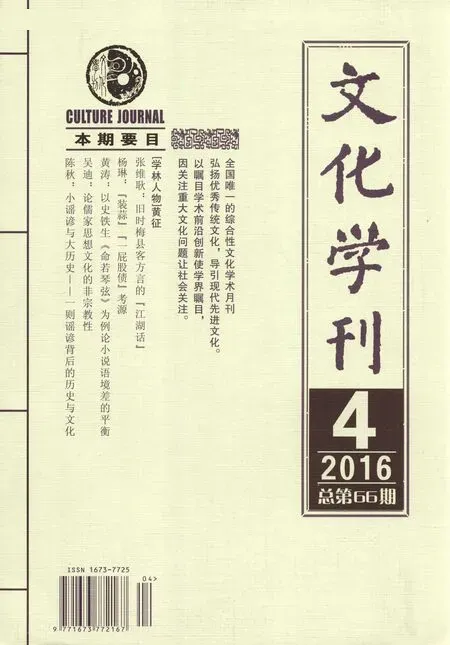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1+X”模式探索
——基于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的研究
許子嬋
(晉中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
【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1+X”模式探索
——基于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的研究
許子嬋
(晉中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本文通過對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發展狀況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分析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過程中的存在的問題,提出“1+X”的發展模式,不僅可以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且對于推動社會經濟轉型和社會協調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1+X”模式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日趨重視。為了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示范帶頭作用,探索和積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方法和經驗,國家及各大省、市陸續確立了多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名單,從而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發展現狀
本次研究以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作為調查研究對象,山西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大省,到目前為止,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共有17家,其中國家級包括:山西老陳醋集團有限公司、山西廣譽遠國藥有限公司、稷山縣飛凱達食品有限公司;省級包括:山西水塔醋業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雙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有限公司等14家,主要涉及食品制作技藝、中藥傳統炮制制作技藝和傳統手工藝品制作技藝三大類。近三年間,這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的發展狀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企業的生產規模情況
山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生產規模和生產經營收入方面產業化程度低。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中達到規模化生產的僅有8家,其余9家均未實現規模化生產,主要以“小作坊+農戶”的形式進行生產。從17家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近3年的生產經營收入可以看出只有山西老陳醋、太原雙合成食品、山西廣譽遠國藥等一些知名大企業收入呈正增長,達到規模化生產,其余小作坊增長率基本為負值,甚至平定市文亮刻花瓷砂器研究所出現了投入大于產出的情況。
(二)企業累計資金投入情況
從17家非遺保護示范基地近三年累計資金投入情況可以看出投入的資金不足,導致產業化發展難以成規模。一方面表現在政府對于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投入不足,2012年到2015年3年期間,17個保護性示范基地共計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性資金1.05億元,其中政府財政投入0.05億元,而且僅有9家企業受到政府的不同程度資金投入。企業自身方面投入力度也不夠,不能合理的擴大生產規模,導致收入增長率緩慢或出現下滑的趨勢。
(三)企業保護傳承情況
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的傳承人,主要涉及國家級、省級、市級及縣級傳承人。從傳承人的數量上看,基本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傳承人建設路徑,保障了傳承人隊伍的穩定性,傳承類型主要涉及群體傳承、家族傳承和社會傳承。
(四)企業對于與自身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的保存情況
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對自身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的保存主要涉及以下方法:
1.收集、整理相關歷史資料、賬冊等進行建檔保存,將資料編撰成冊,出臺相應的檔案管理機制,加大非物質遺產的保護;
2.保留原始工具,收集實物標本籌建博物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3.通過建立景區,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將這一資料傳承,系統的呈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4.成立了傳習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傳承、研發、創新、開發。
(五)基地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所采取的主要方法
現階段,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的主要保護措施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活動提高宣傳力度,增加企業知名度,提高生產競爭能力;
2.增加資金投入擴大生產力、加大培訓力度培養人才、更新設備、改善工作環境,提高生產效率;
3.采取“基地+博物館+旅游”的形式,推動基地產品的發展。
4.開展項目保護,建立完善的傳承人管理制度,大力支持傳承人開展傳承活動,使項目后繼有人、傳承有序;
5.對核心工藝進行了重點保護及復古性恢復等措施。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問題分析
從企業、政府和社會等方面來分析山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在非物質文化生產性保護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一)產品難以規模化生產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生產情況看,長子縣西南的響銅樂器、高平刺繡、平遙薛生金器技藝、平定縣張氏砂器陶藝坊等多家企業產品呈現“小作坊”和“農戶”的形式,生產均未達到產業化。
1.企業自身的投入不足,難以規模化生產。
企業的投入包括資金、宣傳、管理、技術等方面,而且這些方面都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企業資金投入不足,會影響企業難以創新,難以引入先進設備和技術,難以擴大經營范圍,勢必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收入和資金再投入,最終導致企業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受影響。
2.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脫離了社會、文化和生活的需要,難以規模化。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傳統手工技藝品逐漸脫離了社會的需求,其生存和發展受到了阻礙,比如:長子縣西南的響銅樂器、平遙薛生金器技藝等,逐漸脫離了社會、文化和生活的需要,以至于在以低成本、高效率、大利潤的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中,很難具有相應的競爭力。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銷量不高
山西省17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近3年的經營收入中,只有9家企業呈正增長,其余均出現負增長,可見企業產品的銷量不高。
1.企業產品銷量不高體現在市場的需求不大,一方面由于企業的創新力度不夠,導致產品類型單一,外觀、花樣及品種太少,可供市場選擇性低。另一方面還體現了產品覆蓋范圍小,只注重禮品、收藏,忽略民用。此外市場的需求還受公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的影響。
2.企業自身市場開拓能力不足, 市場運作能力差,知名度不高,缺乏品牌的影響,導致產品滯銷。這方面問題小作坊最明顯,一方面由于自身市場開拓能力不強,缺少專門的銷售路徑,受市場銷售波動影響較大;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知名度不高,缺乏品牌效應,導致產品滯銷。
(三)政府的扶持和監管力度不夠
1.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夠
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上都是屬于地方文化或民間文化,經濟價值不高,項目規模小,對市場的把控能力有限,風險預判能力不足,其弱勢地位非常明顯,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及扶持,容易瀕危。政府支持主要包括提倡、宣傳和資金扶持等。在生產性保護這一方式上,政府的資金扶持尤其關鍵,但從近三年的數據上看,山西政府的資金扶持廣度和深度不夠。
2.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
政府的監管力度也會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產品的發展。由于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市場受假冒產品沖擊嚴重,醋業、酒業以及中醫藥方面都出現類似問題,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受到嚴重影響。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1+X”模式運行
結合上述問題分析,本次研究提出了“1+X”模式探索。“1+X”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模式中“1”代表企業基地自身,“X”代表“農戶”“院校”“合作社”“旅游”等多個合作單位部門,通過優勢資源的集中以及政策的推動,擴大產品的延伸及品牌化建設,從而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的保護和傳承。
(一)建構 “基地+農戶”模式,加強企業基地可持續發展
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人力資源來源于農戶,比如中醫藥和手工布藝等,為了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性保護和傳承能夠持久和穩定,促進企業的長期性發展,必須以基地為平臺,與“農戶”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模式,從而達到互利共贏的雙豐收。
(二)建構 “基地+院校”模式,促進產品的時代化發展
為了促進產品的規模化和產業化的發展,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產品能夠滿足市場化環境的需求,需要企業以自身優勢為基礎,聯合各大院校一起研究、開發和創新。將高校的優勢資源利用起來,從產品的樣式和外觀入手,確保產品樣式的多樣化,作用功能的生活化和大眾化,增加市場的可供選擇性,推動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產品的時代化發展。
(三)建構“基地+公司”模式,推動基地生產產業化發展
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小企業、小作坊由于自身市場開拓能力不足,缺乏銷售路徑和品牌效應,市場消息滯后,產品滯銷,不能規模化生產。企業基地可以采取“基地+公司”模式,基地可以聯合銷售公司、市場調研分析公司以及市場廣告公司,采取強強聯手,增強產品的品牌化,提高市場的占有力,使產品達到規模化生產和銷售,推動產品生產產業化發展。
(四)構建“企業基地+旅游”模式,實現基地產品市場化發展
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建立“基地+旅游”的發展模式,一方面在生產基地建立博物館和旅游景區,增強社會大眾的保護意識,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保護和傳承;另一方面與旅游公司建立橫向合作,在各大景區推出手工藝產品,通過節假日期間景區的人流量提升經濟效益,實現基地產品市場化的發展。
除此以外,“1+X”模式,不僅以企業基地為依托,還可以繼續多元化發展,為了保證模式的正常化運行,還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完善,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
[1]羅藝.論日韓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對中國的啟示[J].當代世界,2010,(5):66-67.
[2]劉德龍, 張興宇,袁大偉.非遺的生產性保護與民眾的日常生活需求——以魯南奚仲文化的保育路徑為例.中華文化論壇,2014,(3):115-112.[3]徐藝乙.傳承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中的作用[J].貴州社會科學,2012,(12):5-8.
[4]胡惠林,王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從“生產性保護”轉向“生活性保護”[J].藝術百家,2013,(4):19-25.
[5]楊亞庚,陳亮,賀正楚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探索[J].東方學術,2014,(1):201-217.
【責任編輯:王 崇】

秦 立鹿紋 鳳翔縣鐵溝遺址采集
C910
A
1673-7725(2016)04-0164-04
2016-03-05
本文系2014年度山西省藝術科學規劃項目“山西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利益主體行為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14A409)的研究成果。
許子嬋(1987- ),女,山西大同人,助教,主要從事社會管理、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