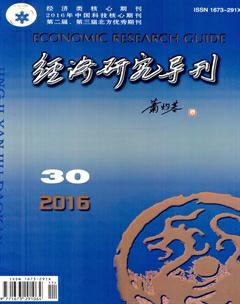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轉型
劉思思
摘 要:快速城鎮化是我國邁入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其中也蘊含著社會矛盾凸顯、社會沖突加劇等重大公共安全風險。需要加快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方式轉變,綜合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三方力量,兼顧效率和公平,構建多方聯動、重點突出、全面協調的公共安全管理體系。
關鍵詞:快速城鎮化;公共安全管理;轉型
中圖分類號:C93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0-0116-02
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03個百分點,為推進現代化建設、保持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同時,由于城鎮化所用時間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大大壓縮,各類矛盾和沖突在短短三四十年內集中顯現、交織、碰撞,也引發了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難度。
一、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土地、資金進行再分配、再平衡,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秩序進行再分化、再調整,本身就意味著風險和動蕩,加上我國城鎮化在時間上高度壓縮,在動力上過分依賴行政主導,資源要素錯配、社會矛盾沖突更為嚴重。
1.人口流動性上升弱化了社區自治功能。以良好鄰里關系為紐帶構建的熟人社區是我國傳統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入,社區人口的頻繁流動和居住形態的快速變化,對原有穩定的社區結構造成巨大沖擊,社區居民在價值觀念、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日益明顯,溝通交流趨于減少,傳統開放式熟人社區逐漸向封閉式的陌生人社區轉變,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隨之降低,容易誘發各種矛盾沖突以及犯罪、吸毒、賭博等社會問題,社區公共安全面臨嚴峻挑戰[2]。
2.城市內部二元分割激化社會矛盾。二元結構不僅存在于城鄉之間,在城市內部也同樣存在。突出的表現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目前,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約有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1],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加上貧富差距拉大,這部分群體社會心理極易失衡。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不斷崛起,社會期望不斷提高,但受制于自身文化技能,很難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情緒增加。安徽團省委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36.5%的人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現過痛苦失望,9.7%的人產生過憤怒報復心理。
3.“城市病”問題突出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由于人口過度涌入,內部空間規劃不合理,產業布局失衡等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國大城市普遍出現以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資源短缺為代表的城市病,不僅直接危害人民身體健康,還對公眾心理和社會心態造成不利影響。我國655個城市,約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時段出現擁堵[3],每年因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過20萬人。2007—2015年,超過360個城市遭遇內澇,城中村和城鄉接合部等外來人口集聚區人居環境較差、社會秩序混亂。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城市病”還有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擴展的趨勢。
4.體制機制不健全誘發矛盾沖突。由于過分依賴行政推動,加上要素產權制度不健全,缺乏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和協調機制,近年來,在土地征用、城區擴建、舊城改造過程中的沖突事件呈上升趨勢[4]。中國社科院法學院研究所報告顯示,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中,由拆遷征地引發的占到一成左右。各類“釘子戶”時常見諸報端,對社會心理和氛圍造成消極影響。同時,拆遷過程中的產權爭奪和拆遷后的一夜暴富等也是誘發矛盾沖突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轉型的思路和對策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人員結構日益復雜,利益主體更趨多元,矛盾點和風險點增多,需加快推進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轉型,構建多方聯動、重點突出、全面協調的公共安全管理體系。
1.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首先,要轉變政府治理理念。目前我國內地公安機關的110報警服務臺每月接到的報警電話中,屬于社會服務性質的已達80%以上[5]。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大包大攬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要樹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理念,將政府供給的公共安全服務,尤其是社會治安服務從大量低效的非警務活動中解放出來,聚焦在對違法犯罪活動的有效打擊上。其次,要改進評價考核方法,建立從效果、效率、效益三個維度、政府部門、社會公眾、第三方機構三方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安全服務成效評價機制,提升政府資源利用效率。再次,要高度社區綜合治理。社區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單元。要通過進一步完善社區安全體系,培育和發展社會團體,開展社區文化建設,加強安全教育和監管,建立社區居民間有效的信任制度,增強社區的凝聚力,逐步重現守望相助的熟人社會文化傳統[6]。
2.進一步加強市場供給。長期以來,出于規模經濟和特殊的行業性質和服務內容的考慮,我國在公共安全領域實行了比較嚴格的市場管制,這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是必要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管制成本已逐漸大于管制收益。因此,應逐步放開社會資本進入公共安全領域的準入限制。除法律法規和禁毒外,其他產品都可以嘗試市場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比如,英國就曾以15億英鎊的價格外包警務,包含社區巡邏、犯罪偵查等。同時,公共安全服務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逐步放開管制的同時,應對市場的準入門檻、質量標準、服務價格等予以明確規定,在讓人民享有高質量的公共安全服務的同時,盡可能突出公共安全服務的公平屬性。
3.培育壯大社會供給。政府的力量有限,市場供給以盈利為必要條件,在公共安全領域還有大量的“真空”地帶,只有通過調動社會資本的力量,有效使用社會資源,才有可能真正滿足日益增長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需求。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夯實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的法律基礎,給予社會組織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要完善社會供給的資助激勵機制,在培訓、資金、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通過建立常態化的公共安全培訓制度,成立專門基金會為自愿供給行動購買意外保險等,增強社會供給的能力。
當然,政府、市場、社會三方供給的邊界不是絕對的,其中,必然有交叉、有滲透,有學者就提出過城市公共安全服務合作網絡[7],這與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多元主體之間合作和協調的具體機制、利益如何平衡、權責如何界定,都還需要在具體的實踐中去總結、完善。
參考文獻:
[1]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Z].2014.
[2] 劉智霞.社區公共安全的建設[J].城市與減災,2007,(4).
[3] 向春玲.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
[4] 劉建平,楊磊.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風險與城市治理轉型[J].中國行政管理,2014,(4).
[5] 袁春瑛.社會治安服務有效供給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0.
[6] 高瑞,李存祥.淺析構建熟人社區建設在社區管理模式的運用[J].赤子,2015,(15).
[7] 李禮.城市公共安全服務供給的合作網絡[J].中國行政管理,2011,(7).
[責任編輯 劉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