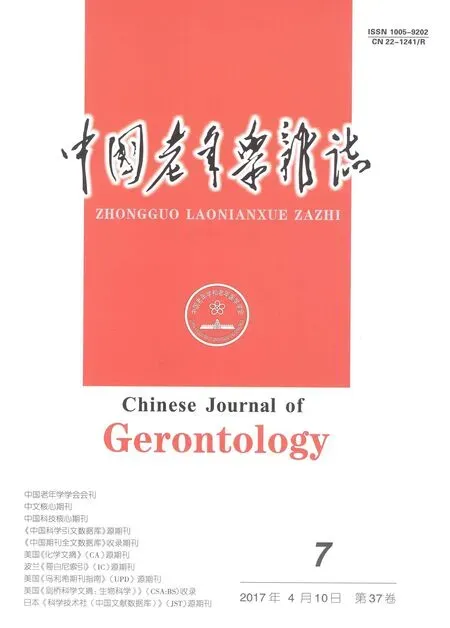老年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社區健康管理的必要性分析及項目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劉 丹 田 青 趙紅云 曾 燕
(武漢科技大學醫學院腦與認知功能實驗室,湖北 武漢 430081)
老年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社區健康管理的必要性分析及項目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劉 丹 田 青 趙紅云1曾 燕
(武漢科技大學醫學院腦與認知功能實驗室,湖北 武漢 430081)
老齡化;癡呆;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健康管理;社區
研究表明,老年期癡呆的潛伏期很長,癡呆癥狀出現相對于早期腦神經病理改變可滯后10~20年〔1〕。目前老年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概念〔2〕。流行病學資料顯示,MCI患者是老年期癡呆的高危人群。現今,MCI已被國際公認為是癡呆的前期狀態,并且早期干預MCI對延緩癡呆的發生、發展至關重要〔3,4〕。本文通過綜合分析我國日益增長的MCI患者人群和高危老齡人群壓力、早期干預MCI的理論依據和可行性、發達國家開展MCI早期健康管理的幾種模式和我國開展老年人MCI社區健康管理的優勢與基礎,提出立足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項目化MCI健康管理模式的構想。
1 MCI的推薦定義和診斷
1.1 MCI的推薦定義 專家提出MCI是介于正常老化與癡呆之間的一種過渡狀態和癡呆的早期階段,可作為一個臨床疾病,推薦定義:(1)認知能力與年齡不相符;(2)非癡呆;(3)認知功能下降;(4)基本生活能力正常〔4〕。
1.2 MCI診斷流程 (1)根據病史和某些客觀檢查如神經心理評估篩查出MCI患者。目前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量表是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MSE)和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CA),兩份表格均易于操作,完成共需約20 min。再結合臨床癡呆評定量表(CDR)、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和老年抑郁量表(GDS)進一步辨別分析。(2)區分MCI的臨床亞型。根據是否存在記憶力下降可將MCI分為遺忘型(aMCI)和非遺忘型(naMCI);根據損害區域可分為單區域型和多區域型。(3)進一步尋找可能的病因。MCI是一組臨床綜合征,在病因學上具有高度的異質性,確立診斷后,進一步分析可能的病因有助于預后的判斷。不同原因的癡呆在MCI階段的臨床鑒別比較困難,醫生需根據患者或知情者提供的病史、實驗室和神經影像學檢查等作出綜合分析。變性疾病常隱襲起病、進行性加重;血管性疾病常突然起病,多伴有血管性危險因素、腦卒中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病史;有精神疾病因素的患者常有焦慮或心境障礙病史;部分患者可繼發于其他系統性疾患如心房顫動、充血性心力衰竭、糖尿病和腫瘤等。不同病因引起的認知損害區域有所差異,單域或多域aMCI常被認為是非阿爾茨海默病(AD)的前驅狀態,naMCI進展為AD可能性更大。
1.3 MCI的診斷標準 目前主要根據國際公認的Petersen S的 MCI診斷標準,有記憶下降主訴,最好有旁人確證;客觀記憶損害:文盲組17分≤ MMSE ≤23分、小學組20分≤ MMSE ≤ 25分、中學或以上組23分≤ MMSE ≤ 27分;總體認知功能正常;ADL正常;無精神障礙。
有關內容綜合如下:(1)以記憶障礙為主訴,且必須有知情者證實;(2)其他認知功能相對完好或輕度受損;(3)ADL不受影響,ADL量表≥18 分;(4)達不到癡呆診斷標準;(5)排除其他可引起腦功能衰退的系統疾病;(6)GDS評分為2~3級;CDR評分為0.5,記憶測查分值在年齡和教育匹配對照組1.5SD以下。
2 老年人MCI健康管理的理論依據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表明藥物干預(包括銀杏和抗感染藥)可改善MCI的預后,對于血壓、血脂和血糖等危險因素的管理及預防性使用阿司匹林和維生素E等減少MCI發展為癡呆的風險也需進一步證實〔5〕。因此,早期介入,施與積極的綜合健康管理對預防癡呆的發生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研究〔5〕表明,成年人認知功能存在可塑性,即可以通過豐富生活環境、認知訓練和認知刺激來提高,甚至逆轉。MCI 患者仍然保留有相當的認知能力和認知可塑性,還處于實施干預、預防癡呆發生的最佳時期,早期接受干預可以較長時間維持現存的認知功能水平〔6,7〕。
最近的研究表明,早期篩查,早期健康管理可以提高人群對MCI或者癡呆危險因素的知曉和管理能力、降低MCI的發病率、降低患者死亡率、降低醫療花費和改善MCI患者生活質量〔8,9〕。其中通過堅持平衡飲食〔9〕、適宜的認知刺激〔10〕和認知訓練〔11,12〕、多元化的健康教育〔13〕、大眾和個體的體育活動〔13,14〕和活躍的社交活動均可延緩癡呆的發生和發展〔15〕。
3 發達國家實施老年人MCI健康管理的幾種模式
在發達國家,首先是從國家層面制定綜合防治策略〔16〕,(1)針對全科醫生開展相關知識培訓,增加家庭醫生的相關專業知識,號召家庭醫生積極參與癡呆管理,制訂綜合治療方案;(2)整合現有醫療資源,利用好社會健康資源,比如,日托中心,咨詢服務設施及相關支持系統加強MCI的管理;(3)建立專門的癡呆醫學中心;(4)在社區試點開展以維持和改善老年人認知功能的公共衛生服務〔17,18〕。除了政府部門以外,一些國家強大的醫療保險機構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在MCI的預防和研究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早在1997年就出臺了《介護保險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MCI階段的患者出現在醫院或者診所的可能性比較小〔19〕,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常常是他們最早接觸和接觸最多的專業衛生人員,社區衛生人員在MCI的早發現、早診斷、早干預和早治療過程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19〕。許多國家的社區衛生保健機構已經開始介入MCI的早期識別及干預,已有研究報道初級衛生保健機構開始建立記憶診所〔20〕。加拿大一個為期3年多的隊列研究表明,記憶診所通過采取包括提供社會工作者服務、長期護理計劃、安全開車回家、整合社區資源、定期科學評估、定期隨訪、監測和轉診等綜合干預措施積極干預MCI,極大地增強了MCI患者的生活質量,改善了MCI患者和癡呆病人就診和尋醫的條件與機會〔20〕,患者的滿意度非常高〔20〕。在初級保健機構設置記憶診所為MCI患者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
4 我國老年人MCI健康管理所面臨的壓力
4.1 MCI和癡呆患者人群的壓力巨大 中國正面臨日益增加的MCI患者人群,據中國老年人認知功能障礙診治專家共識撰寫組的意見,中國已經有MCI患者人群近3 700萬〔4〕。最近,華山醫院神經內科洪震教授領銜的科研團隊在上海市靜安區靜安寺街道60歲以上老年人群中率先建立了國內第一個研究老年認知功能障礙的社區人群隊列——“上海老年隊列”,并于2015年在國際上首次報道了我國老年人群中MCI的患病率〔21,22〕,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患病率相近〔23〕。
除此之外,中國面臨的癡呆患者人群壓力也特別巨大。流行病學資料表明中國各類癡呆患者總數已經超過900萬〔24〕,到2030年將達1 200萬,2040年將達到2 200萬,是所有發達國家癡呆患者人數的總和〔24〕,其中以AD為最高發,占所有癡呆病例的60%~70%〔2〕。
4.2 我國針對MCI和癡呆,各方面的準備均顯不足 據估計,目前全球癡呆疾病所耗費的直接醫療資源高達8 180億美元,還不包括家庭照顧所產生的間接費用和人力成本〔3〕,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94%的老年期癡呆癥患者只能選擇家庭照顧〔3〕。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的相關社會資源和人力嚴重不足〔25〕,我國僅有少數幾家三級醫院開設有記憶診所,目前還沒有一家從事老年期癡呆研究的專門機構和醫院;癡呆并未被納入到慢病管理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針對MCI的健康管理和保健服務還相當欠缺;相比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制定的指南、模型和數據庫〔2,3〕,我國在該領域的工作尚處于空白階段,難以與國際接軌。
另外,在思想觀念上也存在宣傳不夠、認識不足的問題。被診斷為MCI可能會增加個體的焦慮,甚至導致抑郁;被貼上了MCI標簽,可能會退出社會生活;也有可能因為誤診導致醫療和護理資源的浪費〔25〕,因此早期識別和早期干預不僅花費巨大、困難重重,如果措施不當,還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另外,被診斷為癡呆可能帶來3個惡果〔4〕:(1)一損俱損,兩代人都活不好;(2)老年歧視,嚴重的老年癡呆可能導向對老年人群的負向評價和老年價值的徹底否定;(3)老年惡待,如果在心理上已經厭煩老人,在情感上已經排斥老人,在行為上就可能虐待、遺棄甚至殺老。
5 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本土化社區老年人MCI健康管理模式
5.1 我國開展社區老年人MCI健康管理的可行性和優勢 盡管中國基于社區層面的MCI健康管理尚未起步,但是我國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進行MCI綜合防控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首先,我國大多數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已經基本形成慢性病基層防治模式,在慢病管理基礎上增加MCI健康管理內容和服務項目,無較大的經費之憂,極具操作性,且患者的依從性良好;其次,負責慢病管理的家庭醫生團隊經神經精神病專家嚴格培訓后開展MCI預防保健服務項目,統一規范執行標準,能夠保證MCI健康管理質量;再次,進行戶籍式電子網絡信息管理可使MCI管理更全面,科學完善的電子健康檔案有利于記錄查閱、追蹤治療和反饋總結。因此,結合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中的慢病基層防治模式,以社區為平臺,開展MCI綜合健康管理,能帶來可觀的健康狀況改善,且惠及面最廣,成本最低。那么,如何設計一個低成本、廣覆蓋、可持續、可復制及高效益的MCI社區健康管理模式?
5.2 構建項目化MCI社區健康管理模式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我們提出,立足于社區開展MCI群體干預和綜合健康管理,既可從群體層面提高民眾意識,幫助人群識別和控制MCI危險因素,預防癡呆;又能保證MCI患者繼續生活在熟悉的人群和居住環境中,減輕其脫離社區支持系統和熟悉人群的焦慮感。為了增加健康管理效果和服務質量,達到預防癡呆的目的。為此我們擬構建一個項目化MCI社區健康管理模式。該模式的特點為:(1)在國家針對65歲及以上老年人所提供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基礎上,增加MCI健康管理內容,做到轄區內65歲及以上的MCI患者和MCI高危老年人全覆蓋; (2)組建專業化的MCI健康管理團隊,且相對固定,保證管理質量。以社區慢病防治家庭醫生團隊和神經精神疾病專家為核心,借助大學生志愿者團隊力量,鼓勵干預對象(轄區內65歲及以上MCI患者和MCI高危老年人)及其家屬廣泛深度參與;(3)根據認知功能評分和危險因素情況將干預對象分級,制定分級健康管理計劃;(4)分級實施結構化綜合干預措施;(5)綜合、動態、科學地評價干預效果。采用聯合量表MMSE、MoCA和ADL每3個月1次評價干預對象認知功能變化;檢測外周血生物學標志物輔助評價個體干預效果;采用多個指標考核項目管理績效,比如MCI患病總人數、MCI發病率、MCI管理覆蓋率、規范管理人數、癡呆轉化率、認知功能維持情況、管理失訪等指標評價項目管理效果。借助以上模式,通過對社區老年人的健康知識、生活習慣、飲食習慣、體育鍛煉、運動環境、學習環境、認知功能和康復保健等進行綜合干預,延緩癡呆的發生和發展,提高老人的生活質量,降低醫療花費。
1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The Global Impact of Dementia.Published by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London〔EB/OL〕.http://www.worldalzreport 2015.org
2 Petersen RC,Smith GE,Waring SC,etal.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outcome〔J〕.Arch Neurol,1999;56(3):303-8.
3 Petersen RC.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a diagnostic entity〔J〕.J Intern Med,2004;256(3):183-94.
4 中華醫學會老年醫學分會老年神經病學組.中國老年人認知障礙診治流程專家建議〔J〕.中華老年醫學雜志,2014;33(8):817-25.
5 Bliss TVP,L?mo T.Long-lasting potentiation of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the dentate area of the anaesthetized rabbit following stimulation of the perforant path〔J〕.J Physiol,1973;232(2):331-56.
6 Simon SS,Yokomizo J,Ebottino CM.Cognitive intervention in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 systematic review〔J〕.Neurosci Biobehav Rev,2012;36(4):1163-78.
7 Fitzpatrick-Lewis D,Warren R,Ali MU,etal.Treatment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CMAJ Open,2015;3(4):E419-27.
8 Sampson EL,Bulpitt CJ,Fletcher AE.Survival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ople:the effect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social engagement〔J〕.J Am Geriatr Soc,2009;57(6):985-91.
9 Polidori MC.Preventive benefits of natural nutrition and lifestyle counseling against Alzheimer's disease onset〔J〕.J Alzheimers Dis,2014;42(Suppl 4):S475-82.
10 Kinsella GJ,Ames D,Storey E,etal.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memory:a randomized trial of memory groups for older people,including those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J Alzheimers Dis,2015;49(1):31-43.
11 Law LL,Barnett F,Yau MK,etal.Effects of functional tasks exercise on older adul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t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Age Ageing,2014;43(6):813-20.
12 Giuli C,Papa R,Lattanzio F,etal.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training for elderly:results from my mind project〔J〕.Rejuvenatiin Res,2016;19(6):485-94.
13 Sink KM,Espeland MA,Castro CM,etal.LIFE study investigators.effect of a 24-month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vs health education on cognitive outcomes in sedentary older adults:the LIFE randomized trial〔J〕.JAMA,2015;314(8):781-90.
14 Taylor ME,Delbaere K,Lord SR,etal.Neuropsychological,physical,and functional mobility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falls in cognitively impaired older adults〔J〕.J Gerontol A Biol Sci Med Sci,2014;69(8):987-95.
15 Hughes TF,Flatt JD,Fu B,etal.Engagement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progression from mild to severe cognitive impairment:the MYHAT study〔J〕.Int Psychogeriatr,2013;25(4):587-95.
16 Awata S.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 system supporting the liv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J〕.Nihon Ronen Igakkai Zasshi,2013;50(2):200-4.
17 Kamegaya T,Maki Y,Yamagami T,etal.Pl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program for prevention of cognitive decline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with subjective memory complaints〔J〕.Geriatr Gerontol Int,2012;12(4):673-9.
18 Hughes TF,Flatt JD,Bo F,etal.Interactive video gaming compar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 feasibility study〔J〕.Int J Geriatr Psychiat,2014;29(9):890-8.
19 Kremen WS,Jak AJ,Panizzon MS,etal.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heritability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Int J Epidemiol,2014;43(2):600-10.
20 Lee L,Hillier LM,Stolee P,etal.Enhancing dementia care:a primary care-based memory clinic〔J〕.J Am Geriatr Soc,2010;58(11):2197-204.
21 Ding D,Zhao Q,Guo Q,etal.The Shanghai Aging Study:study design,baseline characteristics,and prevalence of dementia〔J〕.Neuroepidemiology,2014;43(2):114-22.
22 Ding D,Zhao Q,Guo Q,etal.Prevalenc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Aging Study〔J〕.Alzheimers Dement,2015;11(3):300-9.
23 Sachdev PS,Lipnicki DM,Kochan NA,etal.Cohort Studies of Memor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COSMIC).The prevalenc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diverse geographical and ethnocultural regions:the COSMIC Collaboration〔J〕.PLoS One,2015;10(11):e0142388.
24 Chan KY,Wang W,Wu JJ,etal.Epidemiology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forms of dementia in China,1990-2010: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J〕.Lancet,2013;381(9882):2016-23.
25 Maki Y,Yamaguchi H.Early detection of dementia in the community under a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 system〔J〕.Geriatr Gerontol Int,2014;14(S2):2-10.
〔2016-12-11修回〕
(編輯 李相軍)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81571095)
1 杭州市余杭區第五人民醫院康復科
曾 燕(1968-),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腦與認知功能障礙研究。
劉 丹(1976-),女,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神經科學、腦與認知功能障礙研究。
R592
A
1005-9202(2017)07-1792-03;
10.3969/j.issn.1005-9202.2017.07.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