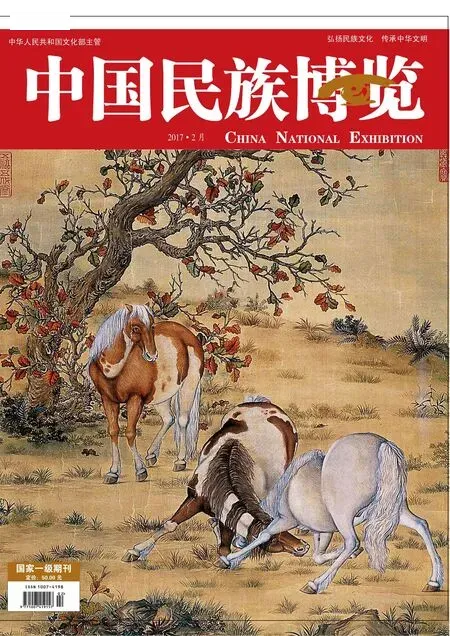游藝文化視角下藏羌鍋莊融 入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的可行性探究
穆田恬
(阿壩師范學院,四川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623000)
游藝文化視角下藏羌鍋莊融 入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的可行性探究
穆田恬
(阿壩師范學院,四川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623000)
本文從游藝文化視角切入,將游藝文化古樸的形態、藝術的語言與樂生的旨歸特色與藏羌鍋莊相結合,探討藏羌鍋莊作為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的可行性,以期起到豐富審美經驗、提升審美趣味、促進身心和諧發展的美感教育目的。
游藝文化;藏羌鍋莊;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
藏羌族鍋莊作為原生態藝術文化形態之一,深深植根于藏羌文化之中。隨著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觀念的深入,藏羌鍋莊也以其獨特的舞蹈藝術特性和原生態藝術傳承價值,成為校本文化中受眾面極廣的藝術樣式之一。
以四川省阿壩師范學院為例,學校是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所少數民族師范類院校。阿壩師范學院將藏羌鍋莊作為校園文化,在每年新生入校后組織大一新生學習藏族鍋莊,更以系部之間鍋莊比賽的形式作為校本文化進入新生的大學生活。阿壩師范學院在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文化工程上,一直進行著積極而有效的實踐與嘗試。雖然學校是一所地處民族地區的高等院校,但是就生源來看,仍以漢族學生為主,少數民族學生只占總人數的1/3。由此,對于相當一部分沒有接觸過藏羌鍋莊這一古老藝術形態的漢族學生而言,藏羌鍋莊還是一個新奇的“外來物”,是一個對象化的文化客體。一定程度上,鍋莊比賽這一集體活動成為“為了比賽而進行的集體舞蹈訓練”。對藏羌鍋莊的學習不僅成為一種強制性的被動學習,而且藏羌文化可能難以在學生之間產生文化認同感,也難以深植于學生心中。
基于此,筆者提出以游藝文化的視角,充分利用游藝活動的特征,通過可綜合的民族文化內容、可整合的藝術活動過程、可對話的文化交流方式,對藏羌鍋莊融入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的可行性進行探討,希冀以校級選修課的方式介入,一方面,旨在通過學校公共藝術教育,“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素養,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另一方面,旨在通過對藏羌鍋莊的學習,使大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藝術有所了解與掌握,培養他們主動開拓、接納多樣性文化的學習意識,擔負起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發展的重要使命。
一、游藝文化內涵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篇》),是我國古文獻中最早對“游藝”二字的論述,據朱熹注釋:“游者,萬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詩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朱熹這一注解被后來的學者所普遍認同,只是游藝文化中“藝”的形式、內容,乃至功能,隨著社會變革而烙印下了時代的痕跡,但“游”的意味卻始終如一,如朱熹所言為“萬物適情之謂”。
我們認為,游藝文化發生的場域多為民俗活動,它與“社會的民俗”“經濟的民俗”“信仰的民俗”等民俗事象一同進入我國民俗活動之列。既然游藝文化作為一種民俗文化活動,必然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通過筆者對游藝文化活動的梳理,發現游藝文化活動主要是以民間競技與民間游戲為主要內容,兩類活動內容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由于游藝活動的競技與游戲成分十分豐富,因此在游藝活動中,無論是表演游藝的人還是觀賞游藝的人,均在參與游藝活動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程度上愉悅的情感體驗。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內容、形式與功能也呈現愈加多樣化的趨勢發展,但無論如何,游藝文化始終在歷史長河的流變中,保持著其古樸的形態、藝術的語言與樂生的旨歸特色,且對于個人、集體、國家而言,均發揮著悅心與益智、識知與娛樂、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功能。
二、游藝文化視角下藏羌鍋莊融入學校公共藝術課程的可行性
(一)在古樸的形態中開展教學
隨著社會的發展,藏羌鍋莊主要的社會功能與發生場域也在轉變。但藏羌鍋莊作為樂舞文化的實質卻從沒有改變,即它是群體自發情感與個體主觀的集中表現,且反映了群體與個人的日常生活情態。藏羌鍋莊的這一樂舞實質,正是游藝文化在古樸形態特征上的體現。那么,藏羌鍋莊的古樸形態何以在學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中體現呢?筆者認為,必須轉變教學觀念、注重課堂互動,將廣播式的學習轉變為互動式的學習。比如充分利用民族地區的優勢,邀請本校的藏族羌族學生,使他們成為課堂教學的實施者,教師只是課堂的協助者。如此,學生既可以成為課堂教學的學習者,更可以成為課程資源的主動開發者,改變了學生“自上而下”被動吸收新知的過程。學生可以由1-2名藏族羌族同學來帶領進行分組學習,學習內容不僅局限于“跳鍋莊”,學習時間不用固定在課堂,學習對象也不止于教師,各小組成員可依據自身喜好,充分利用校園藏羌人文與自然的天然條件,對“接近日常生活原貌”的藏羌鍋莊進行課下拓展學習、課上交流分享。這樣,藏羌鍋莊作為校園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就不僅僅局限于鍋莊比賽這一活動形式上了。學生在課堂內外能夠充分體驗與感知藏羌鍋莊所涵蘊的古樸而鮮活的藝術生命力。
(二)借藝術的語言對話不同專業
人們在游藝活動中,總是打破約定俗成的“習慣”,加入“即興”“創新”元素,不斷豐富著游藝文化的活動方式,這是人們借多樣的藝術語言外化人們日益變化的審美心理的體現。同樣,這一點從藏羌鍋莊在隊列上的變化可見一斑。藏羌鍋莊最初是圍篝火而跳的圓圈舞,但現在它的隊列形式也不局限在圓圈的范圍內,在組織隊形中也會出現直線、弧線等,偶爾也會出現“龍擺尾”的圖案。這種和諧、對稱、均衡、比例、整齊劃一的隊形變化,其實是科學符號與藝術形象融合最直接的表達。因此,對于各個專業的學生而言,在學習與創造發展藏羌鍋莊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比如理工科類學生可以設計更加美輪美奐的幾何隊形變化,甚至用網絡技術預設合成隊列變化場景圖;美術設計專業學生可以在富有藏羌文化特色的服裝道具上進行裝飾加工。不同專業的學生在創新演繹藏羌鍋莊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運用不同的藝術語言進行了多學科多領域的滲透與對話,達到了提升大學生對科學符號與藝術形象綜合感知和理解的審美素養的學校公共藝術教育目的。
(三)融樂生的旨歸于美感教育
游藝活動首先是一項以愉悅身心為目的的“游戲活動”,再次是一項涵蘊了“藝術內涵”的游戲活動。在游藝活動中,因游藝活動接近“日常生活原貌”的特征而使參與其中的人獲取自在安逸的熟悉感,參與者以放松的心態將自己全情投入,創造出有趣而有創意的游藝活動本身。可以說,游藝活動的參與者在其間中傳達自己的感受和認識,以具有愉悅性的形式來借此表現主客觀世界,他們既是游藝活動的創造者,也是游藝活動的受益者。誠然,藏羌鍋莊作為學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內容,于學生而言除了強身健體的獲益以外,在學習藏羌鍋莊的過程中,學生并沒有承受專業知識上的太多學習壓力。在自由開放的民族情感交流與對話中,用自己熟悉但又藝術化的專業語言來表達自己對藏羌鍋莊的認知,實則是學生主客觀情感被引領向樂生旨歸發展的表征。通過藏羌鍋莊游藝化的形態,達到豐富審美經驗、提升審美情趣、發展創造美的能力、促進身心和諧發展的美感教育目的。
三、結語
能夠不斷創新發展的藝術教育必須徹底消除以“我”為圓心的封閉意識。人與人、物與物之間“不一致”的對話,乃是多樣性世界得以不斷生成新的東西,生活更加豐富的自然特征。游藝文化視角下的藏羌鍋莊融入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課程,能夠創造藝術教育所需的多樣化與開放化、趣味性與創造性的人文對話環境。非藏羌學生學習藏羌鍋莊,其實是以藏羌文化“異己者”的身份介入傳統文化藝術,但也由于異己者所擁有的不一致性,帶給了非藏羌族學生學習鍋莊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在多元化文化社會形態下,游藝文化視角下的藏羌鍋莊可以成為打破社會人之間彼此孤立、自我封閉狀態的高校公共藝術教育之手段。同時,在創造性的藝術對話中,也為傳統藏羌鍋莊的發展提供可再生藝術形態的可能性。
[1]穆田恬.漢代樂舞百戲的游藝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2014(5).
[2]教育部辦公廳印發.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R].2006(3):8.
[3]鞠向玲,賀秀梅.藝術教育離我們有多遠?——高校公共藝術教育現狀分析及價值探討[J].藝術教育,2012(8).
G642
A
穆田恬,女,回族,四川省都江堰市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學前教育專業舞蹈教學、藝術教育,阿壩師范學院基礎教育系。
本文為校級課題《民族地區高校學前教育專業舞蹈課程研究》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JY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