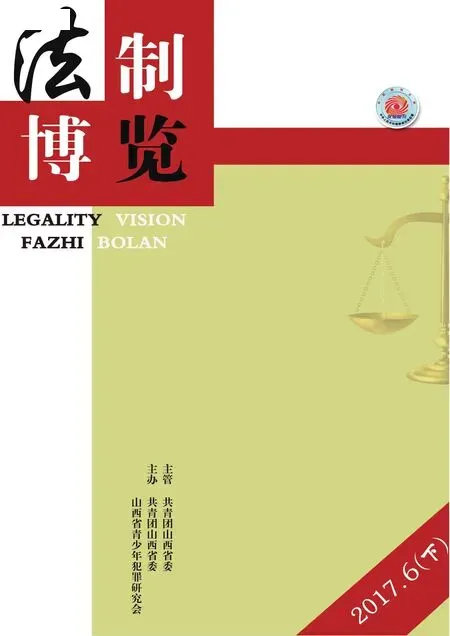從司法解釋看網絡誹謗犯罪的認定
劉丹陽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5
?
從司法解釋看網絡誹謗犯罪的認定
劉丹陽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5
網絡技術的進步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便捷的同時,其匿名性、傳播范圍廣等特點也使網絡誹謗問題日益突出,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13年9月10日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對誹謗罪進一步細化,增強了可操作性的同時,其一至四條的出臺也引起了廣泛爭論,主要涉及三個爭議焦點:第一,“轉發誹謗”是否是對法律的僭越;第二,僅以數字劃分來認定“情節嚴重”是否過于僵硬;第三,以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是否具有法律依據。而本文將對這三個問題進行詳細解讀,并與國外網絡誹謗罪的規制作對比,更好地幫助民眾理解其存在的積極意義,同時加以借鑒,并對我國網絡誹謗罪如何完善提出幾點建議。
司法解釋;網絡誹謗;國外法律
一、對網絡誹謗犯罪司法解釋的探討
根據我國刑法第246條的規定,“誹謗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某種事實,貶低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①兩高司法解釋的前四條所規定的網絡誹謗罪只是借助了網絡等新型大眾傳媒的特點,其本質仍然屬于誹謗罪,是對傳統方式構成誹謗罪的細化與補充。
(一)“轉發誹謗”是否是對法律的僭越
該司法解釋第1條將誹謗行為劃分為捏造誹謗、篡改誹謗和轉發誹謗三種情形。“所謂捏造,是指無中生有、憑空制造虛假事實,所謂篡改,是指以作偽的手段對原信息改動、曲解事實”。②刑法對誹謗罪規定的客觀構成要件為虛構或杜撰事實誣蔑第三人或他人,但該條第三款將轉發誹謗也作為“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使很多人針對其是否是對法律的超越產生了激烈討論。
很多民眾認為該款是對法律的創設:第一,從“捏造”的內涵講,其指憑空制造,因而認為第三款的明知而散布且情節惡劣不能作為捏造的一種新形式,若是將該規定加以合法化,不僅違背了司法解釋變更刑法原有規定的立法法規定,而且也會致使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案件突然激增;第二,從刑法的目的來講,刑法以懲治犯罪從而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秩序為目的,且我國的立法政策也越來越趨向非犯罪化,若是按該解釋第三款將其作為對“捏造”擴大解釋的合法化,那似乎與原本的目的本末倒置,反而突顯了懲罰,降低了犯罪門檻。但也有少部分的法律人士對此加以反駁,認為我們應當將“捏造”與“散布”結合在一起,放到具體案件中,比如說一個人捏造了誹謗他人的事實,若未向公眾散布,既未構成犯罪,也不會造成案件數量激增;而且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即使在網絡上也是有界限的,在面對新形式的犯罪平臺時仍應遵照罪刑法定的原則予以傳播。
(二)僅以數字劃分來認定“情節嚴重”是否過于僵硬
該司法解釋中特別受到人們關注的是“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認定為“情節嚴重”的規定。很多人對兩個“次數”產生質疑,并笑談被轉發499次后趕緊刪文。并指出“情節嚴重”一般是指進行誹謗的手段極其惡劣,產生的后果嚴重等,但是只要點擊、瀏覽5000次以上或轉發500次以上就算嚴重嗎?如果這樣的話,比起中國13億人口,就算人們平常看“貓撲”、“貼吧”等無意間瀏覽到的捏造的信息恐怕也早早超過了該解釋規定的次數,按此規定若再加上行為人是主觀上捏造的該信息,那必然是構成了刑法規定的誹謗罪。如若自訴的人多那必然會導致司法資源浪費以及更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但也有少部分的學者認為不應把焦點僅僅放在“5000”和“500”這兩個數字上,而應當關注到這個轉發量和點擊量背后對當事人所造成的影響,這兩個次數已對其名譽產生嚴重詆毀的后果;而且兩高也在該款出臺時說明這兩個數字是根據長期實踐所作出的。
(三)以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是否具有法律依據
該司法解釋第四條規定了“一年內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轉發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反對者認為該規定既不是累犯,也不是繼續犯,在法律上無法找到依據。“累犯是指因犯罪受過一定的刑罰處罰,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的期限內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③但顯然該規定是一年內多次誹謗他人行為未經處理;“繼續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對象的一個犯罪行為從著手實行到行為終了,犯罪行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狀態同時處于持續過程中的犯罪”,④但顯然該規定是說明了有多個實行行為。從刑法條文看,誹謗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屬輕罪,而司法解釋的規定卻放寬了入罪標準,并不符合要求。但也有學者認為將該條放到司法解釋出臺的背景來看并沒有創設法律,而是結合網絡新型犯罪的特點,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而進行的詳細詮釋。
二、國外對網絡誹謗的規制
通過對國外立法中關于網絡誹謗罪的規制,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該司法解釋的不足與優勢,并予以完善。
(一)美國對網絡誹謗罪的規制
美國在1962年的《模擬刑法典》中將誹謗罪歸入妨害公共治安罪。在美國法律中,誹謗罪也屬于輕罪。美國刑法對誹謗罪的對象并沒有嚴格限制,包括公司等社會組織,而我國卻要求是特定的自然人,可以看出我國在對待誹謗罪時立法方面比美國更加注重對不同的主體區分開來;此外美國刑法要求行為人需具有主觀惡意,該法認為“所公布材料的真實性或重復性不能作為否定惡意的辯護理由”。⑤而這又與我國新出臺的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司法解釋的規定不同,我國是鼓勵公民利用網絡進行反腐,但是對主觀故意捏造的信息卻顯示真實性的問題未明確說明,在實踐中也給執法者帶來一定困難,這也正是該解釋應予以完善的一點。但根據我國刑法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若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信息為真實的,那該誹謗者不應成立誹謗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刑法的謙抑性,也印證了該司法解釋正是對刑法誹謗罪的細化。
(二)英國對網絡誹謗罪的規制
英國《誹謗罪法》第4條規定:“明知誹謗內容虛假而惡意發布誹謗信息的,構成誹謗罪,處在普通監獄或者矯正所服不超過兩年的監禁刑,并處罰金”。⑥而我國新出臺的司法解釋對以“捏造事實論”的第三款正是與英國法律的規定相一致,并對抽象的誹謗罪加以細化。此外英國的普通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劃分規定為:“把誹謗罪作為嚴格的傳統責任犯罪。即法律并不要求控告方在審判中證明被告人犯罪的故意或過失,只要證明被告人實施了該犯罪行為并給被誹謗人造成了危害后果,就完成了舉證責任,法院就可以判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⑦將該規定與我國新出臺的的司法解釋相比,可以看出我國立法雖開始對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行為加大了公權力的介入,但在公民名譽權的保護上仍然弱于英國,這也是其不足的一點。
(三)德國對網絡誹謗罪的規制
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其對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法律規定與英美普通法制度既有相同點,也有其獨特的條文,特別是德國的誹謗罪在刑法中有所規定。“德國刑法在第186條規定了害惡的誹謗,第187條規定了中傷,第188條規定了對政治生活中的人進行的害惡的誹謗”。⑧我國新出臺的司法解釋與之相比有很多相似之處,該司法解釋雖然是關于網絡誹謗罪的,但其重點突出了主觀上的“犯罪故意”,也對關于利用網絡反腐作出了規定,其雖然并不是立法,卻體現了其規定上的進步意義。
對利用網絡進行誹謗行為的規制,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論法系,國際上各國都沒有再另設罪名,但均依靠誹謗罪對其加以規制。多數國家采用民法與刑法相結合的理論,即罪輕時依照侵權對被誹謗人進行賠償,構成網絡誹謗罪時納入到刑法誹謗罪的條款,當然也有美國這種只依靠侵權法來治理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行為。而我國利用網絡進行誹謗司法解釋的出臺,不僅借鑒了各國的經驗,更是重新界定了網絡誹謗的入刑標準,更好地區分公訴與自訴,切實保障被誹謗人與誹謗人各自的權利。
三、網絡誹謗的正確釋義及其完善
(一)網絡誹謗規定的正確釋義
1.對“轉發誹謗”的解讀
針對民眾對該款的質疑,筆者詳細進行分析詮釋其合理性。第一,針對“轉發誹謗”是否符合“捏造”的內涵,筆者覺得其是新型手段下的重新解讀。“捏造”在網絡等新型媒介上除了原本創造無中生有的事實外,也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即明知是誹謗信息依然傳播就相當于間接創造無端事實進行傳播。第二,從刑法的目的來看,該解釋第三款的出臺是為了在網絡環境下也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名譽權,在網絡等新型媒體傳播平臺上,由于其匿名性與傳播范圍廣的特點,我們很難認定誹謗信息捏造者和散布者,才會對明知是誹謗信息依然散布的情形納入該解釋中,而并非民眾認為的加重了懲罰。第三,筆者認為通常所理解的誹謗罪的構成要件即“捏造+誹謗”并非刑法條文上所直接規定的,而是理論上的通說,因而第三款的構成要件即“明知+散布+情節惡劣”并不存在任何對法律的僭越。第四,筆者認為該第三款的出臺還起到了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強調了“散布”這一客觀構成要件,更加突顯了其在誹謗罪中關鍵作用;二是通過將“情節惡劣”作為構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提高了該款的入罪標準,在保護公民名譽權的基礎上,也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實現二者的平衡,防止動輒以刑法引起恐慌。
2.基于實踐以數字劃分來認定“情節嚴重”
針對該司法解釋第二條第1款對情節嚴重的次數的限制,筆者認為:第一,從其在社會上的傳播來看,該條款只是對實際被瀏覽、點擊、轉發的次數進行了一個簡單的量化,而轉發后再次被瀏覽或轉發以及口頭傳播次數甚至可以到數以萬計,因而可以看出其影響范圍還是非常廣泛的,將該款列入“情節嚴重”的情形是體現了我國罪責刑相統一的原則。第二,我國誹謗罪屬于告訴才處理,即使行為人有捏造他人信息并加以散布的行為構成誹謗罪,只要被誹謗人認為其名譽受到損害的程度不大未提起訴訟,那么該誹謗人也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人們對于該條款的出臺可能加大受到追訴的誹謗案件數量的增多憂慮是多余的,其只會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塑造更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第三,以數字劃分來認定情節嚴重的規定,能夠在罪與非罪之間劃定一條清晰的界限,有效約束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使得執法機關在打擊網絡誹謗犯罪的時候堅持罪刑法定原則,防止出現執法機關在打擊網絡造謠行為的時候隨意升格法定刑⑨。
3.以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權益
通過對該解釋第四條以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規定探討,筆者認為該條是依據了刑法理論上徐行犯的規定。“徐行犯是指行為人基于一個犯罪故意,重復實施多個僅構成一個犯罪“行為”的危害舉動,這些舉動的總和僅侵害了一個確定的法益、觸犯了一個罪名的犯罪形態”。⑩就好像該條款規定的一樣,比如某甲今天在網絡上編造并散布他人的誹謗信息被轉發200次,下個月繼續在網絡上編造并散布他人的誹謗信息被轉發200次,第三個月仍然在網絡上編造并散布他人的誹謗信息被轉發100次的方法來侵害他人的名譽權,由于一年內次數累計已達到500次,根據誹謗罪的構成要件,其行為屬于以徐行犯的方式實施的誹謗罪。
(二)網絡誹謗犯罪司法解釋的積極意義
首先,該解釋出臺后的一系列案件中可以看出其“既為當前認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犯罪提供科學的、操作性極強的指南,又為檢察機關積極主動地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誹謗行為行使公訴權提供司法根據”。?
其次,在與國外關于利用信息網絡進行誹謗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們也應當看到其的合理性。在面對我國刑法對誹謗罪規定過于抽象的弊端,新出臺的司法解釋既參考了國外關于誹謗罪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國;也借鑒了國外關于誹謗罪的法律規定,例如英國;同時更是結合了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犯罪所獨有的特點,比如解釋中采用次數對情節嚴重的情形加以規定。
(三)對網絡誹謗司法解釋的完善
利用網絡進行誹謗的司法解釋的出臺,一直是對平衡公民言論自由權與名譽權的探索。但其仍然存在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予以完善。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該解釋對故意捏造并散布的行為予以制裁,對利用網絡反腐的行為予以鼓勵,但是對于故意捏造并散布但經查證屬實的信息是否構成誹謗罪卻并未規定,根據英國對誹謗罪的規定加以借鑒,筆者認為該行為構成誹謗罪,因為其雖然沒有侵犯他人的名譽權,但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主觀上存在犯罪故意其客觀上實施了捏造并散布的行為,不能因巧合結果來免于其不構成犯罪。其次,“網絡謠言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真實信息模糊,這與部分黨政機關信息公開程度不夠透明有一定的關系,治理網絡謠言,最有效的辦法是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能夠有效地運轉起來,謠言就會消失在‘陽光信息’下”。?再者,對于5000和500次的規定,根據德國刑法的規定應該改成排除惡意點擊或瀏覽后的次數達到這個標準后作為情節惡劣的情形,但是在實踐中卻不易操作,為了防止惡意實現點擊量,筆者認為可以改成IP量,有效防止次數惡意增加;最后,真正打擊網絡謠言需要我們全社會去共同參與,廣泛實施網絡實名制,同時加強對誹謗信息的管理與監督。
[ 注 釋 ]
①趙秉志.刑法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646.
②莫洪憲.打擊犯罪與保護言論自由并不沖突[N].檢察日報,2013-9-16.
③陳興良.刑法學[M].第2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264.
④陳興良.刑法學[M].第2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222.
⑤儲植.美國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263.
⑥謝望原.言論自由的法律邊界:不得誹謗他人[N].人民日報,2013-9-12.
⑦劉良凱.談談誹謗罪的舉證責任——對一起誹謗案件的分析[EB/OL].2009-12-17.http://china.findlaw.cn/bianhu/xsssfzs/xingshizhengju/yzzr/7761_3.html,2014-1-4.
⑧[德]Ausfertigungsdatum.德國刑法典[M].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58.
⑨賈文宇.司法解釋明確界限,依法打擊網絡造謠[N].廣西日報,2013-10-23.
⑩陳興良.刑法學[M].第2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224.
?謝望原.言論自由的法律邊界:不得誹謗他人[N].人民日報,2013-9-12.
?王新,張媛.整治網絡謠言:國外經驗與啟示[J].生產力研究,2012(10).
D
A
2095-4379-(2017)18-0035-03
劉丹陽(1992-),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2014級刑法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