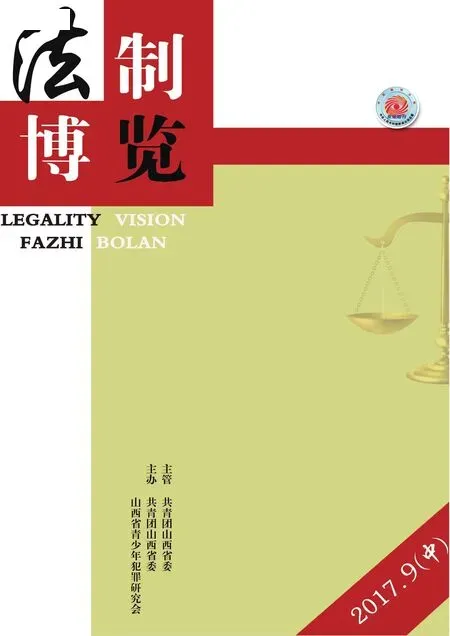淺析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的“徇私”
楊 磊
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100
淺析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的“徇私”
楊 磊
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100
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的“徇私”,應當理解為該罪的犯罪構成要素,且“徇私”應當理解為不僅僅包括自然人個人之間的私情或私利,也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
徇私;犯罪構成;司法實踐
我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犯罪中第四百一十八條雖然明確規定了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但由于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關于“徇私”的認定,在理論界本來就有較大的爭議,在司法實踐中原來也存在諸多的疑惑和困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徇私”的規定也不盡相同①,加之社會的不斷發展,教育、就業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司法實務中,一線偵查人員面對招收公務員、學生過程中各種各樣與時俱進的徇私舞弊手段和行為,在認定此罪時便有了更多的困惑。因為對種種“徇私”的準確定位,不僅僅直接關系到定罪中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等定性問題,還和量刑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為了更好的懲治該種犯罪,筆者立足于司法實踐從該罪“徇私”的內涵、屬性入手,淺談一下自己的認識,得出結論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徇私”的內涵
從理論界到實踐中,并觀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關于“徇私”的內涵的爭議焦點主要在于“私”的界定。一種觀點認為“私”應當是自然人個人之間的私情或私利,不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這種觀點的理由強調從文義解釋入手,依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名詞解釋,認為法條中的“私”若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就不符合刑法用語的邏輯;這種觀點還強調運用體系解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理由是“私”若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那么就與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的規定的罪名在法理上相互矛盾。
與之相對的是另一種觀點,認為“私”不僅僅包括自然人個人之間的私情或私利,也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本文同意這種觀點。理由如下:首先,犯罪的本質是具有法益侵害性,各種具體規定的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最終不管是為了徇個人之私還是集體、團體、單位之私,都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具體到本罪中,就是侵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招收公務員、學生工作中的公正、客觀性,侵害了社會大眾對國家機關權威性的信賴心理,所以說,徇個人之私還是集體、團體、單位之私,對最終法益被侵害并沒有影響;其次,任何事物都應該運用辯證法的角度去看待,所謂的公私分明,“公”和“私”是一個相對來說的概念,都是通過比較得出的誰是“公”和“私”,于集體、團體、單位而言,自然人個人是“私”的概念,于國家而言,集體、團體、單位又是一個“私”的概念,所以,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看也并不必然否認“私”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再次,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說,不管是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還是最高法關于上述注釋一的規定,如果只將徇私界定為個人之私,那么必然導致大量存在的以為單位謀利為名實則為自己謀利的瀆職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不能被依法懲處,不符合立法中設置這些特殊瀆職罪名的立法精神。
二、“徇私”的屬性
縱觀理論界和實務中,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中,“徇私”的法律屬性這個問題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爭議焦點,具體到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厘清了“徇私”的內涵后,還需進一步明確“徇私”是否是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的構成要件的要素?又進一步是屬于客觀方面還是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總的來說,理論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行為說,認為“徇私”的屬性排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徇私舞弊是加重情節,其余“徇私”的屬性是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但同時有學者指出行為說的一大缺陷,即作為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可能會把賄賂犯罪概括在內,輕罪如果包含了重罪,就是不可取的了。二是目的說,認為“徇私”的屬性是相關行為人的犯罪目的,不影響定罪,但是對量刑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該觀點強調所有的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都是出于直接的犯罪故意。三是動機說,認為“徇私”的屬性是相關行為人的犯罪動機,不屬于犯罪構成的要素。這種觀點強調“徇私”是一種內在主觀的心理狀態,具有隱蔽性和相當的不確定性,是一種驅使犯罪行為的動力因素,并且“徇私”也是在行為人開始犯罪活動之前形成。四是動機和目的說,該觀點強調“徇私”既是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觀方面,又是這類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具有主、客觀雙重屬性。
綜上所述,本文的觀點是在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中,“徇私”的屬性既是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也是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換言之,具體到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徇私舞弊是該罪的犯罪構成,且具有主、客觀雙重屬性。理由是:首先,我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在刑法條文中對罪狀的描述,不僅是對具體罪名的犯罪構成和量刑的類型化歸納,也是將罪狀的功能在惜字如金的法條中發揮出來。雖然不排除一些具體的法條中罪狀的描述是起到語感的作用,但本文所要討論的罪名中,徇私舞弊顯然不屬于起語感作用的描述;其次,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罪刑法定原則,堅持“徇私”是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犯罪構成要素,才能不違和罪刑法定的立法精神;最后,徇私舞弊不論是從理論上的解釋,還是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在體現出行為人主觀的心理狀態即犯罪故意的同時,也概括表達了行為人為實現主觀故意所實施的具體行為。因此,本文將“徇私”認定為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構成要件,并且同時屬于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
三、司法實踐中“徇私”的認定及建議
通過本文前兩部分的分析,作為檢察機關的一名偵查人員,在司法實踐中,在辦理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時,具體到認定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徇私”的案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入手:
首先,從“為誰徇私”的角度來說,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中的“徇私”,應當理解為不僅僅包括自然人個人之間的私情或私利,也包含集體、團體、單位之私。
其次,從“徇什么私”的角度來說,既然上文明確將“徇私”認定為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構成要件,并且同時屬于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那么就得有一個證明的標準,換言之,“徇私”在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存在“可證性”比較小的通病下,這些私情、私利需以什么形式出現、從證據的法律角度看偵查人員需取得證明力到何種程度的證據?本文認為,私情既包括積極方面的情感,諸如為徇親情、友情、愛情等正面積極尋求的感情因素,也包括消極方面的情感,諸如排擠、報復、泄憤等負面的感情因素;私利也不能僅僅理解為一定的金錢、物質利益,也包括非金錢、物質利益,諸如政治利益中的入黨、職務升遷、崗位調動等,榮譽、名譽、就業、入學等非金錢、物質利益,且私利不僅包括眼前的各種利益,還應當包含未來的一些可期待利益。當然,本文只是采取了列舉式的方法羅列了一些司法實踐中可能會遇到的,可以算是行為人獲利的因素,當然不包含證明標準的所有情況。
最后,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尚且不統一的規定,本文從立法的角度建議,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徇私”的范圍,出臺具有指導意義的“徇私”證明標準,在避免理論界爭論的同時,明晰司法實踐中一線辦案人員的困惑,增強實踐的可操作性,既能夠打擊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也能保證在就業、入學壓力越來越大的當前社會,招收的公務員、學生都是通過公平公正的途徑,競爭后擇優錄取,揚社會正氣,凈校園風氣。
[注釋]
①法[2003]167號文件<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第六章第四條關于“詢私”的規定明確地將徇私界定為個人之私;高檢發研字[1999]10號文件<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査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第二部分第十項解決了徇私是否包含詢單位之私.其中規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牟取本單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節嚴重的,應予立案”,非常明確地界定了徇私應當包含單位之私.
[1]張嬌.招收學生、公務員徇私舞弊罪立法研究[D].甘肅政法學院,2014.
[2]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余凱冰.簡析瀆職罪中“徇私”的涵義、地位與性質[J].法制與社會,2008(3).
[4]王俊鴿.淺議瀆職犯罪中的“徇私”[J].法制與經濟,2012(3).
D924.3
:A
:2095-4379-(2017)26-0136-02
楊磊,男,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