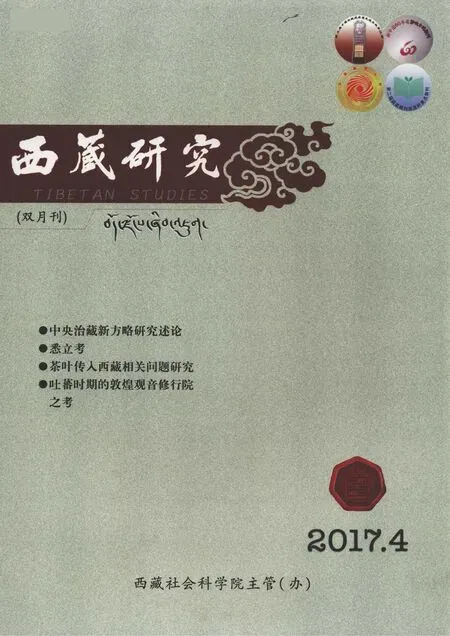傳統藏戲的開放性結構
袁聯波(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
2016-12-28
袁聯波(1971—),四川渠縣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戲劇戲曲學研究。
傳統藏戲的開放性結構
袁聯波
(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
傳統藏戲;開放性結構;故事性;連綴式;曠野
傳統藏戲大多采用了一種連綴式的故事編寫手法。為保證故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傳統藏戲往往會將故事發生的各種淵源交待得明明白白。傳統藏戲基本都是圍繞“一人”來敘述故事的,以“一人”為中心。在某些傳統藏戲中“一人”是由兩代人或夫妻二人相續完成的。在時間維度方面,傳統藏戲通過故事敘述的完整性、連貫性、單向性(“一次過”)等而顯示出一種明顯的開放性結構特征。在空間維度方面,藏族地區曠野中主要的景點幾乎全部被囊括,無所不包地被納入藏戲之中。歷史上藏族主要的人物類別,藏族地區常見的,甚至能夠想到的動物形象,幾乎都進入了傳統藏戲之中。
一
一般而言,“戲劇時空特性直接影響到戲劇結構”[1]。無論是時間維度還是空間維度,傳統藏戲都呈現出一種明顯的開放性結構特征。有研究指出,開放式戲劇結構特征表現為,“按照事件、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展開劇情,人物較多,劇情展開的時間較長,場景富于變化,情節更為豐富、曲折;回敘成分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可以沒有回敘成分。這類劇作的長處是有頭有尾,能夠容納具有較大廣度的生活材料。”[2]這里盡管談的是話劇的特征,但是各種樣式的戲劇結構呈現出來的基本特征是大體一致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傳統藏戲時間維度上開放性結構的特征:完整性、連貫性、單向性。
藏族民眾喜愛聽故事,藏民族有著極為豐富的說唱藝術和民間故事。“聽故事”在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也成為了民眾一種重要的娛樂方式。講故事與聽故事逐步成為藏民族一種傳統的文化習慣。傳統藏戲內容大部分改編自佛經故事。這些使傳統藏戲極為重視故事,故事性也成為傳統藏戲的一個重要特征。故事性主要體現為故事的完整性與連貫性。傳統藏戲大多都很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完整性在傳統藏戲中體現得十分鮮明,藏戲故事的開端、發展、結尾都交待得完整清楚。這既同藏族民眾欣賞習慣有關,也與佛教主題表達有關,傳統藏戲結尾時都會“善惡有別”地交待劇中人物結局。連貫性特征也極為鮮明地體現在傳統藏戲故事之中。作為戲劇之一的傳統藏戲沒有像西方戲劇那樣,按照戲劇性要求對故事進行重組和加工,提煉出那些對戲劇性營造和人物刻畫更有利的元素,而扔棄那些多余的素材,從而使情節更趨集中凝練,而是十分重視故事的連貫性,注重給觀眾呈現出一個完整連貫的故事。顯然,在故事性與戲劇性之間,傳統藏戲似乎更偏重于故事性,盡管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關系。
西方戲劇十分強調矛盾沖突的集中性,要求在緊湊的時空內集中地展現戲劇沖突。西方戲劇通過對時間的壓縮,使戲劇的各種情節元素快速運行,戲劇性意味濃烈。戲劇的時空限制,“是為了簡化行動,慎重地從行動當中剔除一切多余的東西,使其保留最主要的成分,形成這種行動的一個典型(ideal)”[3]。而傳統藏戲,“比較偏重于生活本身的邏輯而并不拘泥于戲劇結構所要遵循的一般原則。戲劇的開端、發展、結局也大體上按生活發展的邏輯和情理去構思、鋪排。從這一意義上說,它更接近于生活本身甚至以自然主義的描繪來保持藏戲特有的樸素風格。在著名的八大傳統藏戲中更是如此,它們一般并不追求跌宕有致的情節和復雜曲折的‘中心事件’,而是更多地注重事件發展是否符合生活邏輯的合理性。”[4]不難看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戲劇模式。
傳統藏戲大多敘述的是修行者“放逐與回歸”的故事,修行者在世俗社會所經歷的種種遭遇直至被放逐,以及放逐途中的各種苦難經歷,是戲劇重點表現的內容。八大傳統藏戲中的智美更登、云卓拉姆(即諾桑王子)、卓瓦桑姆(即王子、公主)、頓月與頓珠、蘇吉尼瑪、白瑪文巴等莫不如此。智美更登、云卓拉姆、卓瓦桑姆、頓月與頓珠、蘇吉尼瑪都有過被放逐的經歷。國王準備除掉白瑪文巴,于是安排他去險地尋找寶物,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放逐。盡管他們的性格大多偏于克己寬人、忍耐內斂,幾乎從不主動作出帶有攻擊性色彩的事情。而戲劇發展基本是按照他們的經歷安排的,以其行程和經歷組織情節結構的,同時各種外部助力的大量介入,這些使傳統藏戲呈現出一種開放的結構形態。
傳統藏戲大多采用了一種連綴式的故事編寫手法。為保證故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傳統藏戲往往會將故事發生的各種淵源交待得明明白白。換言之,即是在劇情的戲劇性意義上的開端處朝前縱向“回溯”,盡可能地將各種緣由梳理清楚。如《諾桑王子》中,戲劇性意義上的開端應該是云卓拉姆嫁給諾桑王子,然而戲劇意圖交待清楚云卓拉姆為什么會嫁給諾桑,這樣就牽涉到獵人用捆仙索“捉住”云卓拉姆一事,這一事件又涉及到獵人的捆仙索是怎么得來的這一問題,而這個問題又關聯著獵人幫助龍宮一事,那么接著的問題就是為什么龍宮會請獵人幫助,于是便引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戲劇開端。這里是一種典型的傳統藏戲的故事連綴法,力圖按照故事原本的邏輯將戲劇“還原”到它初始的起點。這種連綴和還原,使傳統藏戲具有意味濃烈的故事性,不疾不徐,娓娓道來。但是從戲劇性上講并無多大實質性價值,屬于“冗余性”素材。這里戲劇性意味被分散了,而故事性意味得以凸顯。
傳統藏戲中為了讓故事更具“合理性”,往往也會運用連綴法。譬如為了讓兩個身份以及物理距離等都相去甚遠的人見面,或者讓人物卷入原本不應該被卷入的事件之中,戲劇會為此安排一系列的事件,從而使故事發展更具“合理性”。《卓瓦桑姆》中,國王帶領大臣和百姓到東方山頂去打獵,結果國王的寶貝獵狗丟失了,于是大家露宿山頂為國王找獵狗,找尋中在一住戶門前發現了狗的腳印,接著進屋搜查,搜查中打開了一緊閉的房門,于是發現了仙女卓瓦桑姆。國王住在王宮,而卓瓦桑姆住在森林中,為了讓兩人能夠見面進而結緣,于是戲劇安排了這一系列的事件。《蘇吉尼瑪》中,因宮內屢次出現兇事,國王便派獵人看守花園。一天獵人看見一群野豬在園中糟蹋花木。獵人便追趕野豬,半途遇見一只香獐子,獵人放棄了野豬追香獐子,后又遇見一只麋鹿,獵人又放棄香獐子,緊追麋鹿。于是迷路的獵人便遇見了蘇吉尼瑪,從而引出了國王與蘇吉尼瑪見面結緣的情節。《頓月頓珠》中,某天頓珠下山,在山谷口看見許多牧童在玩游戲,他便同大家一起玩耍。“一起玩耍”引出了頓珠“力氣大”事件,而“力氣大”又引出了頓珠是“屬龍的”,從而引出后文國王抓他祭祀龍神的情節。
無論是縱向“回溯”故事發生的各種緣由,還是為了使故事發展更具“合理性”而安排的一系列的事件,都鮮明地體現了傳統藏戲連綴式的故事編寫手法,這些是為藏戲故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服務的。這種連綴式的敘述手法使傳統藏戲具有鮮明的故事性特征,牽出了更多的人和事,使戲劇生出了更多的枝蔓,也使其形成了一種開放式的戲劇結構形態。
傳統藏戲基本都是圍繞“一人”來敘述故事的,以“一人”為中心,圍繞在他周圍的有對手或者敵人、幫手和助力等,以此展開戲劇情節。在某些傳統藏戲中“一人”是由兩代人或夫妻二人來完成的:《卓瓦桑姆》中卓瓦桑姆飛升而去之后,這“一人”轉移到兒子身上;《白瑪文巴》中商人諾桑也死去,但該劇重點本就是兒子白瑪文巴;《諾桑王子》中,云卓拉姆被逼走后,“一人”轉移到作為丈夫的諾桑身上。傳統藏戲的敘述視點大多是隨著“一人”而轉移的。如《白瑪文巴》中,商人諾桑被國王迫害之后,白瑪文巴被母親放在家中偷偷地帶養,但是隨著白瑪文巴逐漸長大,國王仍然發現了他的存在。國王運用對付他父親的辦法再次指派白瑪文巴去海上取寶,在空行母密咒的幫助下白瑪文巴安然回歸。國王不甘陰謀失敗,再次要求他前往羅剎國取寶,在空行母密咒的幫助下白瑪文巴再次安然回歸。該劇中,白瑪文巴不斷地轉換地點,戲劇視點也隨之轉換。
由于“一人”為主線基本貫穿全劇,傳統藏戲形成了一些與此相關的特征。首先是人物形象重于人物性格。這里我們需要區分一組概念:性格與形象。傳統藏戲往往圍繞“一人”展開故事,從不同方面豐富著人物的“形象”,但是這種形象很大程度上并非戲劇意義上的“性格”。人物“性格”刻畫需要將人物置于不同的戲劇情境之中從不同方面去加以剖析。傳統藏戲大多鋪陳了“一人”做了什么事,故事展開過程中“一人”事實上的確做了很多事,但是沒有充分展示他們為什么要做這些事(即使敘述了為什么做,也更多地是從人物意志化了的宗教信仰角度思考問題,而非感性和本性的自然流露),尤其是對剖析他們的內心世界程度不夠。傳統藏戲極為重視故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故事的邏輯不斷地推動著“一人”前行,沒有更多的停留,通過更多的“場面”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這些使得傳統藏戲呈現出一種極為鮮明的開放性結構特征。其次是形成了一種“傳奇性”特征。故事隨著“一人”的行動而不斷地轉移敘述視點,這些地點很多為兇險之地。“一人”放逐途中發生了許多奇事,遇到了一些奇人,故事離奇曲折。如頓月死的時候山岳震動、仙樂奏起,頓月的死而復生;白瑪文巴被羅剎吃后又吐出來;頓珠能夠自由往返于人間和龍宮,而且能夠說服眾龍改邪歸正等。
傳統藏戲中的故事大多是“一次過”的,隨著“一人”的歷程而不斷地變換敘述視點。除他們“回歸”,“一人”同以前的人和事再次“相遇”的并不多見,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單向性”的敘述特征。如《頓月頓珠》中,頓珠被后母裝病趕走之后,兄弟二人一路艱辛,頓月死后,頓珠繼續前行,后來拜老喇嘛為師,再到因屬龍而被抓去祭祀龍神,再幸運地活著從龍宮回到人間,因隨同師傅去王宮而被認出,隨之與公主結婚,作了這個國家的國王,再后來找到了死而復生的弟弟,接著與弟弟頓月一同回歸看望父親,戲劇也以“大團圓”結局。頓珠遇到了不同的人,也做了很多事。這些事情很好地塑造了頓珠的形象,如放逐途中,突出了頓珠忍受艱辛和苦難的一面,龍宮一幕凸顯了頓珠舍己利他的精神等。而這些事情大多為“一次過”的。當然一些傳統藏戲也敘述了再次“相遇”,并且將再“相遇”描寫得比較生動感人,這是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形象刻畫的需要。如頓珠從龍宮重回人間再次見到師傅,尤其是與深愛著他的公主再次相遇,都描寫得很感人。
毋庸置疑,傳統藏戲中不少人物都是“一次過”的,出現一次便不再出場,而這恰恰也是很多開放性戲劇的特征。傳統藏戲中出現了很多人,而真正的中心則是“一人”,其他人更多是作為故事展開必要的輔助性“元素”而出現的,他們共同為戲劇的展開營造出了戲劇發生和發展的情境。從這個角度而言,傳統藏戲中一些“冗余性”的人與事也體現了其在劇中的存在價值。但是盡管如此,傳統藏戲原生態的故事式樣無疑是以犧牲戲劇性為代價而形成的。在時間維度方面,傳統藏戲通過故事敘述的“完整性”“連貫性”“單向性”(“一次過”)等而顯示出一種明顯的開放性結構特征。故事敘述中主要事件并不比次要事件分量重多少,主要事件被大量的次要事件所沖淡,敘述的整體態勢非常平緩地向前推進,而沒有形成明顯而集中的戲劇焦點。但是由于“一人”的行動主線清楚明白,次要事件都是緊緊圍繞“一人”來展開進行的。所以盡管敘述事件很多,結構很開闊,但是在“一人”、故事主線及主題思想的統攝下而不至于散亂無章。
二
傳統藏戲的開放性結構不僅體現在“時間”上,而且也表現在空間維度方面。如前文所說,傳統藏戲基本都是圍繞“一人”來敘述故事的。“一人”被放逐之后的活動范圍很廣闊,并且不少是在曠野展開的。“曠野”也是展示“一人”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八大傳統藏戲中關于曠野的景點有:遠洋、海邊、海島、邊荒、森林、村莊、草原、沙灘、大山、草壩子、廟宇、池塘、山洞、樹底、平壩、山谷、湖中、草堆、船中、河道、橋梁、茅棚、沸血海、懸崖、冰天雪地、城郊、蚊子谷、猛惡林、毒蛇山、荒山、海上、神塔、羅剎國、鐵水鑄成的地方、荒原,等等。藏族地區曠野常見的和主要的景點幾乎全部被囊括,對這些景點稍作分析,可以發現它們的壯闊性及兇險性。這些景點中很多是藏民族生產生活中常見的地方,如山川湖海、草原平壩、懸崖山谷以及廟宇佛塔等,也有一些想象虛構的地點,如沸血海、羅剎國等。這些景點很多是不同傳統藏戲中“一人”的親歷之地,戲劇的視點也隨著他們的行動在這些景點之間轉換,使戲劇在物理空間層面形成一種鮮明的開放性結構特征。同時“一人”親歷這些景點,尤其是其中不少為艱難和兇險之地,也使戲劇具有了“傳奇性”特征。
傳統藏戲不僅物理空間極為開闊,而且描寫的人物類別和涉及到的動物也十分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傳統藏戲中描寫到的人物類別主要有:國王、王后、巫師、獵人、漁夫、屠夫、隱士、大臣、百姓、王子、公主、仙女、馬頭明王、山神、野人、嬪妃、婆羅門、奸臣、部落酋長、仆役、鬼怪、大梵天、空行母、菩薩、夜叉、乾闥婆、妖魔、商人、閻王、聾子、瞎子、羅剎、喇嘛、云游僧人、乞丐,等等。這些人物有現實生活中的,也有宗教中的。傳統藏戲中涉及到的動物(及動物神靈)主要有:鹿、天馬、犀牛、大象、神牛、鸚鵡、麋鹿、野豬、香獐子、豺、狼、虎、豹、神龍、龍王、杜鵑、夜鶯、猴子、猿、駿馬、獵狗、巨鷹、羊、烏鴉、熊、牦牛、鷺鷥、鵝、孔雀、天龍、螞蟻、雞,等等。不難發現,那個時期藏族主要的人物類別,藏族地區常見的甚至能夠想到的動物,幾乎都進入了傳統藏戲之中。從而形成了傳統藏戲極為龐大豐富的形象(廣泛意義上的形象)體系。
獼猴為傳說中藏族的始祖。有學者認為,《諾桑王子》中烏鴉給諾桑傳遞訊息同藏族崇拜烏鴉的習俗有關。敦煌藏經洞的藏文文獻記載了吐蕃對烏鴉的認知:“烏鴉系人的怙主/傳遞仙人圣旨/藏北系牦牛之鄉/于該地之中央/它傳遞圣旨/翱翔飛忙……烏鴉系神鳥/飛禽展雙翅/飛到神高處/目明耳又聰,它精于神靈秘法/無一不能通達……”在藏族人們的意識里,烏鴉為神物,具有先知先覺的作用[5]。藏族先民在古老的創世歌中唱道:“最初斯巴形成時,天地混合在一起。分開天地的是大鵬,大鵬頭上有什么?”在另一組異文的答歌中說:“大鵬把天撐高空。”這里實際上暗示著它是藏族創造世界、辟開宇宙的文化英雄[6]。尊狗的習俗到目前為止在藏區還存在。白馬藏族每當新年正月初一凌晨雞叫頭遍,各家門前點一堆火敬神,祝農業豐收,然后到井邊取水,向屋內外灑水,呼喊祖先并唱水歌。此日先喂狗,以示對狗的尊敬[6]。各種動物崇拜在藏民族文化中十分盛行。在藏族民眾那里,人與動物是伙伴、朋友關系,人與自然以及自然界生物之間是一種和諧共存關系。正因為如此,各種動物形象才大量地出現在傳統藏戲中。
隨著“一人”視點不斷地轉移,如此龐大豐富的形象體系鋪陳在極為開闊的景點,開闊的景點、流浪漢式的敘述視角使傳統藏戲形成了開放性的結構形態。“藏戲的舞臺是放射性的,可以把藝術空間射到客觀世界每一個角落,把時間延伸到每一個瞬間,在小小舞臺(或場地)上,可以‘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7]“三世”“輪回”觀念以及三界之間“互相貫通”的神話時空的介入,會同開闊的現實時空,使傳統藏戲形成了極為豐富而開闊的結構。這是藏民族豐富而廣闊的想象力的藝術成果,它又反過來滋養著民族的文化和民眾。
傳統藏戲在演出正戲之前,往往會安排一些歌舞表演,這樣一方面可以活躍氣氛、聚集觀眾,同時也讓劇團和演員同觀眾見面。表演過程中,觀眾圍繞四周觀看,表演形式十分隨意。傳統藏戲表演時設有一名劇情介紹人,一般是由劇團的團長兼任。他介紹劇情發展,掌握著全劇表演的節奏。劇情介紹人根據演出現場的具體情況可以隨時對表演進行適當的調整。戲劇表演過程中什么地方需要重點突出,什么地方可以簡略處理,或者一筆帶過,都由劇情介紹人掌控。可能在戲劇發展到最激烈緊張的時候,穿插一段與劇情完全無關的民間歌舞演出,甚至可以在演出過程中安排穿插與劇情毫無關聯的即興式表演。同時由于傳統藏戲大多取材于佛經故事,某些情節無法直觀地展現出來,劇情介紹人的敘述可以填補其中的缺失部分,從而使故事顯得連貫和完整。表演過程中,演員可以隨便喝茶聊天,觀眾可以在欣賞表演的同時喝茶品酒,吃著酸奶子。由于對于劇情觀眾大多已經耳熟能詳了,他們似乎更多地是在欣賞演員的藝術表演,這一點同漢地的京劇觀眾很相似。
傳統藏戲表演中的劇情介紹人極具特色,是其他戲劇表演形式中所沒有的。因為劇情介紹人的引導,傳統藏戲的演出可能每次都不完全一樣。劇情介紹人也成為了事實上的臨時性的導演與編劇。事實上就是因為傳統藏戲的開放性結構,長篇史詩式的篇幅內容,故事情節的相對松散,劇情介紹人才能夠每次根據不同的情況而進行取舍和調整,進行不同的裁剪和整合。這種藝術處理方式每次都可能為觀眾提供不完全一樣的演出版本,讓觀眾得到不完全一樣的審美享受。在“規范”與“即興”之間獲得了無限的藝術可能性,使傳統藏戲呈現出另一種意義上的開放性結構。但是這也對劇情介紹人的藝術感知能力和把控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每次中途對劇情打斷,加入一些歌舞表演,尤其是一些即興式的表演,事實上也會破壞戲劇的藝術完整性。而這似乎恰恰也是民間表演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傳統藏戲開放性空間結構,因在廣場演出,沒有舞臺的限制和規范,也催生出戲劇的一些其他藝術特征。譬如廣場空曠的場地、自由隨意的觀戲情境等都對演員表演藝術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演員必須以高亢嘹亮的嗓音、幅度較大的表演動作進行演出,以此來引起觀眾的注意或者讓觀眾能夠清晰地接收到表演的相關信息,這也促使傳統藏戲形成了獨特的豪放粗獷的藝術風格。
[1]朱棟霖等.戲劇美學[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99.
[2]譚需生,路海波.話劇藝術概論[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75.
[3][英]萊辛.漢堡劇評[M].張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241.
[4]韋芝.淺論藏戲的結構特色[J].藝研動態,1986(2).
[5]邢莉.藏戲與藏族的民間信仰[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
[6]林繼富.藏族本教信仰中的古老崇拜[J].青海社會科學,1992(4).
[7]劉志群.我國藏戲與西方戲劇的比較研究[J].西藏藝術研究,2006(4).
TheOpenStructureofTibetanTraditionalOpera
Yuan Lian-bo
(The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ofChengdu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21,China)
Traditional Tibetan Opera;Open Structure;Story;Cluster;Wilderness
Cluster type of writing technique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Tibetan opera.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story,the traditional Tibetan opera stories tend to illustrate the background and origin of the story comprehensively.The opera is developed around “one person” and take that as center of the story.The “one person” is made up of two generations or one couple in some operas.The open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Tibetan is opera embodied by its nature of integrity,coherence,unipolarity of story-telling in terms of time dimension.The operas also integrate wilderness and landscapes of Tibetan plateau in terms of spatial dimensions.Therefore,one can easily find historical figures and animal images in Tibetan operas.
J825
A
1000-0003(2017)04-0126-05
[責任編輯:劉乃秀]
[責任校對: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