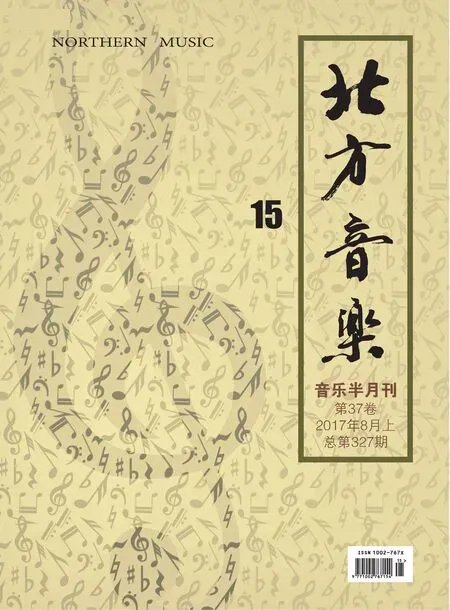音樂教育中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周 怡
(海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音樂教育中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周 怡
(海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創造力,是推動一個社會物質、精神文明前進的重要動力。與其它學科相比,音樂在激發人的潛能和創造性方面有非常明顯的效果。文章提出通過創設問題情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重視音樂實踐,營造創新情景;多維度的創作評估三方面,在音樂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音樂教育;創造性思維;評價
創造力,是推動一個社會物質﹑精神文明前進的重要動力。法國文學大師羅曼·羅蘭指出:“生命的第一個行動是創造的行為。”[1]馬斯洛也認為“創造性是每一個人生下來就有的繼承特質。”[2]創造力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創造的力量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辭海》上對創造力的解釋是:“對已積累的知識和經驗進行科學的加工和創造,產生新概念﹑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3]心理學界對于創造力的定義,存在著一些爭議,從不同的角度對創造力進行解釋。目前,人們主要從創造過程﹑創造主體和創造產物三個視角來定義創造力。大多數對創造力的定義是從創造力的結果入手,把創造力定義為人們根據一定的目的,運用已知的信息,產生出某種新穎﹑獨特﹑有社會和個人價值的產物的能力。[4]
音樂教育中創造性思維的培養,是音樂學與創造學的交叉學科。探討如何在音樂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不但是有意義的,而且是必須的。筆者認為在音樂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創設問題情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韋伯斯特認為,創造力涉及一組可能性的條件(包括動機﹑聚合—分散思維﹑環境以及個性)和可能性的技能(包括音樂的資質﹑概念的理解力﹑技能﹑審美的敏感度),所有這些都與“產品目標”以及“創作性產品”的制作相互作用。在他的創造性思維的概念模型核心,他提出了兩種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導致了多樣的解決方法:發散性思維(導致了多樣的解決方法),聚合性思維(導致了單一的解決方法)。[5]創造性思維便是與發散性思維相聯系的。那么,在課堂上如何激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產生創造性?“問題”是一把開啟創造之門的最好鑰匙。科學地提出問題,激活學生的發散性思維,使之進行創造性地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是創造性產品得以產生的核心內容。皮亞杰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也認為:學生只有在尋找答案時,學習效果最好,教師應該促使而不是指導學生學習。
二、重視音樂實踐,營造創新情景
“關注音樂實踐”已經成為國際音樂教育改革的一個焦點。美國著名音樂教育家﹑哲學家戴維·埃里奧特在《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一書中提出了語境中的音樂創造力系統。他的音樂創造性包含以下幾方面:音樂實踐語境﹑創造性音樂成就﹑創造性音樂制作者﹑音樂成就﹑音樂制作和音樂制作者。他認為:音樂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人類行為,也是具有多樣性的人類實踐活動,音樂教育的本質和意義取決于音樂自身的本質以及音樂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埃利奧特還認為:音樂創造力的發展要求營造一個鼓勵冒險和對于學生們創造性成就進行建設性評估的可接受環境。教師應該鼓勵學生們研究并選擇有創新的音樂作品來自己表演或者在自己的樂團中表演;產生詮釋的﹑即興演奏的和(或)作品的問題的解決辦法;產生音樂改編的計劃和草稿;編輯給定的作品或改編。[6]
認知心理學認為,思維是由一些不同的過程或操作組成的,將新的經驗或過程融入個體認知結果的過程,形成了這些經驗的意義。[7]學習過程是有機體積極主動地形成新的完形或認知結構,強調刺激反應之間的聯系是以意識為中介的。每個學生作為一個有獨立意識的個體,不應當被外界環境被動地﹑消極地﹑機械式地決定,應該具有積極的創造性和主動性。音樂實踐,正是尊重學生的主觀意識,讓他們把自己的理想﹑愛好﹑興趣﹑追求﹑需要和個性付諸于行動的最佳途徑。
音樂實踐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課堂上以學生為主體的音樂活動﹑各種晚會﹑比賽﹑音樂團體的活動……這些實踐活動,都對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具有積極的意義。美國20世紀初具有影響力的兒童音樂教育家薩帝斯·科爾曼(Satis Coleman,1878-1961)認為:兒童天生就具有熱愛和探索音樂的傾向,只是這種傾向由于后天非自然的強化和訓練或是無情地打擊,大多無法繼續保持,慢慢被限制甚至被扼殺。科爾曼推崇兒童主動學習音樂,孩子想唱就讓他們大膽地唱﹑愉快地唱,不能加進過多人為地﹑世俗地干擾,不能以犧牲兒童的學習興趣﹑個性﹑人格和尊嚴為代價去實現所謂的目標,“兒童從音樂學習一開始起,就要多給兒童自由表現的機會。”[8]這種“表現機會”就是一種音樂實踐,這種實踐能讓兒童內在的精神生活自然地抒發宣泄出來,有利于兒童個性和創造性的發展。
三、多維度的創作評價
傳統的音樂教學評價體制,往往是對學生某一方面的音樂才能進行評價,對所有學生(無視他們的個體差異)采用一個標準進行學習評價。傳統教學評價在測驗設計中具有預見性﹑精確性﹑客觀性和一律性,而創新和個性發展的評價系統具有非預見性﹑模糊性﹑主觀能動性和多元性。[9]無疑,傳統的教學評價無論是在信度還是效度方面,都難以對創造性思維做出合理的評價。創造性思維的評價,是超越對已知藝術問題的信息提取或簡單反應,主要把對象定位在學習者面臨音樂藝術課題時,在思維品質上所表現出來的敏捷性﹑流暢性﹑變通性﹑獨特性﹑深刻性,以及在原創觀念中體現出來的合理性。[10]
創新的教育評價應遵循整體性原則﹑導向性原則和可操作性原則,在教育過程的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評價方式。通常有:診斷性評價﹑發展性評價﹑過程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無論采取哪種評價手段,都必須注重評價系統的反饋——改進作用。[11]
埃利奧特認為語境下的音樂評價應該包括三個步驟:描述性﹑詮釋性和評估性。[12]新型的“像冊”式評價為此提供了可能。“像冊”式評價,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作為對學生藝術心理發展的形成性評價技術,用于哈佛大學加德納領導的“零點計劃”。20世紀90年代起,逐步延伸至美國教師教育的各個專業。其中,音樂教師教育對其響應是較強的。[9]“像冊”式評估的核心是建立學生的業績檔案冊。檔案冊主要包括書面材料﹑學生進步的聲像錄制品﹑各類表演資料等。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編制自己的業績檔案冊,將所有的信息進行組織和保管,并根據學生年齡﹑表演團體的內別等進行分類,以此印證和監控學生個體在學習過程中的成長。教師使用這樣的“像冊”,使學生和家長獲得足夠多的信息,便于他們對學生的學習給予客觀的評價,最大程度地有益于學生和教學。
除此之外,《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量》﹑《音樂能力傾向測驗》﹑《夸爾瓦瑟音樂才能測驗》等多種音樂能力傾向測驗也為多元化的評價方式提供了多種選擇。
四、結語
《本能的繆斯》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人類中的每一個成員與生俱來就具備創作的能力,也就是說音樂創作﹑音樂的創造性是人類的本能。[13]那么,作為音樂教師,如何喚醒學生的創造性本能,音樂創造性﹑創造性音樂教學是一個值得每一代學者永遠探討的話題。
[1]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
[2]馬斯洛.人的潛能和價值[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夏征農.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4]莫雷.教育心理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5]湯韻.P.伯德納音樂創造性研究對音樂教育的啟示[D].北京:中國音樂學院,2010.
[6][美]戴維?埃利奧特著,齊雪,賴達富譯.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9.
[7]Ausubel.D.P.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68,83(02).
[8]尹愛青.當代主要教學體系及教學法[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9]劉沛.傳統教育評價與素質教育的悖論及評價的換代方案——音樂教師教育的“像冊”式評價和動力學習范式[J].中國音樂,2004(02).
[10]劉沛.音樂成就測量與評價的認知主義方向[J].中國音樂, 2001(04).
[11]崔學榮.音樂教育創新的理論與實踐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2.
[12][美]戴維·埃利奧特著,齊雪,賴達富譯.關注音樂實踐——新音樂教育哲學[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9.
[13]讓·羅爾·布約克沃爾德,王毅,孫小鴻譯.本能的繆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G623.71
A
周怡(1980—) ,女,湖南長沙,碩士研究生,海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聲樂教學、音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