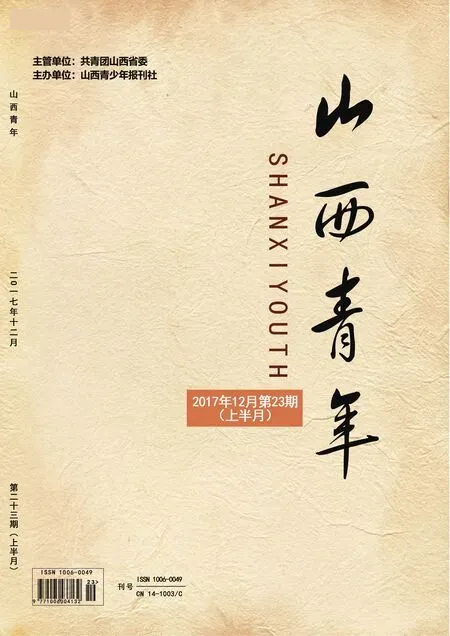中國古詩翻譯:不可譯性與補償策略
郭彥娜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29
中國古詩翻譯:不可譯性與補償策略
郭彥娜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29
中國的古典詩歌語言簡練、意蘊深遠,有巨大的文化魅力和審美價值。但是,中國古詩翻譯之難也是不爭的事實。本文討論古詩譯意過程中涉及的語內翻譯的困難,并重點從漢字藝術、語言、意象和韻律四個方面分析翻譯過程中產生的損失,提出可行的補償策略,旨在促進中國古典詩詞在西方的有效傳播。
古詩翻譯;不可譯;補償策略
一、引言
中國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其深厚的文化韻味和深遠的意境吸引著中西方讀者。18世紀,來華傳教士在其著作中就已經零星提及李白、杜甫的著名詩篇。19世紀中葉,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德埃爾韋·圣德尼侯爵翻譯的《唐詩》譯集出版,標志著中國古典詩詞在法國的譯介開始起步,并在20世紀進入了“全面開枝散葉的生長期”(阮潔卿,2007:3)。然而,中國古詩翻譯之難也是不爭的事實。漢學家畢來德曾細致地探討中國古典散文翻譯的過程,他認為:“翻譯同屬一種語族的兩種語言,似乎涉及的是文本的轉換。一般來說,從意大利語或者德語翻譯成法語不那么費力,因為我們懂得怎么樣轉換句子結構。可是,僅僅調整漢語的句子結構,很難產生好的翻譯。”(Billeter,2014:84)翻譯古典散文尚且不易,翻譯古詩則更加困難。首先,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以象征和音韻為基礎,詞語的外延和內涵在詩歌寫作中得到最大的靈活運用,甚至超出語言的一般規則,使詩歌的意義具有了無限性和開放性。這些特點很難在另一種語言中得以充分發揮,因此詩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譯性。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曾作如下著名斷語:“詩就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法國學者伯納富瓦(Yves Bonnefoy)也曾直截了當地評論道:“詩能夠被翻譯嗎?不能。太多的限制我們不能夠超越,太多的東西我們不得不放棄”(Bonnefoy,1990:95)。中國古詩以其簡練的語言、豐富的象征、嚴格的韻律和與西方文化的異質性,在翻譯中更容易損失詩意。
二、中國古詩的不可譯性
同任何翻譯一樣,詩歌翻譯經過理解闡釋原文和目標語重現兩個階段,涉及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語內翻譯是翻譯活動得以精確進行的初始環節,譯者在理解詩歌的意義與意境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受個人經驗和先在視野的限制,不同的譯者帶有不同的個人體驗,對詩歌的理解和感知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理解詩歌、重構詩歌文本的初始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于中國古詩翻譯而言,歷史的演變、文化的變遷和語言的內部畸變很可能成為語內翻譯的干擾甚至障礙。以許淵沖翻譯《詩經》為例。塵封散佚的歷史、晦澀難解的古語,造成《詩經》的語內翻譯的困難,要求譯者具有深邃廣博的知識,成為余光中所說的“學者加作家”。兩千多年的《詩經》研究,在《詩經》的文字、音韻、訓詁、名物、校勘、輯佚,乃至詩的背景和詩義的解釋方面,都積累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在語內翻譯階段,可為譯者所利用。首先,譯者需要準確理解詩經中數量眾多的生僻字、通假字。如《摽有梅》中的摽,“掉落”之意,翻譯為“tombé”(許淵沖,2008:16)。語內翻譯失誤直接造成語際翻譯的失敗。例如,《野有蔓草》尾句“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中“臧”字,許淵沖先生將“臧”(善,美;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譯為“藏”,因此將“nous nous plaisons”的句子誤譯為“Et nous cachons”(許淵沖,2008:56)。呂叔湘感嘆道:“以中國文字之艱辛,詩歌鑄語之凝練,譯人之誤會在所難免。”(呂叔湘,2009:128)。其次,譯者需要熟悉上古的風俗習慣或文化典故。比如,《衡門》一詩中,“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姜、子分別是齊、宋國貴族的姓,代指大戶人家的貴族女子。在經過語內翻譯之后,譯者選擇歸化翻譯法,處理為la grande famille和la riche famille(許淵沖,2008:96),即“名門望族”。文化差異對中國古詩翻譯的影響對于西方譯者而言更為顯著。文化缺省、文化負載詞以及地域文化下的語言認知差異都構成了中國詩歌翻譯的困難。在這個意義上,喬治·穆南指出:“中國文明距離我們如此遙遠,可以肯定地說,翻譯中國的文學和詩歌對譯者而言,失敗的幾率更大”(Mounin,1963:274)
在語際翻譯階段,中國古詩詞的形式的不可譯性主要體現在文字、語言、意象和韻律四個方面。第一,漢語主要是表意文字,法語是拼音文字,二者之間差異巨大。漢字的意象和形式美在表音文字中完全消失。例如,魯迅在七言律詩《亥年殘秋偶作》僅56個漢字中,有“蒼茫”、“菰蒲”、“荒”等5個帶有草字頭的漢字,突出了悲涼的秋和詩人惆悵的心緒。在翻譯中,要保留這種由文字所承載的意韻幾乎不可能實現。第二,漢語屬于分析語,單音多義,通過獨立的虛詞和固定的次序來表達語法意義,具有豐富的意境變化;而法語屬于屈折語,嚴格按照詞法、句法和章法組織,由性、數、格、主謂結構、時態語態等派生意義和邏輯。古詩詞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上,采用的語言體系是“在觀物和感興作用下呈露知覺世界的符號系統”(周紅民,2012:71),往往避免虛詞,僅通過簡單的實詞排列表達豐富的意境。在目標語重現階段,譯者很容易將簡練感發的古詩語言邏輯化,包括添加主謂結構、關聯詞等。例如,王維《竹里館》:獨坐幽篁里(Seul/assis/bambous cachés/dans)彈琴復長嘯(Jouer/cithare/et/longtemps/siffler)。單字翻譯結果不可讀,譯者程抱一根據法語語言規則,加入主語、動詞變位等方式將詩句“補充”完整。“Seul,assis entre les bambous,je joue de la cithare et je siffle”。詩句不可避免地被拉長,并且原詩渾然一體的詩化意境被邏輯分割。第三,意象是詩歌的基本要素,在中國古詩中表現的更為明顯。詩人講究含蓄的表達,借用意象言志寄情,所謂“意在言外”。正如袁行霈所言,“詞語的情韻是由于這些詞語在詩中多次運用而附著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詩歌的讀者,一見到這類詞語,就會聯想起一連串的詩句,這些詩句連同它們各自的感情和韻味一起浮現出來,使詞語的意義變得豐富起來”(袁行霈,1996:7)。比如,“柳”是傳統的送別象征,《詩經·采薇》中觸景生情,緣情寫景,將戰士出征前離別的感傷以及還鄉后物是人非的哀痛一并交織融合到充滿象征意味的畫卷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許淵沖譯為:“A mon départ/Le saule en pleurs”(許淵沖,2008:112)。在翻譯這類意象詞語時,譯者不得不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接受限制,選擇加“pleurs”(含淚)一詞,深化詞義,以達到傳情的效果。第四,音樂性是古詩最根本的特征。漢語的四聲構成了發音的抑揚頓挫,由于語音的特征,漢語詩歌講究“平仄律”。無論是古體詩還是格律詩,古詩的音樂性都是通過節奏和押韻表現出來。然而,“由于音美與語言本身固有屬性緊密結合,從符號學的觀點看,那部分僅僅依賴符號本身結構才能產生藝術效果的東西往往是不可譯的”(任鶯,2007)。
三、翻譯中的補償策略
中國古詩的形式、音律、意境和文化內涵在譯入語中必然有損失,這也是詩歌不可譯論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認,語言系統的差異導致兩種語言的抗譯性,然而,古今中西人類的情感共鳴和認知共通使詩歌具有絕對的可感可譯性。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提出翻譯的兩種方法:“或者盡量保持作者的安寧,帶領讀者接近作者;或者盡量保持讀者的安寧,帶領作者接近讀者”。異化和歸化是翻譯中國詩歌的兩種重要途徑。歸化法是譯者帶領作者接近讀者,即按照目的語詩歌的規則將中國古詩進行創造性移譯。詩“美”是歸化法的的主旨。許淵沖所譯唐詩正是歸化法的典范,取一首為例:
相思Lespoisd’amour
紅豆生南國 Les petits pois rouges de sang
春來發幾枝 Poussent dans le sud au printemps.
愿君多采擷 Je te prie d’en cueillir toujours:
此物最相思 Ils t’apporteront mon amour.(許淵沖,2008:30)
從詩歌形式上看,譯者將王維的五言絕句譯為法語中的十音節詩,并采用了AABB雙迭韻,讀來朗朗上口。古詩的形式和意義所損失的部分,譯者通過創造性的歸化譯法最大程度地加補償韻律和形式,使讀者能夠體會到原文的詩美。許淵沖認為:“如果譯詩做出一點犧牲,不那么意似了,但卻在更大程度上保存了原詩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總的看來,應該說是更忠實于原詩的,這就是我提出的三美理論”。
如果說歸化法通過創造性的移譯盡量還原詩美,那么異化法則是通過翻譯副文本(比如注釋、闡釋和批評等)最大程度地還原詩“真”。異化法的以嚴謹的深度翻譯補償詩歌翻譯中的意義損失,這也是19世紀以來法國漢學家翻譯中國文學的普遍態度。當代漢詩翻譯大家吳德明(Yves Hervouёt)認為:“用法語的十音節詩翻譯五言詩,或者更甚者,用亞歷山大詩體翻譯七言詩,這樣的做法對我來說很難想象。我認為譯詩首要的原則是準確性,應當盡可能直譯”(Coyaud,2009:20)。保羅·雅各布翻譯的《登幽州臺歌》采用了異化翻譯法:對這首簡短的古體詩,譯者附了三個長注釋,解釋古體詩和近體格律詩的區別,幽州臺的典故,“古人”和“來者”的內涵以及“天地之悠悠”的理解方式(Jacob,1983:28)。
歸化法的創造性移譯和異化法的深度翻譯都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中國古詩翻譯中意義和形式的損失。近年中國古詩翻譯常采用出版層面的補償策略,即采取法漢對照的辦法(尤其是漢語部分采用手寫書法)或者附上傳統書畫的形式,使讀者直觀的感受到文字之美,通過書、畫領略到詩的韻味。中國古詩的空靈簡潔、含蓄凝練以及意象音韻之美很難在翻譯中再現,但是譯者應盡量通過補償策略加以還原,使讀者能夠多方面體會到中國古詩的魅力。
[1]Billeter,Jean Fran?ois.Trois essais sur la traduction[M].Paris:Allia,2014.Bonnefoy,Yves.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1972-1990(M).Mercure de France,1990.
[2]Coyaud,Maurice.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classique[M].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09.
[3]Jacob,Paul.Vacances du pouvoir,Poèmes des Tang[M].Paris:Gallimard,1983.Mounin,Georges.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M].Paris:Gallimard,1963.
[4]任鶯.淺論中國古詩英譯的局限性[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5]阮潔卿.中國古典詩歌在法國的傳播史[J].法國研究,2007.
[6]許淵沖.翻譯的藝術[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
[7]許淵沖.精選詩經與詩意畫[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8.
[8]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9]周紅民.漢語古詩英譯的“感興”與“理性”[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1).
H
A
1006-0049-(2017)23-00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