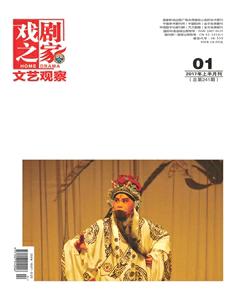國際電影節與二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電影互動
【摘 要】二戰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進入全面對峙的冷戰狀態。在此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蘇聯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這兩大社會主義國家舉辦的國際A類電影節,便成為了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國際電影交流與文化互動的主要平臺,發揮了傳播先進電影文化、塑造國家形象、建構社會主義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功能。本文主要以卡羅維發利電影節為研究對象,重點考察新中國電影在其中的獲獎情況及傳播策略,進而總結新中國電影海外傳播與互動的經驗啟示。
【關鍵詞】二戰;國際電影節;社會主義陣營;互動
中圖分類號:J99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004-02
一、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的重要特征
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A類電影節之一。1946年(第一屆)至1949年(第四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馬里安溫泉舉行,1950年(第五屆)起改在卡羅維發利舉行。1958年以前,除1953年和1955年未舉行外,每年舉行一次。1959年蘇聯創辦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后,為了與之交替舉行,便改為兩年一次,1994年之后又恢復為每年一次。第一、第二屆不評獎,從第三屆開始正式競賽與評獎,最高獎為“水晶地球儀大獎”。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通過“二月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最高政權,于是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開始由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電影部主辦。由于其屬于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電影節從此便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自由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確立服務于共產主義宣傳事業的目標,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盛會。關于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電影節的共產主義宗旨,電影節主席布洛烏希(Antonin Brousil)曾有過清晰闡述:“社會主義國家國際電影節的基礎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奠定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舉辦的國際電影節卻具有另外一種嶄新的性質。它們從開始舉行那天起直到現在,一直實現著鮮明的人道主義使命……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認為參加卡羅維發利電影節對自己是非常必要的。”[1]
概而言之,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有以下重要特征:第一,評委陣容方面,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評委構成了絕對主體,兼顧少量歐美國家的左翼電影藝術家。僅以中國為例,從1951年開始,中國電影藝術家們首次加入電影節評審團,此后共有水華、史東山、蔡楚生、王震之、田方、郭維、林杉等人擔任過評委。第二,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同時作為擁有輝煌電影傳統、電影藝術最為發達的東歐國家,幾乎包攬了每屆電影節的最高獎“水晶地球儀大獎”。據筆者統計,以1948-1962年為例,除了1948年第三屆和1956年第九屆之外,蘇聯每屆都包攬了大獎,分別是第四屆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第五屆的《攻克柏林》、第六屆的《金星英雄》、第七屆的《難忘的一九一九》、第八屆的《忠實的朋友》、第十屆的《勞動與愛情》、第十一屆的《靜靜的頓河》、第十二屆的《謝遼沙》、第十三屆的《一年中的九天》。第三,為了照顧其他各兄弟國家,電影節設置了明目繁多、略嫌泛濫的各類獎項。僅以1954年第八屆電影節為例,除了“水晶地球儀大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演員獎”“最佳女演員獎”等主要獎項外,還設置了眾多其他獎項:如“音樂片獎”“新的人們斗爭獎”“傳記片獎”“喜劇片獎”“勞動獎”“和平獎”“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斗爭獎”“爭取自由斗爭獎”“榮譽獎”“爭取社會進步獎”“報道片獎”等,分別由中國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捷克影片《姐妹們》《尤利烏斯·伏契克》《馬戲表演》、匈牙利影片《為了十四條命》、民主德國影片《恩斯特·臺爾曼傳》《河流的歌聲》、保加利亞影片《九月起義的英雄》《人之歌》、波蘭影片《我找到了真理》、日本紀錄片《五一節在東京》獲得。[2]
二、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對新中國電影發展的影響
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對傳播與塑造新中國國家形象具有重大意義,于此,目前還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認識。事實上,它對于新中國電影的國際亮相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0年與蘇聯交惡、斷絕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文化交流為止,從第五屆到第十三屆的12年時間內,中國在此電影節上每屆都有重要斬獲。1950年第五屆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上,新中國首次參加便獲得很大成功,共獲得兩項大獎:《中華女兒》榮獲“自由斗爭獎”,石聯星憑借影片《趙一曼》榮獲“最佳女演員獎”,標志著新中國電影海外獲獎零的突破;1951年第六屆電影節上,《白毛女》榮獲“特別榮譽獎”,《鋼鐵戰士》榮獲“和平獎”,《新兒女英雄傳》導演史東山獲得“特別榮譽獎”中的導演獎,《翠崗紅旗》獲得“攝影獎”;1952年第七屆電影節上,《人民的戰士》榮獲“爭取自由斗爭獎”,《內蒙人民的勝利》的編劇王震之獲得“編劇獎”;1954年第八屆電影節上,《智取華山》榮獲“自由斗爭獎”,《梁山伯與祝英臺》獲得“音樂片獎”;1956年第九屆電影節上,《桂林山水》和中、捷合拍的《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共同獲得“紀錄片獎”;1957年第十屆電影節上,《祝福》榮獲“評委會特別獎”;1958年第十一屆電影節上,達奇、王曉棠憑借《邊寨烽火》榮獲“青年演員獎”,中法合拍的兒童片《風箏》獲得“榮譽獎”,這也是新中國第一部合拍故事片;1960年第十二屆電影節上,《聶耳》榮獲“傳記片獎”,動畫片《蘿卜回來了》獲得“榮譽獎”;1962年第十三屆電影節上,動畫片《大鬧天宮》榮獲“短片特別獎”。
1962年以后,隨著中蘇關系的徹底破裂、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隔絕、以及“文革”的到來,中國基本上進入“閉關鎖國”的文化交流狀態,不再參加卡羅維發利等國際電影節,直至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才重新參加。1984年第24屆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上,史蜀君憑借《女大學生宿舍》榮獲“導演處女作獎”;1986年第25屆電影節上,《良家婦女》獲得“國際評論家獎”;1988年第26屆電影節上,謝晉的《芙蓉鎮》獲得該電影節最高大獎——“水晶地球儀獎”。
由于參賽影片代表著國家形象,因此新中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國際電影節的組織及選片工作。筆者認為,中方在國際電影節的選片方針及傳播策略可分為幾種類型:一是革命戰爭題材影片。如《中華女兒》《趙一曼》《白毛女》《鋼鐵戰士》《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人民的戰士》《智取華山》等,其中,《中華女兒》《趙一曼》《新兒女英雄傳》反映抗日戰爭;《人民的戰士》《鋼鐵戰士》《智取華山》反映解放戰爭,《翠崗紅旗》反映紅軍時期的斗爭。二是民族特色影片。少數民族題材影片頗受青睞,《內蒙人民的勝利》《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邊寨烽火》分別展示了蒙古族、藏族、景頗族的民族地理風情與優美的自然風光,它們的民族風情對渴望了解中國的外國觀眾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三是名著改編及人物傳記片。例如《祝福》改編自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無產階級大文豪魯迅先生的代表作,在國際舞臺上充分展示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風采;《聶耳》展現了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人民音樂家聶耳的生平事跡,使這個不朽形象受到國外觀眾的喜愛。四是戲曲片、動畫片、兒童片、風光片等類型。如《梁山伯與祝英臺》《蘿卜回來了》《大鬧天宮》《風箏》《桂林山水》等,呈現了優秀的中國古代民間傳說、英雄神話、戲曲文化等,打造了多元化的中國形象。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中國電影通過國際電影節進行了有效的國家形象傳播與塑造。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不僅見證了新中國電影的首次國際獲獎,也是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新中國電影的福地。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也曾有《老兵新傳》《小鯉魚跳龍門》《革命家庭》等不少中國電影獲獎。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陣營舉辦的國際電影節,起到了促進兄弟國家電影交流互動、推動各國電影事業發展、建構社會主義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功能,同時它們也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接受西方國家電影參賽,并與西方的國際電影節形成了良性的競爭關系。國際電影節與海外電影周、海外電影發行放映等共同發揮作用,構成了新中國電影海外傳播的主渠道。
在通過國際電影節對國家形象進行海外傳播的效果上看,新中國獲獎電影與后來第五代導演海外獲獎的民俗電影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以張藝謀作品為代表的第五代民俗電影(如《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五魁》等)雖然也在國際電影節上斬獲不少獎項,但卻陷入為獲獎而故意迎合西方評委口味的“后殖民主義”怪圈,這些影片所著力塑造和傳播的古老、愚昧、落后、封建的舊中國形象——“宅院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丑化國家形象、歪曲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相反,新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所傳播和塑造的“中國形象”,既是積極、正面、革命的“紅色中國”(《中華女兒》《鋼鐵戰士》《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等影片),同時也是多元化、充滿了民族風情的“魅力中國”(《梁山伯與祝英臺》《大鬧天宮》《桂林山水》等影片)。這種將紅色革命文化與民族特色文化相融合的電影傳播策略,為當前“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國家文化戰略提供了可利用的寶貴經驗。
參考文獻:
[1](捷)A.M.布洛烏希.卡羅維·發利——全世界電影的一面鏡子[J].電影藝術,1958(7).
[2]曉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第八屆國際電影節[J].世界電影,1954(9).
作者簡介:
王文斌,武漢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影視藝術。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政治景觀與民族寓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電影的文化研究(1945-1989)》(16YJC760054)之階段性成果;武漢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東歐電影研究》(2016YB020)之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