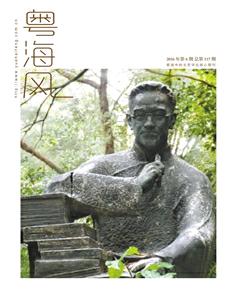區(qū)域性作家的困境與騰挪
袁敦衛(wèi)
題記:愿為磨刀石,使刀鋒利。
——賀拉斯
2013年5月至2016年3月,本人在大量閱讀東莞作家年度作品的基礎(chǔ)上,撰寫了《東莞文學(xué)備忘錄:2013-2015》年度評(píng)述文章,共約六萬字。按照事先約定,凡是在東莞居住的作家當(dāng)年正式出版或在省級(jí)以上文學(xué)刊物公開發(fā)表的文學(xué)作品,只需作者提供文本(紙質(zhì)版、電子版不限),即可納入評(píng)述范圍。三年來,本人利用閑暇時(shí)間細(xì)讀小說、散文、詩歌、劇本、非虛構(gòu)、評(píng)論作品共計(jì)370多篇(部/首),總字?jǐn)?shù)超過430萬字。如今這項(xiàng)在很多人看來“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覺得有必要對(duì)三年來的閱讀感受做一個(gè)大致的梳理,一方面可作為文藝工作者認(rèn)識(shí)當(dāng)前創(chuàng)作狀況的階段性地方報(bào)告,另一方面能為區(qū)域性作家窺見自身創(chuàng)作面目提供參考。
一、區(qū)域性作家及東莞文學(xué)近三年的基本面貌
“區(qū)域性作家”既不是一個(gè)現(xiàn)成的概念,也不是可靠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而僅僅是用以界定某類創(chuàng)作主體的描述性詞組,其語法結(jié)構(gòu)類似于“處于成長期的作家”。這個(gè)詞組指涉的對(duì)象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他們是某個(gè)具體時(shí)代作家群體中的“大多數(shù)”;第二,他們的寫作通常是業(yè)余性質(zhì)的,即無法通過單純的創(chuàng)作維持體面的經(jīng)濟(jì)生活;第三,作為作家,他們的聲望和影響力通常局限于一個(gè)區(qū)域,大至一省或數(shù)省,小至一縣一市;第四,如果不是發(fā)生某種奇跡——譬如有人的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令人驚異的爆發(fā)或是被某個(gè)左右文壇的大師極力舉薦,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終生都將保持這種不紅不紫、不寵不辱的狀態(tài);第五,有一種可能:在一個(gè)時(shí)代只是“區(qū)域性”的作家在另一個(gè)時(shí)代變成全國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從“二人轉(zhuǎn)”變成“芭蕾舞”,釀成這種轉(zhuǎn)變的因素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像沈從文、金庸、張愛玲等,都多少帶點(diǎn)這種意味;第六,一些作家之所以是“區(qū)域性”的,與他們不跟文學(xué)“死磕”有關(guān)系(但不是絕對(duì)的關(guān)系),一是因?yàn)槲膶W(xué)不“經(jīng)濟(jì)”,二是因?yàn)槲膶W(xué)多少需要“狂熱”。在這一點(diǎn)上,莫言是一個(gè)典范,為了一天吃上三頓餃子、娶石匠家“睡眼朦朧”的女兒做老婆,一門心思往文學(xué)的窄門里鉆,所以莫言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了解莫言或者有點(diǎn)眼紅的人把他的獲獎(jiǎng)當(dāng)作“一炮打響”,這是缺乏根據(jù)的。波德萊爾早在1846年就說過:一個(gè)出色的作家“打響的頭一炮是許多他們(指其他作家和不知情的讀者——引者注)不知道的頭一炮的結(jié)果。”[1]第七,“區(qū)域性作家”只是對(duì)作家創(chuàng)作地位和藝術(shù)影響力的一種大致描述,它與當(dāng)前流行的、帶有方志色彩的“地方寫作”沒有必然的關(guān)系。
根據(jù)以上描述,東莞近十年來聚集了一大批有相當(dāng)創(chuàng)作實(shí)力而影響力相對(duì)有限的作家,而正是從這一大批區(qū)域性作家中,陸續(xù)走出了王十月、鄭小瓊、塞壬、柳冬嫵、丁燕等具有全國性聲譽(yù)的寫作者,他們分別在小說、詩歌、散文、評(píng)論和非虛構(gòu)長卷上涂抹了自己的話語色彩,彰顯了獨(dú)特風(fēng)格。從文學(xué)生態(tài)來說,任何一個(gè)大作家腳下都有無數(shù)個(gè)區(qū)域性作家泥土般的存在。根據(jù)本人初步統(tǒng)計(jì),近三年(2013-2015)東莞作家正式出版、在省級(jí)以上文學(xué)刊物公開發(fā)表的文學(xué)作品共計(jì)約510篇(部/首),其中在全國文壇產(chǎn)生一定反響的作品約10部。這或許印證了法國評(píng)論家蒂博代所言:“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無聞的成千上萬個(gè)作家來維持文學(xué)的生命的話,便根本不會(huì)有文學(xué)了,換句話說,便根本不會(huì)有大作家了。[2]
大批作家聚集東莞這座以工業(yè)聞名的二線城市,既是東莞“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反映,也是東莞積極營造文學(xué)氛圍的結(jié)果。王蒙、賈平凹、莫言、余華、蘇童、韓少功、蔣子龍、余光中、洛夫等著名作家詩人的到訪,好似給這座堅(jiān)硬的工業(yè)化城市帶來了柔和的清風(fēng);雷達(dá)、李敬澤、謝有順、楊克等名家的指導(dǎo)則使東莞文學(xué)始終埋頭于“走正道、干實(shí)事”,十年來風(fēng)雨不改,成為中國最活躍的文學(xué)熱土之一。
但是,東莞作家近三年來的創(chuàng)作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常見的短板和困境。對(duì)于大多數(shù)目前還處于突圍狀態(tài)的區(qū)域性作家來說,或許有其借鑒意義;東莞作家突圍的方向或許也是他們尋求突破的方向。根據(jù)本人對(duì)文學(xué)的基本理解和三年來撰述備忘錄的感受,東莞作家的常見短板和寫作困境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六種情形,現(xiàn)分述如下。
二、區(qū)域性作家的常見短板與困境
(一)對(duì)語言缺乏敬畏
作家首先是語言的工匠,是唯一以打磨文字為立身之本的“手藝人”。令人詫異的是今天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幾乎自行廢除了對(duì)語言本身進(jìn)行審視的功能,除了謝有順、李建軍等少數(shù)批評(píng)家還會(huì)對(duì)作家的文字較真外,大部分批評(píng)家已經(jīng)閉口不談文字了(部分原因是他們當(dāng)中某些人的文字也非常不堪),一些批評(píng)家甚至認(rèn)為語言文字僅僅是“末節(jié)”,批評(píng)家沒有必要像語文教師那樣去挑剔作家的語言毛病。其實(shí)這是嚴(yán)重的短視:如果作家連語言文字都不審慎,我們還能希望他們對(duì)什么審慎呢?我也不認(rèn)為廚師對(duì)食材的選擇、切配、烹制敷衍隨意,還能呈獻(xiàn)出人間至味。
區(qū)域性作家對(duì)語言這一符號(hào)載體缺乏敬畏有三種情形。第一種:錯(cuò)字、別字、漏字、衍字頻繁出現(xiàn),有時(shí)一兩萬字的作品,文字錯(cuò)漏竟然多達(dá)二三十處,讓人幾欲廢讀。當(dāng)代作家基本上都借助電腦寫作,電腦輸入的自動(dòng)性和隨機(jī)性極易造成文字錯(cuò)漏,但這不應(yīng)成為作家敷衍讀者的理由。對(duì)文字缺乏基本的敬畏,丟三落四,只會(huì)貶損作家自身的尊嚴(yán)。一個(gè)連自己的文字都不愿意精讀細(xì)看、認(rèn)真校正的作家,不值得尊敬,因?yàn)樗鹣染鸵源譃E的文字冒犯了他的讀者。對(duì)于有人主張廢除語態(tài)助詞“的地得”的差別,我認(rèn)為這是典型的語言懶漢思想。作家本應(yīng)是對(duì)語言的細(xì)微差別最為敏感的人,如果自甘麻木,粗制濫造,“差不多就行”,語言在作家手上還有什么生命力可言?
第二種:詞義不清、語言冗雜、口水泛濫。在區(qū)域性作家的作品中,因?yàn)閷?duì)詞義不了解而造成誤用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如將“空穴來風(fēng)”理解為“毫無根據(jù)”(其實(shí)恰恰相反),將“無時(shí)無刻”理解為“時(shí)時(shí)刻刻”,將“萬人空巷”理解為“街上空無一人”,將“見某人最后一面”理解為“最后看某人一次”,將“一發(fā)而不可收”誤用為“一發(fā)不可收拾”等。當(dāng)前的文學(xué)作品詞語泛濫,句子洶涌,篇幅越拉越長而韻味越來越淡,與作家對(duì)語言本身缺乏“工匠精神”息息相關(guān)。此外,語言冗雜,口水泛濫同樣是區(qū)域性作家筆下常見的病態(tài)現(xiàn)象,它們的共同癥狀是:句群內(nèi)部差異小,有效信息貧乏,無謂地制造重復(fù)。
第三種:語言過于“熟濫”,既無個(gè)性又無光彩,既無棱角又無彈性。生活世界是無限豐富且變化無窮的,綿密的語言之網(wǎng)尚且抓不住經(jīng)驗(yàn)的游魚,更何況那些粗疏空洞的編織物?有些作家一描寫男人看到美女,就是“眼睛都直了”,一描寫害羞就是“臉紅到耳根”,一形容人多擁擠就是“像沙丁魚罐頭”……似乎所有男人看到美女或者害羞都是一樣的表情和神態(tài)。如果作家的語言倉庫動(dòng)輒被這類缺乏個(gè)體直接經(jīng)驗(yàn)支撐的句子“劫持”,未嘗不是一種危險(xiǎn)。對(duì)此憂心忡忡的卡爾維諾直接稱之為“語言瘟疫”,張大春則目為“語言的尸體”。其實(shí)并不是某些語言注定會(huì)成為“尸體”,它取決于作家所創(chuàng)設(shè)的語境,一些看似“熟濫”的語言在特殊語境下,反倒可能成為光芒四射的神來之筆。
(二)對(duì)敘事方法沒有熱情
這一點(diǎn)主要是針對(duì)小說而言。區(qū)域性作家對(duì)敘事方法的冷漠主要源于他們對(duì)敘事方法帶來的作品變形缺乏體認(rèn),因而主動(dòng)求新求變的動(dòng)力不足,大多數(shù)作家僅滿足于講好一個(gè)首尾相續(xù)的故事,而在“如何講”上面著力不多,以致大部分小說作品給人以手法上的陳舊之感,譬如以物喻人,以環(huán)境烘托人物心理等等,極易落入俗套。
小說本是一種強(qiáng)調(diào)虛構(gòu)的文體,在虛構(gòu)中“重構(gòu)”現(xiàn)實(shí),意味著小說只要能“重構(gòu)”一種非歷史性的“心理的現(xiàn)實(shí)”,就不必拘泥于刻板僵硬的時(shí)空方法。無論時(shí)空如何變形扭曲,只要“現(xiàn)實(shí)”在心理上是可理解、可讀取的,都不會(huì)傷害甚至反過來豐富作品的自足性。比如以陳崇正的作品《碧河往事》為例:碧河鎮(zhèn)半步村的草臺(tái)戲班班主周初來去看望早年曾唱過戲的母親,順便邀請(qǐng)她來觀看戲班里新來的女演員韓芳演出。韓芳的半場(chǎng)《金花女》,勾起了母親一連串的歷史回憶:文革期間,她曾迫害過一個(gè)叫陳小沫的戲曲演員,逼她“把釘子敲到她師傅的腦袋上,說是讓她戴罪立功”。母親懷疑韓芳是陳小沫的后人,前來追討留在自己手里的玉手鐲。母親在后臺(tái)的一曲《金花女》,引得眾人“嘖嘖稱奇”。母親死后,給自己墓碑上的文字留下兩張紙條,上面分別寫著:“陳小沫之墓”和“陳丹柳之墓”。周初來知道,母親其實(shí)就叫陳小沫。
初讀此文,似乎頗為費(fèi)解:母親何以既迫害“陳小沫”,而自己又是陳小沫?靜心細(xì)想,原來這不過是陳崇正打破常規(guī)敘事套路的障眼法:母親陳小沫在文革中飽受摧殘,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嚴(yán)重的人格分裂:一邊是施暴者(陳丹柳即是逼迫陳小沫往師傅頭上敲釘子的人),一邊是受害者(陳小沫),她在這兩者之間不停轉(zhuǎn)換角色,因而形成了情節(jié)上的悖謬。陳小沫的人格分裂既指證了文革對(duì)藝術(shù)家的人性摧損,又為當(dāng)前的世事剖析提供了一個(gè)獨(dú)特的視角:“人在命運(yùn)最悲愴處,也應(yīng)該有柔情……惟有如此,所有遭難才有意義。”小說精巧構(gòu)思,筆墨節(jié)制,看似波瀾不驚,卻又暗流洶涌,可說是潑向當(dāng)前小說敘事扁平化現(xiàn)象的一瓢冷水。
對(duì)于敘事方法格外在意的張大春曾表示:我不只是一個(gè)說故事的人,還是一個(gè)于無事處反省“說”這件事的人[3]。對(duì)區(qū)域性作家來說,反省“如何說”,有時(shí)比故事本身更為切要。
(三)對(duì)現(xiàn)實(shí)過于粘滯
我從來不反對(duì)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小說和散文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著力刻畫——越是窮形盡相越是生色。但在許多區(qū)域性作家那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刻畫”變成了對(duì)世界表象的死纏爛打,夾裹不清。一些作家沉溺于描寫生活的各種場(chǎng)景、細(xì)節(jié)和人物心理,但角度和筆法始終沒有變化,讀者就像被按在現(xiàn)實(shí)的泥淖里,絲毫沒有喘氣的機(jī)會(huì)。原因是作家自己也不自覺地陷在這攤泥淖里,“進(jìn)得去卻出不來”,我稱之為“粘滯”。
其實(shí)就作品本身而言,“粘滯”并非缺陷,而只是暴露了作家的格局和境界:他們只停留在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世界里,永遠(yuǎn)只寫他們經(jīng)歷過的事,吃過的飯,喝過的水,見過的人,遭過的罪……當(dāng)然他們也有想象,但那想象只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重組和再現(xiàn),目的還是向現(xiàn)實(shí)逼近,他們對(duì)眼前的現(xiàn)實(shí)有一種未經(jīng)反思過的強(qiáng)烈依賴,他們慣于對(duì)未知之事閉口不言。正因如此,卡爾維諾才“感到整個(gè)世界都快變成石頭了”,于是他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兩個(gè)層面對(duì)這“石化”般的現(xiàn)實(shí)發(fā)起了反擊。他在《新千年文學(xué)備忘錄》中說:
未知永遠(yuǎn)比已知更有魅力;希望和想象是對(duì)人生經(jīng)驗(yàn)的失望和哀傷的僅有的安慰。[4]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何余華讓賣血的許三觀用嘴巴給一家老小炒菜:“我用嘴給你們每人炒,你們就用耳朵聽著吃了,你們別用嘴,用嘴連個(gè)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豎起來,我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們自己點(diǎn)。一個(gè)一個(gè)來,先從三樂開始。三樂,你想吃什么?”在匱乏中端出豐富,在哀傷中溢出喜樂,或許比單純控訴現(xiàn)實(shí)、描述被苦難碾壓的傷痛要有意味得多。當(dāng)然,這種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粘滯”與其它作品描寫苦難給人類造成的“重壓”不同,前者是被無多少價(jià)值的生活表象纏繞而令人厭倦,后者則引起受眾強(qiáng)烈的內(nèi)心震顫;前者以水平式的拖沓重復(fù)讓人急于脫身,后者則被現(xiàn)實(shí)的力量搖撼而出現(xiàn)短暫的閱讀中斷。
我們不妨看看張大春的《自莽林躍出》是如何處理“現(xiàn)實(shí)”的:在亞馬遜叢林深處,我們碰到了三個(gè)“渾身皺皮、乳長及腰、滿手滿腿長著褐色長毛的所謂女人”。向?qū)Эㄍ哌_(dá)帶著癩子狗連跌帶撞跑到了密林里,把“我”扔給三個(gè)女人。“我”又驚又怕,對(duì)著女人們胡亂開槍,又給她們?nèi)邮澄铩H齻€(gè)女人似乎并無惡意,她們?cè)凇拔摇睂?duì)面盤腿坐下,一邊漫不經(jīng)心地享用干熏河豚、矮象腿和炒堅(jiān)果,一邊微笑著閑談。后來——
她們甩了甩及膝的雜亂長發(fā),跳起身,對(duì)我又嘰里咕嚕一番……其中一個(gè)還回頭說了十二個(gè)字,聽著使我頭皮一緊——我清清楚楚地聽見她用河南土腔說:“就此別過后會(huì)有期吾等告辭。”
這十二個(gè)字不僅把“我”的迷彩帽“震飛掉”,也差點(diǎn)把讀者手上的小說震飛掉。有些讀者或許還會(huì)跳起來:“張大春,你這不是瞎胡鬧嗎?”可愛的考古學(xué)或人類學(xué)家可能還要認(rèn)真考證一下,歷史上是否有過河南人向亞馬遜河流域遷徙的歷史;文學(xué)史家則忙著向大春求證:您是哪一年去的亞馬遜,怎么沒聽您說過?當(dāng)我們這樣鬧騰的時(shí)候,張大春正掩口大笑,幾乎撲倒在書桌底下。難怪張大春說,小說好比“稗子”,“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5]其實(shí),理想的讀者根本不關(guān)心張大春是否去過亞馬遜,他們知道,如果大春在亞馬遜叢林碰到的都是猴子、樹懶、鱷魚、森蚺這些活物,那就算不得什么,只有寫出那不可知、不可測(cè)、不可解的存在,才算是“對(duì)狂野的大自然心存敬畏”,“才沒有冒犯或辜負(fù)這一片隨時(shí)可能蹦出個(gè)大魔王來掐死我的莽林。”
(四)對(duì)現(xiàn)有格局無力突破
區(qū)域性作家一般都有較長時(shí)間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史,而且往往形成了對(duì)某類題材和體裁的創(chuàng)作慣性和偏好,格局初顯,成為地方文壇辨識(shí)他們的基本依據(jù)。從我的閱讀經(jīng)驗(yàn)來看,有些作家連續(xù)幾年的作品面貌和創(chuàng)作手法都大同小異,以致審美效應(yīng)逐年遞減。比如反復(fù)描寫自己在城市的漂泊狀態(tài)、描寫對(duì)故土家園的依戀、對(duì)鄉(xiāng)村衰敗的感傷、描寫童年記憶和青春萌動(dòng)等。其實(shí)所有的區(qū)域性作家都有尋求突破的內(nèi)心期待,只是受制于各種因素,對(duì)當(dāng)前的創(chuàng)作格局既愛且恨。“愛”是由于這種格局一直是他們寫作成績的證明,“恨”是由于這種不紅不紫的“成績”似乎暗示了他們的格局和地位。
區(qū)域性作家無力突破現(xiàn)有格局的原因并不復(fù)雜,常見的無非是勤奮程度、個(gè)人稟賦、學(xué)習(xí)方法等等。但我個(gè)人認(rèn)為,對(duì)寫作沒有“野心”是當(dāng)前區(qū)域性作家難以突破現(xiàn)有格局的最大障礙。所謂“野心”不是指天馬行空、好高騖遠(yuǎn),而是指作家要盡力避免在同一水平不斷重復(fù)自己,帶著成長之痛做一個(gè)更“野”、更陌生、更難歸類和辨認(rèn)的寫作者。我相信一部作品沖擊“高峰體驗(yàn)”,遠(yuǎn)遠(yuǎn)勝過十部作品重復(fù)“高原反應(yīng)”。持續(xù)通過寫作修煉作家的心性,超越老舊的自我,這是一個(gè)高于創(chuàng)作的、更根本也更實(shí)在的問題。在這一點(diǎn)上,我認(rèn)為塞壬是一個(gè)榜樣:她的散文見刊不多,但每一篇都盡可能向不同方向掘進(jìn),并細(xì)心打磨,力求潤澤光亮,《悲迓》《祖母即將死去》《虛度,在光陰的另一面》等都是顯例。
(五)對(duì)流行價(jià)值缺少反思
作家與普通人的最大差別在于,他們以文字為觸須,探測(cè)來自世界的不安定氣息。但如果作家覺得世間的一切都合情合理,井然有序,一切都可以對(duì)號(hào)入座,恐怕他們的作品也很難對(duì)讀者有所開啟,他們的寫作充其量只是為這世界增加一點(diǎn)文字的裝飾。在我看來,作家至少應(yīng)該在某些時(shí)刻,是孤獨(dú)的人。他們孤獨(dú)是因?yàn)楦杏X到與這個(gè)世界有點(diǎn)不合拍,感覺到這個(gè)世界似乎哪里不對(duì)勁,他需要說出來、喊出來,雖然他們未必能找出問題的癥結(jié),并提供具體的方案。
在我的閱讀印象中,我總覺得區(qū)域性作家們離這個(gè)世界太近,不是時(shí)空距離、生存方式上的近,而是價(jià)值觀念上的高度雷同——他們太像是這個(gè)世界的私生子。他們幾乎毫無察覺地同情、順應(yīng)、固化乃至坐實(shí)某種流行但又可疑的價(jià)值觀念,乃至成為流行觀念的推手。譬如描寫成功男性,幾乎沒有不寫他們的情人的(有時(shí)好幾個(gè));描寫人生苦難,幾乎沒有不寫物質(zhì)匱乏的(而且最好是從小寫起);描寫人生得意,幾乎沒有不寫別墅豪車的(最好是配合著美女來寫);描寫人性復(fù)雜,幾乎沒有不寫酒色權(quán)謀的……其實(shí)作家并沒有先天的題材禁忌,惟一的困難在于他怎樣為我們延展——哪怕是一點(diǎn)點(diǎn)——不那么陳腐的認(rèn)知和感覺疆界,否則不過是在既有的認(rèn)知和感覺范圍里換個(gè)方式打轉(zhuǎn)而已。博爾赫斯曾說,一個(gè)民族精神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是與這個(gè)民族大多數(shù)人的精神狀況背道而馳的,因此我們才能理解作為“民族魂”的魯迅為何總是那樣孤獨(dú)[6]。在區(qū)域性作家那里,我?guī)缀蹩偸呛敛毁M(fèi)力地看到作家的內(nèi)心世界與“大多數(shù)人的精神狀況”是如此接近,乃至彼此狎戲——他們太像是這個(gè)世界的私生子,他們對(duì)這個(gè)世界幾乎沒有任何價(jià)值層面的困惑和疑問。
(六)對(duì)寫作本體論認(rèn)識(shí)模糊
寫作本體論追問的是,寫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說作家寫作的自覺性建立在什么基礎(chǔ)上?對(duì)大多數(shù)區(qū)域性作家來說,他們寫著寫著就成了“作家”或成了“詩人”,有的甚至還獲得了不小的聲譽(yù)。但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并沒有建立起相對(duì)清晰的寫作自覺。在一些區(qū)域性作家那里,小說則直接變?yōu)楸姸鄬?shí)用工具中的一種:記錄底層生活、抨擊專制暴政、揭露黑暗內(nèi)幕、歌頌愛國主義、反戰(zhàn)反腐、禁煙禁毒等等,幾乎衍變?yōu)榱硪环N形式的“概念寫作”。
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理論認(rèn)為文學(xué)有認(rèn)知、教育、娛樂等功能,但寫作本身究竟意味著什么?傳統(tǒng)理論從未正面作答。梁?jiǎn)⒊J(rèn)為小說的目的在于“新國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fēng)俗、新學(xué)藝、新人心、新人格”,幾乎將小說之外的事物都點(diǎn)到了,唯獨(dú)沒有論及小說自身,正因如此,張大春才認(rèn)為“小說從來不曾擁有過自己的目的”,因?yàn)樗浑x開孩子們聽故事的庭院就失去了身份——僅僅作為故事本身帶領(lǐng)孩子們穿越時(shí)間的綿延,也就“斷送了成就一門藝術(shù)、成就一種美學(xué)的可能。”[7]雖然張大春把小說的本體論濃縮為一句“一個(gè)詞在時(shí)間中的奇遇”,但我更愿意用余秀華的詩歌來考量和檢驗(yàn)作家對(duì)于文學(xué)本體論的自覺程度。在2014年的備忘錄中我曾寫過:
“閱讀余秀華詩歌的唯一困難,在于忘記她是一個(gè)農(nóng)婦和腦癱患者。”
三、區(qū)域性作家的騰挪之法
“騰挪”本是棋類用語,在象棋中是指挪開本方處于不利位置的棋子以便更好地發(fā)揮其他棋子的作用,在圍棋中是指在敵強(qiáng)我弱的情況下“輕巧又有彈性”地處理本方孤子以“求活”。對(duì)寫作而言,“騰挪”意味著“騰空”、意味著“挪移”,意味著對(duì)困境和僵局的“轉(zhuǎn)身”和佛家意義上的“不舍不得”。
(一)思想的騰挪
我傾向于把“思想的騰挪”理解為作家對(duì)寫作本體的再發(fā)現(xiàn):也就是讓寫作成為它自己所要成為的事物,而不是任何對(duì)寫作的簡(jiǎn)化和抽象。在我的閱讀經(jīng)驗(yàn)中,東莞作家最易陷入的思想囚籠就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代入離鄉(xiāng)背井、飽受漂泊之苦的底層社會(huì)角色中,繼而以職場(chǎng)失意、身體疾患、城鄉(xiāng)對(duì)決、人生無定等作為思想的母本,最后以“文學(xué)”這一工具展開具有強(qiáng)烈現(xiàn)場(chǎng)感和身體感的文字演繹。在我看來,這既是區(qū)域性作家的優(yōu)勢(shì),也是劣勢(shì)。優(yōu)勢(shì)在于它能迅速為作家在特定的、帶有區(qū)域文化色彩的文學(xué)社群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和編碼;劣勢(shì)在于它傾向于將作品導(dǎo)向一個(gè)工具性的存在,一項(xiàng)遠(yuǎn)遠(yuǎn)比作品本身狹隘的實(shí)用功能,就好像——
小說通過一場(chǎng)以利益和情色為核心的酒場(chǎng)博弈,深入刻畫了以林昭為代表的中小企業(yè)主們的生存環(huán)境和內(nèi)心狀態(tài),也可說從人性陰暗的角度揭示了中國錯(cuò)綜復(fù)雜的酒桌文化。
其實(shí)這是我為袁有江的中篇小說《紅樓夜宴》所寫的概述。這樣的概述無疑是對(duì)小說的簡(jiǎn)化,因?yàn)樗闹埸c(diǎn)在“中小企業(yè)主們”,在“酒桌文化”,它甚至無法解釋經(jīng)歷巨大波瀾的林昭回到東莞后,面對(duì)妻子的那份從容和“日常”。我有時(shí)猜想它或許是在現(xiàn)實(shí)和文字兩個(gè)層面同時(shí)展開了一項(xiàng)漫不經(jīng)心的“騰挪”:從高檔酒樓上的觥籌交錯(cuò)、暗流洶涌到與妻子共進(jìn)一頓日常的“晚飯”。騰挪的結(jié)果是:日子總得過,波瀾終歸平靜。文字在自我釋放緊繃的張力時(shí),其實(shí)也暗暗釋放了林昭。如果是這樣,我或許應(yīng)該重新評(píng)價(jià)《紅樓夜宴》,只是該文本提供的證據(jù)不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