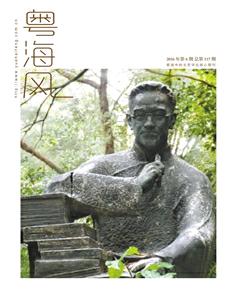厭女與憂郁:重讀《傷逝》
周云龍
一、前提與方法:作者已“死”
在起源神話已遭遇破解的年代,仍執迷于某種假設的“本意”而前索后引,勢必把閱讀實踐導入一個令人苦惱不已的混亂境地。如此,至少要面臨三重困難。第一,任何作品只要以人類的語言為工具和介質,都將無法避免“延異”的運作,因為“延異”是語言和意義的條件;那么,語言就不是透明的,它從來都無法精準傳達任何人的任何“本意”,而總是某種“本意”的溢逸延宕或指涉中斷。第二,縱使存在著作者的某種“本意”,并且可以借助語言得以精準傳達(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讀者的閱讀實踐亦無法直達這一“本意”,其原因在于:除了讀者同樣面對著語言和意義的“延異”外,還必須考慮讀者“前理解”的巨大干擾。其實這前兩個困難中的任何一個作為前提,就足以徹底終止對作者“本意”的執迷與追溯。這里不妨再仁慈一點,假設還可能存在著“第三”重困難。試著做一反向思考:如果《傷逝》是以小說的形式(浪漫主義意義上的)“表現”了魯迅與周作人或許廣平間的愛恨情仇糾葛,或者是魯迅的其他什么“本意”,那么,《傷逝》早就已經“完成”,并向所有人關閉了闡釋的大門。再提出“《傷逝》的讀者”或“閱讀《傷逝》”就是自欺欺人,然而常見的《傷逝》解析總是樂此不疲。“讀者”這個名詞此刻已經是荒誕無稽、沒有必要的(不)存在。因此,《傷逝》的作者是魯迅,但并不意味著《傷逝》的意義屬于魯迅,除非《傷逝》一直處于魯迅的“腹語”狀態。
既然閱讀《傷逝》,前提就是讀者已經是一種必然的存在。或者說,《傷逝》從未完成,它的意義永遠向他人敞開,有待讀者參與、介入。作為文本,《傷逝》的作者已“死”,《傷逝》屬于讀者。因此,《傷逝》里面沒有可供讀者參透的“真理”,相反,《傷逝》是某種“表述”。“真理”僅屬于作者,它是封閉的、排他的、反闡釋、反讀者的。《傷逝》的文本嵌絆在具體的語言、文化、政治等提供的歷史氛圍中,唯獨不與“真理”相關。
在“表述”的知識立場上閱讀《傷逝》,就意味著“互文”將是重要的方法。“互文”方法中,既包括文學文本間的互文,也包括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間的互文。而后者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為前者的闡釋效力往往體現在印證的層次,而后者則可以提升到論證的層次。
二、“子君”的性征與性別
“表述”牽連著語言問題。文本《傷逝》作為“涓生的手記”,是敘事者“我”的策略——盡可能混淆敘事者與人物涓生,以增加懺悔的真誠度。但敘事者可能始料未及的是,在“表述”的方法視野中,這一帶有欺瞞性的敘事策略亦可以轉化為讀者對文本的解析策略——像審視涓生那樣審視敘事者。
《傷逝》中有兩個重要人物,戀人涓生與子君,但二者并不在同一個語言維度和權力層級上。“涓生的手記”告訴我們,敘事者把言說的權力給予了涓生。文本中的“子君”是在場的缺席,是敘事者的一種表述。文本呈現的“子君”,并不是現實的子君,子君的真實經驗在敘事中已被抹除,讀者無從知悉。讀者看到的“子君”已經經過敘事者“我”或者涓生的代言和過濾。無論文本中的“子君”多么可悲、多么可敬、多么勇敢、多么悲慘、多么瑣碎……都是敘事的詭計。當讀者談論“子君”時,究竟在談論什么?對該問題的認識,決定著閱讀的自覺程度。“子君”是被表述者,“她”/它在文本中處于被觀察、被建構、被噤聲的位置。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子君”是敘事者的心理“投射”。“子君”是被欲望著的幻象,甚或是涓生/敘事者本人。因此,從性征上講,“子君”是女性,而從性別上講,“子君”是男性,或者說至少是中性。
那么,在“子君”那里,究竟被“投射”了什么?
三、自然主義;或物質的性別指涉
有學者(比如鄭家建先生)認為《傷逝》是最不像“魯迅小說”的魯迅小說,因為其中充滿了瑣碎而冗贅的筆觸,與魯迅既往的簡潔似乎格格不入。這一精準的觀察,從另一角度來講,可能正好意味著其“魯迅性”。
《傷逝》的瑣碎和冗贅,主要指涉文本中大量看似可有可無的日常描寫。魯迅的此類筆法可能也出現過——常常見于其對故鄉風物栩栩如生而搖曳生姿的刻畫,因為其生動和詩意,在審美效果上不會令讀者感到無聊和厭煩。魯迅的醫學背景和美術功力更為此類筆觸提供了基本保障。這種筆觸從藝術手法上講,屬于自然主義式的寫作。借用左拉的話說,創作者就像“一個查考事實的觀察者”。自然主義的手法在契訶夫和梅特林克那里,體現為日常生活的詩化和抒情,其創作也成為現代主義的典范。但《傷逝》僅有日常的外觀,而祛除了其中的詩意,被構建為日常的“非常”與“變態”。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在《傷逝》的文本脈絡中,這句話已經悄然判決了“子君”的必死命運。涓生(因為和子君的自由戀愛)失業后,找到“一條新的路”——通過做翻譯謀生。但這條新路并不像涓生當初籌劃的那般輕松。遭遇挫敗后,涓生認為: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么幽靜,善于體貼了,屋子里總是散亂著碗碟,彌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更容易成為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為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傷逝》)
這是一場男性啟蒙者與日常生活之間激烈的競爭,以及男性啟蒙者的最終挫敗與絕望感,而“子君”/女性則成為競爭雙方爭奪的對象。
這兩段文字,甚至是整個文本的后半部分,充滿了上述(被建構的)二項對立:“我”/涓生/男性/啟蒙者/書案/翻譯/“先前所知道的”——“子君”/“子君”/女性/被啟蒙者/油鹽醬醋、瓶瓶罐罐/“吃飯”/“全都忘掉”。一句話,物質與精神、肉體與理性之間的緊張對立。當“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時,敘事者的態度已然明朗。“子君”在生理層面的生命尚未終結,在符號層面的死亡大門已經開啟——“她”/它在敘事者的“轉向”中被“推開”了。
依據德里達的梳理,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中,從“前蘇格拉底”一直到海德格爾都認為真理源自邏各斯。物質則是邏各斯的衍生和影子——這在柏拉圖的“理念說”和古希臘文藝創作中,都有清晰的體現。比如,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就被克瑞翁視為“非理性”的化身而被排拒在城邦政治之外。這一古老而頑固的認識論,借助卡瓦里羅的說法,就是僅把肉身作為思想的物質性工具,因此,肉身要與思想區分。而女性則被貶低到“非理性”、“肉身”、“物質性”的領地,這正是男權主義思想的基礎。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西方主義”情結,決定了他們無從對上述古老的認識論免疫或反思。指出上述顯而易見的思想與物質間的二元對立及其性別意涵并不困難,在庸俗化的“女權主義”氛圍中,這早已是習見不鮮的陳詞濫調,關鍵在于在此做出闡釋。“子君”身上被“投射”的物質性的“形而下”意義,暗示了敘事者強烈的厭女傾向與自我憎恨。
“子君”是一個尺度和鏡像,是衡量啟蒙效果的尺度和映現啟蒙者自我的鏡像。因為“日常生活”橫刀奪愛,涓生輸了,(期望中的)“子君”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日常生活”懷抱,與之融為一體,結成聯盟。“魯迅”在1928年8月回想起“五四”時期譯介易卜生的原因及《新青年》“易卜生號”刊出之后的情形時寫道:
……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說,因為要建設西洋式的新劇,要高揚戲劇到真的文學底地位,要以白話來興散文劇,還有,因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實例來刺戟天下讀書人的直感:這自然都確當的。但我想,也還因為Ibsen敢于攻擊社會,敢于獨戰多數,當時的紹介者,恐怕是頗有以孤軍而被包圍于舊壘之感的罷,現在細看墓碣,還可以覺到悲涼,然而意氣是壯盛的。
那時的此后雖然頗有些紙面上的紛爭,但不久也就沉寂,戲劇還是那樣舊,舊壘還是那樣堅;當時的《時事新報》所斥為‘新偶像者,終于也并沒有打動一點中國的舊家子的心。……(《<奔流>編校后記(三)》)
這兩段文字坦誠地記錄了啟蒙者的挫敗。與此對照,反而是新文化運動者極力否定的“舊文學”,借助近代中國興起的傳媒報業和文化市場,在此間不經意地真正履行了啟迪民智的重任。在這個意義上,這兩段“坦白”可視為1925年的《傷逝》意義結構的補充性印證和注腳。遭遇挫敗的啟蒙者的動搖與轉向在啟蒙思想退潮期幾乎成為“集體無意識”:最早是“狂人”病愈,后來是呂緯甫、魏連殳……就連《<吶喊>自序》的敘事者也曾在鬼魅魍魎的S會館抄了一段時間古碑。“人必生活著”!啟蒙營壘的瓦解,此時成為知識群體的威脅與誘惑。因此,“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與其說是“子君”的軟弱,不如說是涓生/男性敘事者/啟蒙者自身己所不欲、無法克服的某種誘惑性力量,使他們為之深感恐懼且自我憎恨。為了紓解自我的這一精神危機,他們不得不去發明、建構一個自我的他者——女性/物質性/“子君”,進而對之進行符號壓抑、排除——“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但這一文本實踐邏輯和符號暴力,使男性啟蒙者更為深刻地接近并復制了他們深感恐懼的幾千年來的“吃人”文化傳統。因此,可以說“子君”是涓生的另一個自我,二者一體兩面,二者一起構筑了現代中國啟蒙者分裂的精神世界。
四、“娜拉”是誰?
除了要抵御、紓解啟蒙挫敗和退潮后背叛自我初衷的誘惑與恐懼,現代中國啟蒙者的精神困境還體現于身份認同層面。這一精神困境主要折射在包括《傷逝》在內的現代中國的“娜拉”故事中。
作為人物形象,“娜拉”源自一個眾所周知的文本,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簡單比較一下《玩偶之家》與中國現代有關“娜拉”的故事情節,二者間的差異昭然若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講述的是娜拉對資產階級丈夫的離棄,而中國近現代的“娜拉”則是對封建主義“父親”的離棄,而且,“娜拉”離開父親的家后,最終投入另一屬于“子一輩”的男性知識者的懷抱。換句話說,中國的“娜拉”是“反父不反子”的——這正是“五四”婦女解放不徹底的真正癥結所在。在這一思想背景中重新審視《傷逝》的敘事,可以發現,其意義結構中,“伊孛生”“諾拉”(即易卜生、娜拉)占據著一個不那么顯眼卻頗為重要的位置。
如果復述中國的“娜拉”故 事,娜拉就是這些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她們在(性別意義上的)男性知識者啟蒙下,離開封建家庭,追求個人自由(1930年代后是交際花或革命者)。如果闡釋中國的“娜拉”敘事,娜拉就是這些敘事中的男性人物或敘事者——他們在西方知識的啟蒙下,背離傳統文化,追求現代意識。二者在姿態上完全一致,都是離“家”“出走”。所以,“娜拉”在故事層面是“子君”,但在敘事層面則是敘事者/涓生/男性啟蒙者。
任何反叛,都必須以承認所反叛之物為前提。現代中國啟蒙者的“反傳統”從未脫離“傳統”設定的框架,致使他們窮其一生都糾結在“離開——回來”的拉鋸之中。中國的啟蒙者對民族傳統的反叛是一種“以敵為師”的迂回策略,其背后是更為深刻的現代國族主義認同。這一悖論式的思想狀況決定了“娜拉”在文化上“弒父”時的原罪意識,因此,在無意識層面,他們必須不斷“回家”,向內心的“父親”致歉。這是中國現代啟蒙者精神焦慮的核心內容。
為解決懸擱在“西方”與“傳統”間的文化認同困境,在文本層面構建一個自我的本土他者(常常由女性、兒童或底層承擔)就成了不二選擇。《傷逝》中的敘事者自導自演了一個本土啟蒙者的角色“涓生”,“未脫盡舊思想束縛”的“子君”則被分配了一個被啟蒙的位置。可是,面對西方的易卜生、雪萊時,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己就是離家出走的“女性”“娜拉”,面對(發明出來的)本土女性、兒童、底層時,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搖身一變為西方的代言人——“男性”啟蒙者。在涓生眼里,不止一次地視“子君”為“孩子”——“孩子”不僅對應著心智上的幼稚、空白和有待銘寫,更投射著民族文化的脆弱、不成熟和亟待拯救(“救救孩子!”)。涓生被西方啟蒙,“子君”被涓生啟蒙,但作為“涓生的手記”的《傷逝》是啟蒙敗績的記錄:“子君”被理性的對立面“吃飯”征服了,并“回”到了“父親”的“家”里,郁郁而終。這一敘事正是中國現代啟蒙者對自身分裂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精神困境的(詹姆遜所謂的)“想象的解決”。在理智層面,現代性啟蒙道遠且阻,在情感層面,傳統的“家”的誘惑揮之不去。只有在符號層面“殺死”想“回家”的自己,才能真正上路。或用“涓生”的話說,就是“我”“向著新的生路跨進”,進而重構一種現代意義的“家/國”。所以,包括《傷逝》在內的現代中國的“娜拉”敘事其實是一個中國版的“奧德修斯”神話——男性的奧德修斯要想回家,必須讓女性塞壬死去。不同的是,這類中國版的“奧德修斯”神話有一個“反奧德修斯”的外觀。
“傷逝”的標題令人想起唐朝詩人韋應物的同名詩歌《傷逝》中的“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小說《傷逝》的“手記”文體除了用于表達涓生的“悔恨”,還賦予文本一個悲悼的氛圍。但《傷逝》結尾涓生/“我”的一系列心理動向則意味著“憂郁”的情感面向: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傷逝》)
涓生/“我”失去情愛對象“子君”后,反復告訴自己“要遺忘”,這恰恰說明了涓生/“我”的“忘不了”。 這段引文傳達的掙扎與自虐,暗示了失去“子君”的涓生/“我”的情感“病態”。在弗洛伊德看來,“憂郁”是一種主體喪失情愛對象后的自處情緒典型:主體過度悲傷而無法自控地自我貶抑、悔恨。涓生/“我”在“處死”“子君”后,陷入一種情感與行動上的困頓狀態,所以才生發出祥林嫂般的“我要遺忘”“我要遺忘”“我要……”在弗洛伊德的學說中,“憂郁”是一種病態的常態,因為“正常”的人永遠都處在“喪失”的困擾中。由此,可以說涓生/“我”的“憂郁”癥在文本層面,尤其是《傷逝》的結尾部分正是一種“閾限”狀態——從病態走向常態的過渡和臨界。在隱喻層面,敘事者“我”作為現代中國的知識者,內心遭遇了“離家”、“弒父”、“出走”等一系列“喪失”性的情感創傷,但現代“家/國”的時代使命或“齊家治國”的傳統承續,使其必須壓抑、遺忘所“喪失”之物——它在文本層面正是必須“遺忘”之物——幽靈般的“子君”。
五、希望與階級
在1921年的短篇《故鄉》結尾,有一句“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為中學教材的選入,“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幾乎成為人盡皆“知”且熟視無睹的“名人名言”,似乎也因此而獲得了不證自明的“真理”性。然而,正如大多數被掛在墻上的“名人名言”一樣,這句話因為被抽離了特定的文本脈絡,常常被從字面意義作以庸俗化讀解。事實上,《故鄉》的敘事者在距離此句不遠的地方,就曾反思過所謂的“希望”和自己暗中嘲笑閏土崇拜的“偶像”并沒有區別,甚至還不及閏土的“偶像”那般“切近”。在1925年的散文詩《希望》中,作者還引用裴多菲的書信,兩次寫到“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換句話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要點可能不在“路”/“希望”到底有沒有,而在于“路”/“希望”到底由誰去走,由誰去希望。
“走的人多了……”,這一表述中隱約可聞敘事者召喚“大眾”的聲音。1923年的演講中,魯迅在試圖回答“娜拉走后怎樣”的設問時,把“經濟”作為關鍵詞反復重申。《傷逝》中,在顯在的敘事層面,涓生敗于“經濟”問題,而“雪花膏”、“局長的兒子”、“局長”正是切斷涓生生計的最直接的力量和群體,這一階層也許還應該增補上房東和他家的女工。失業后的涓生認識到:“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里的“愛”不僅是愛情,更是“絕望的希望”。上述內容似乎是“左翼”文學的階級動員主題的雛形和胚芽。但是,無論是《娜拉走后怎樣?》中的“娜拉”,還是《傷逝》中的“子君”,其中內涵的“性/別”議題均被抽空。雖然《傷逝》難得地委婉書寫了涓生與子君之間的性愛過程,但女性的“子君們”始終被安放在“希望”的大纛下,成為在場的缺席。當作為階級議題的“經濟”橫空出世,“性別”議題就被其成功遮蔽和置換。
人獲得經濟權方可“希望”,這完全正確,正確到空洞的地步——等于什么都沒有說。但這又“說”出了一切:只有遮蔽掉“娜拉”/“子君”面對的真實“性別”困境,“階級”才能在1930年代順利登場,現代中國的啟蒙者才能完成對自身精神困境的“想象的解決”,并在社會動員中實現其男性主體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