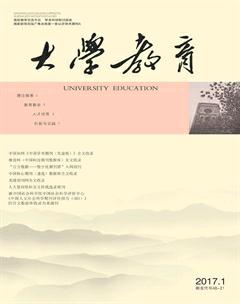愛的成長:現代家庭倫理中的愛
余巖波+王文霞+楊棪
[摘 要]從斐德羅鼓勵人們追求純粹、潔凈的愛情,到舍勒的愛是運動,其思想精髓和基于愛而組建的現代家庭是相通、融貫的,人們均認同愛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由于不同的價值體系相互碰撞,個人的自治和自由同時作用,愛的情感行為也在不同程度地生長著。和諧的家庭關系、恒久的家庭幸福,都需要不斷投入感情、保持愛的進步。基于愛情的情愛是現代婚姻家庭倫理的基礎,層級較高的友愛更具社會意義,而博愛才是愛的歸宿。
[關鍵詞]現代家庭倫理;情愛 ;友愛; 博愛
[中圖分類號] G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1-0049-03
當“原配街頭暴打小三”、“男小三被要求公開道歉”等標題在各大瀏覽器上被推送到6.88億互聯網用戶面前,出軌、婚外情不斷充斥耳膜,家庭暴力納入出警范圍時,我們似乎有必要對現代家庭倫理進行重新審視,對家庭倫理中的愛進行再度的詮釋和思考。
家庭倫理是隨著家庭的建立而產生的一種人倫關系,是調整家庭成員關系的行為規范。現代家庭倫理是在社會現代化背景中產生的家庭人倫關系,烙有現代化的印記,如生產方式變革帶來的物質財富讓家庭有了較好的依存條件,但人們對物質的強烈依賴,在一定程度上減弱或影響了以愛為主要紐帶的家庭情感生活,人際交往的變化和交流手段的增加,影響了人們對家庭生活和家庭價值觀的態度,這些變化和影響又反作用于家庭倫理。愛是維系家庭成員的情感紐帶、家庭生活幸福的主要因素,在現代家庭倫理中地位顯著。
一、愛的理論源起
家庭源于生存需要,具有傳宗接代、繼承家業的基本功能。現代社會強調的情投意合、自由戀愛就是對愛的形式的一種描述,支持因愛組建家庭或將相愛視為家庭成立的前提。事實上,向前追溯,早期的希臘哲學中就包含有愛的因子。
《會飲篇》是柏拉圖最重要且對希臘及后世哲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對話體裁哲學名作,他以阿伽松家的宴會為場景,以宴飲為對話的載體,以宴會賓客的談話為主要內容,闡述了愛的觀點和思想。
按照從左到右輪流的順序,第一個發言者是斐德羅,他認為愛是人類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愛情像一座燈塔,指明人生的航程。“I say, neither kindred, nor honour, nor wealth, nor any other motive is able to implant so well as love.”這句話意為:我認為愛情不是家族、榮譽、財富或其他因素能夠左右或影響的,不受這些因素影響的愛情才是值得擁有和讓人向往的。第二位演說者是鮑薩尼亞,其認為人們應該把愛情賜予高貴的年輕男子,在這種愛的激勵下,人們會更喜歡強壯和聰明的人。第三個是厄律克西馬庫,其認為存在于神圣或世俗的各種活動中的愛的威力適用于一切類型的存在物,提出了愛的普遍性問題。第四個演說者是阿里斯托芬,其認為愛是成就功德的神,引導人們找到與自己真正適合的愛人。第五個演說的是阿伽松,他說愛神是年輕的、嬌嫩的,愛神有正義、節制、勇敢和智慧四種德性,這是柏拉圖指出的古希臘的四大主要德性,后世稱之為四主德,與基督教的七主德相并列。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經典文獻《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用八、九兩卷篇幅論述“友愛”(此“友愛”和一般意義上的愛相通用),主張“友愛”在倫理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家庭中的愛稱為“家室的友愛”,認為“愛者的快樂在于注視被愛者,被愛者的快樂則在于愛者對他的注視”。[1]
歐洲中世紀教父哲學代表奧古斯丁認為愛是人類靈魂的原動力,對愛恰當的排序是所有對生活正確定位的基礎,在日常生活中要按道德的方式對愛進行排序,不恰當的排序是人類生活中一切罪惡的源頭,這一思想奠定了西方一千多年來關于愛的看法的重要基礎。
馬克斯·舍勒是現代德國著名現象學哲學家,《愛的秩序》一書的第一部分有三篇關于愛的論文,分別論述了基督教愛的理念的認識論、本體論和社會學思想,指出“愛是一種內在的價值指涉,一種‘意向性運動,借此運動,我們在某對象已給予的特定價值上‘仰瞻到更高的價值,正是這一仰瞻,一種更高價值的眼光構成了愛的本質。愛就是運動本身,它不是一種目的性行為,不是為了要達到更高價值而去愛”。[2]舍勒富于宗教色彩的愛,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更易產生共鳴。
從斐德羅到舍勒,其思想精髓和基于愛而組建的現代家庭是相通、融貫的,均認同愛在人生、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二、現代家庭倫理關涉的愛
在世界融合的格局中,當下中國的家庭倫理具有愛的以下特點。
(一)老年父母與子女的愛
國家統計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1242萬,占總人口的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為13755萬,占總人口的10.1%。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5月13日發布的世界衛生統計顯示,全世界人口預期壽命較以往有所增長,中國人口預期壽命是75歲,其中男性74歲,女性77歲。兩組數據聯系產生的結果是,老年父母與子女情感延續時間變長,可能會導致愛變得更為復雜。
2014年10月2日18時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以系列報道的方式,報道了老年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其中關于“老漂族”的報道讓人印象深刻,這些生活自理能力不足,隨子女在陌生城市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人際交往有限、情感空虛、與子女的配偶關系緊張、家庭生活不夠愉悅,與子女的愛成為無法啟口的敏感話題。
(二)老年父母與孫兒女的愛
2014年11月6日APEC領導人會議周首場新聞吹風會上,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牟虹表示,中國13億多人口中有6.63億婦女,占人口比例的48.7%;2013年中國就業人口總數達7.7億,其中女性占45%。這組數據能夠有效說明的問題是:追求性別平等的成效顯著,女性參與社會事務的步伐在加快;同時反映出的問題是,以家庭生活為重心的女性挺身職場,家務的料理、孩子的照顧只能由老年父母即隔代的爺爺奶奶代勞,俗語講的隔代親由此凸顯。
隔代親是一個聽上去暖心、充滿濃濃愛意的詞句,但當它與留守兒童緊緊相連,反映的卻是現實生活的凄涼與無奈。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約15.1%、近1000萬孩子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即使在春節也無法團聚。[1][2]
1000萬孩童長年和年邁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有關留守兒童的種種負面報道也就不足為奇了,應該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掙扎著、承擔著養育年幼孫輩的任務,應該在父母膝下享受快樂童年的孩子在孤單中成長,老年父母和孫兒女的愛被現實的生活牽絆著,純潔的隔代親添加了瑣碎的生活斑點,同出一脈的純凈的愛泛溢著艱辛的浪花。
(三)父母與子女的愛
西方學者大衛·波普諾認為,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執著于個人表達、事業成功和物質收益等自我關照的核心問題,降低了對兒童的關注。
“78.8%的留守兒童擁有手機,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2.8%,在上課和課間使用手機上網的留守兒童比例分別為12.3%和46.2%,這兩項內容分別高于城市未成年人近10個百分點和33個百分點。由于留守兒童的特殊性,新媒體對他們而言并不僅僅是提供信息、增長見識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還扮演著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5]這則報道反映了4700萬兒童由于父母的缺位,手機取而代之扮演著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
然而,遺憾的是,那些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似乎也不走運。一篇題為《孩子建議回家沒收父母手機 不陪伴也是冷暴力》[5]的文章寫道:某教育機構讓孩子們圍繞困擾他們成長的問題,結合想象進行創意挑戰賽活動,現場近20個二年級到初二的孩子,都提到父母沉迷手機冷落自己,提出沒收大人手機的創意。父母這種無形的冷暴力對孩子的傷害是不容小覷的。
留守兒童缺少的是陪伴,父母沉溺網絡的孩子缺少的是陪伴,父母忙于工作的孩子缺少的也是陪伴,而融入真情的切身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愛的行為和愛的表達,是通過愛構建的一種良好的人倫關系,但現代家庭嚴重缺乏以陪伴為形式的愛、更缺乏愛的順暢表達,愛的殘缺容易導致家庭危機和家庭成員個人危機的發生。
三、愛的成長層級
現代化以不同的步調在不同的文明中發展,追求性別平等初見成效,家庭倫理關系的軸心從縱向的父子關系轉變為橫向的夫妻關系, 家庭倫理也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在嬗變。為了家庭關系和諧,家庭幸福恒久,不斷投入感情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愛情的情愛是現代婚姻家庭倫理的基礎,層級較高的友愛更具社會意義,而博愛才是愛的真正歸宿。
(一)情愛
隨著個體生命對自主權的重視,人們不再根據外在審判或守舊的家庭標準尋覓生活伴侶,而是在自我權利的啟示下,強調基于愛的情感活動。情愛的范疇是一個獨立的人對另一個人的主動的、出于自身意愿的、賦予感情的某種活動的喜愛以及出于此種感情而做出的行為,是由美的對象激發的情愛活動。情愛源于對彼此的認可和喜愛,隨著這種行為的加深,將對方確定為戀愛對象乃至結婚對象,便會導致家庭生活的焦點從社群和社區轉移到夫妻關系上來。這種關系起初被強烈的角色期望所控制,對彼此的角色期望主要表現為一種正面、積極、理想的形象期待。
期待的美好和真切的現實并存,二者關系的調和依靠婚姻關系的建立。婚姻作為一種強大的制度,是家庭生活的基礎。如果伴侶之間的感情沒有在婚姻生活中得到順利發展,婚后家庭生活將被質疑且充滿危機。民政部發布了《2014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全國共依法辦理離婚登記363.7萬對,2003年以來我國離婚率已連續12年呈遞增狀態。[6]源于自發,始于情愛的家庭緣何成為易碎的花瓶,除去微觀層面個人未能有效抵抗外界對婚姻關系的干擾外,宏觀社會層面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牟虹在2014年11月6日APEC領導人會議周舉行首場新聞吹風會上表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女公務員數量達168萬人,約占公務員總數的24.1%。在農村,婦女占農業勞動者總數的65%以上,許多婦女成為新農村建設的致富帶頭人。
職場的乘風破浪和家庭的柴米油鹽如何平衡,是千萬個家庭每天必須面對的現實又具體的問題,在婚姻中保持彼此的進步,通過德性教育的方式促進愛的成長顯得極為重要。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涉及該議題,他認為德性的養成是在自然的基礎上,通過不斷的訓練和教導而養成的習慣,形成倫理德性習慣化的過程是不斷地做各種向善事情的過程,從而將從做事情的過程中習得的德性融入自己的本性中,習慣化是倫理德性得以實現的過程,而人具有聽從理性勸導的潛能,形成德性則是這種能力的實現,養成的德性繼而體現在活動中,則是第二層次的實現。
由此可見,情愛是可以通過德性培養的方式獲得發育機會的,她不僅在家庭創建伊始具有奠基意義,更重要的是在長期的婚姻生活中要給其提供德性的土壤,情愛方可茁壯成長,長足發展。
(二)友愛
《尼各馬科倫理學》最早提到友愛的是第二卷第7章,友愛被看作是一種在一般生活方面的愉悅性品質。在注重血緣親情的中國社會,父母同多子女的共同生活情境中的親情更加趨近亞里士多德筆下的友愛,因為亞里士多德當時生活在城邦,對以家庭為生活社區的情狀有較多了解。不論是兄妹之間的友愛還是由陌生人建構的朋友之間的友愛,都是因對方自身之故而發生的,為著對方的善,不過由這種共同生活派生的兄弟的共同生活與愛似乎是所有其他愛的最為直接的母體形式。[7]原因主要是兄妹之間的友愛以血緣感情為主要維系方式,而朋友之間的友情會涉及法律、契約等非感情因素。
當下,現實的情況是由父母主導的多子女大家庭時常伴有不友愛行為的發生,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民間糾紛和法律案件并不鮮見。細探下便會發現,這類事情多和家庭財產纏繞不清,透射出物質財富在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也反映了基于血緣親情的家庭倫理在現代化社會中出現的困境。走出困境首先需要明辨的是問題的當事雙方或多方主要以血緣感情為主要維系方式的友愛,和嚴肅、冰冷的法律之間存有難融性,此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根源。
家庭倫理多涉及血緣,家庭中的友愛相較于情愛中的男女雙方的感情更為多元,建立以友愛為基調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多向善的德性的培養和更多德性的付出。
(三)博愛
德國哲學家馬丁·布伯在其成名著作《我與你》中較為深刻地探討了愛的關系和愛的行為,“人也棲身于你之世界,當我與‘你相遇時,我不再是一經驗物、利用物的主體,我不是為了滿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謂‘愛的需要)而與其建立‘關系。因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當以我的整個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來接近‘你,稱述‘你”。[8]在我與它因相遇而構建的關系中,它是與我相遇又相分離的對象,分離是相遇的結果或者是下一次相遇的開始;在我與它產生關聯的關系中,我是主體,是主體性的存在者,它是與我產生關聯的在者。但存在者的存在依賴于在者的存在,否則就不會出現相遇,更不會有相遇關系的發生。但為了讓以主體性身份存在的我處理好與在者的相遇關系,我必須有限有待地對待它。這樣既不會減損我的主體性也不會將在者或它淪為我經驗或我利用的關系,而是在你愉我歡中,恰當地處理了一種相遇的關系。重要的是,相遇關系的恰當處理皆源于愛的存在和愛的行為,是因為我與你之間是一種愛的關系,是愛高明地處理了我與你之間的相遇關系,愛的能力是確立人的主體性原則的應有之義。
循著這條思路,布伯打破了宗教之間的隔閡,他的學說不再被視為猶太教中某一異端的代表,而是整個世界所珍視的財富。1965年布伯去世時,阿拉伯學生聯盟派出代表團參加他的葬禮,向這位猶太思想家致哀。
若能在物質浸染的現代家庭倫理中引入這樣較高層級的愛的哲學思想,我與家庭成員的關系,你與家庭成員的倫理道德皆可呈現良好狀態。博愛思想能讓現代家庭倫理走出危機,讓現代家庭倫理的愛的榮光福照未來。
[ 參 考 文 獻 ]
[1]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14:235.
[2] 孫亦平.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98.
[3] 肖欣.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DB/OL].中新網,2015-6-18.
[4] 蘇婷.第八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狀況調查報告發布[DB/OL].中國教育新聞網,2016-1-5。
[5] 網易親子綜合[DB/OL].http://baby.163.com/13/1217/16/9GAFRA2C00362USS.html,2013-12-17(16):41,22.
[6] 吳為.全國離婚人數12年連漲 微信陌陌成“新殺手”[N].新京報,2015-07-05.
[7]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14:227.
[8] (德)馬丁·布伯著,陳維剛譯.我與你[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5.
[責任編輯:劉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