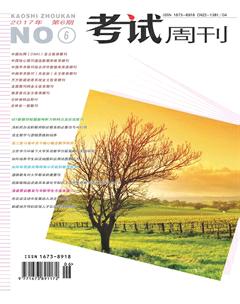對我國高校清考現象動因分析
張微+朱平
摘 要: 勞動力市場的低迷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導致大學生就業難,行政管控的邏輯強力支配等因素對高校教育教學管理提出新的挑戰,由此催生出掩蓋教學質量下降,維護高就業率假象的一種非正常的考試制度。清考產生的外部動因:一方面是行政管控下高校的“實然”選擇,另一方面源自投入成本的上升導致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期望值增加。清考的內部動因,主要是高校面對大眾化帶來質量問題的“應然”選擇及嚴進寬出的高等教育體制。
關鍵詞: 高校清考 行政管控 投入成本 教學質量
20世紀90年代末,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及高校大規模擴招,我國高等教育在多重制度牽引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發布的數據,2004-2014年,高校錄取人數的年增長率平均為10.7%,錄取率由59%提高到74.33%,是1978年的12.3倍,高校畢業生已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主力軍。然而,高校規模的擴張并沒有完善的制度體系與之匹配,一方面是外部對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不斷上升帶來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是高校內部對大眾化帶來的問題應對不當引起教育質量的日益下降。清考作為可以間接提高就業率,掩蓋教育質量下滑的方式悄然而生。清考是針對在某門考試中未通過多次補考甚至重修后依然未通過的學生,進行的一場畢業前由學校或者學院組織的非正常考試。清考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卻并不能真正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也不能破解高校教學質量下降的困局,可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要解決該問題,首先需要理清高校執行清考的動因何在。
一、高校清考現象形成的外部動因
1.行政管控下的“實然”選擇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普及,高校畢業生人數不斷增加,供求矛盾突出,教育部對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在《關于做好201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中規定:“對就業率連續兩年地域60%的專業,調低招生計劃直至停招。”這一規定自頒布以來就成為各大院校的“緊箍咒”,也充分顯示了教育事業的功利性評價導向。《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2014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國發辦[2014]22號)強調“充分認識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聚焦重點難點,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擺在就業工作的首要位置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在《教育部關于做好2015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教學2014[15]號)中表明“2015年宏觀就業形勢面臨多重壓力,高校畢業生規模進一步加大,就業創業工作任務十分艱巨”,督促各地部門和高校強化就業創業體系建設,提升就業創業學生的比例。然而,由政府推動的強化高校社會職能,保障大學生就業的政策議題是否真正能夠緩解社會就業壓力還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明確,政策導向引發的對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與高校辦學理念的嚴重脫節已經成為阻礙高等教育與社會需求良性互動的重要因素,也成為促使本科高校實施清考的根本動因。
當前,我國高校辦學模式仍表現出行政管控的制度邏輯,以政府的行政力量驅動和誘導高校教育教學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呈現“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首先,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行政管控,在中央政府出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2014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之后,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紛紛出臺相應的文件落實大學生就業相關事項,其中《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大力度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的意見》(川辦發[2014]26號)指出“將其放在就業促進工作的突出位置,保持高校畢業生就業局勢總體穩定”。杭州市在《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杭政辦函〔2014〕168號)中明確指出要加大就業援助力度,等等。其次,政府對高校的行政管控,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清政府學習西方的辦學模式,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目的,由政府監辦并掌控的大學。長期以來,我國大學被視為政府的附屬機構,政府習慣于采取行政管控的方式領導和管理大學。由此可見,我國本科高校實施清考主要受到行政管控邏輯的強加支配,過度重視數目管理,強化高校排名,以就業率論英雄,忽視了將不合格“產品”推入市場對社會有限資源的占用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后果。
2.投入成本的上升導致人們對本科以上教育的期望值增加
組織理論認為,組織規模的大小影響著組織結構的變化[1],而組織規模主要指組織擁有的人數。我國高等院校從2003年到2014年短短十年間,毛入學率從15%擴大至37.5%,較十年前翻了一番。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宏觀政策,另一方面在于人們對于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迫切而巨大的需求。縱觀教育發展史,毛入學率的增長與各國人均GDP的增長高度正相關,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研究表明,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各成員國平均受教育年限出現顯著提升。其組織成員國199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數已經達到16.5年,已超過本科畢業年限。經濟的增長使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而這也將導致投入成本的上升。高校的教育成本大部分由政府以教育經費的撥款方式承擔,另一部分由家庭承擔,以學費的形式上繳至學校。根據《教育法》規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逐步提高,全國各級財政支出總額中教育經費所占比例應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
投入成本的上升使家庭對于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不斷增加,自高考恢復以來,國家對大學生的重視使得受教育人群在各行各業獲益匪淺。其家庭生活的質量及社會地位明顯優于其他社會人群,在“學而優則仕”的導向下,對教育的投入越高可以達到更高效益已經成為許多家庭的共識。尤其在教育高消費時期,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費用占總支出的比例遠遠高于高收入家庭,對子女的回報期望值更集中于好的就業崗位。對他們來說,獲得好的就業崗位成為衡量教育質量和辦學成果的標準。在付出巨額成本的情況下,沒有與之匹配的工作崗位,無論對于學生個人還是家庭都是不利的消息,甚至會影響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觀。
二、清考現象成因的內部動因
1.教學質量下降的“應然”選擇
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及高職院校)共2529所,比1999年的1071所增加了2.36倍;高校注冊大學生,在絕對數上已經達到2547萬(包括普通高校與成人高校),成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國。隨著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不只是量的增長,也帶來“質”的變化。馬丁·特羅在總結發達國家大眾化進程規律時,就指出量的增長必然引起“質”的變化,并表明“規模是一切問題的根源”[2]。教學質量的下降,主要原因是高校對大眾化問題應對不當,沒有正確處理數量與質量的矛盾。教育資源難以滿足招生速度的快速增長,一方面主要表現在教育經費不足。政府對學校的投資主要來源于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收入由1999年的1144.08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349.74億元,財政收入雖出現大幅上漲,但高等教育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并沒有出現大幅增長。另一方面是師資短缺,1997年師生比1∶7.8,現在是1∶18.3。雖然1999-2014年教師隊伍保持穩定增長,教職工總數達233.6萬人,專職教師總數達153.5萬人,教師隊伍數量世界第一,但我國學生基數與師生比仍遠高于世界一流大學。2010年,據美國《新聞周刊》對1311所大學的調查,平均師生比為1∶14.8。老師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應對學生的發展,無形中增加了老師的教學負擔。此外,隨著錄取人數在考生中所占比重的不斷增加,生源質量隨之下降,學校原有的教學模式已經無法帶來原有的效益,令老師的教學難度加大。簡言之,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相當多的崗位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門人才勝任,而教學質量的下降不免使企業乃至社會公眾對高等教育成效產生懷疑。
2.嚴進寬出的高等教育體制
高考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成為我國“第一考”,導致形成“獨木橋”現象,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普及及高考體制的改革,這一現象有所減弱。一旦進入大學,眾多學生失去緊張感和目標感,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嚴進寬出的教學體制,而這也是造成高等教育質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西方教育學者認為高等教育的目標是智慧,學生所選專業課程并非為了獲得穩定的工作,而我們太過強調“學以致用”,缺乏分析事物的基本能力。需要強調的是,西方教育也存在考試,美國高校甚至將考試作為檢驗學生學習成績的主要手段,其實也是重要的育人手段,但考試題目多是對于實際情況的分析及解決方案的設計。并不要求死記硬背,考試不是對記憶力的考察,而是對問題理解、分析、解決的考核。而且學生的期末成績往往由平時成績與期末考核幾部分構成,平時成績權重往往高于期末成績。反觀國內教學模式,重結果而輕過程,講究結論的唯一性與確定性。
三、對高校清考政策的反思
反復審視研究,清考制度是由諸多問題引起的,斷不可一概而論。“任何一種大學制度的建設都是選擇的結果,都是一個經過選擇的制度”[3]。從客觀因素來說,高校清考現象的存在主要是因為全社會沒能形成一種“教育為先”的理念。“教育為先”要求大學將育人作為首要任務,然而,大學不僅把就業率作為評判教學質量的因素,更將其作為標榜自己教育成功的標志。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傳統的大學理念的淡化,大學自身本位理念的缺失。大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迷失自我,出現為政策和市場而大學失位的表現。再者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導致大學畢業生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職業,進而造成掛靠就業的現象。最后政府作為主導高校的強勢一方,對高校的發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使大學淪為政府的附屬品,失去特殊性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首先,“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4]。大學應該認清自身的多重責任,以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項職能為根本,以大學本質屬性所要求的任務為基礎,并對受教主體負責,對社會發展負責。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欲望,大學都應憑借文化良知、憑借對真理的虔誠和對正義的維護做出正確的判斷。
其次,大學應該客觀地對待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黨和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為發展教育事業而制定的行動準則”,對高校各項制度的制定具有指導意義但不具有強制性。對教育主管部門出臺的教育指導性政策,大學要報以客觀態度進行解讀,不能聽而任之。畢竟“大學具有政治功能,但它不是政治的工具;大學具有經濟功能,但他不是經濟機器”[5]。學校不應將“職業性”過度強化,把就業率當成學校生存和發展的指揮棒,進而將學生異化成提高就業率的工具。
最后,學校應該落實淘汰機制,留級或退學,保證出口的通暢。學得好與學得不好的都可以畢業,教育公平性何在?公平并不是均等,公平的教育應該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學識和能力獲得相應的“報酬”,而不是搞特殊主義,走“綠色通道”。實際上,只有真正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把學生培養成完整的人、全面發展的人,才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就業前景。那些學識和能力沒有達標的學生,“回爐再造”恰好是給他一次自我完善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成為適應經濟發展的人才。
總之,清考作為國內部分高校的特有現象,雖然具有緩解矛盾沖突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但也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不利于社會資源的配置,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只有標本兼治,才能解決此問題。
參考文獻:
[1]斯蒂芬·P·羅賓斯.孫健敏,李原譯.組織行為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美]馬丁·特羅.從精英向大眾化高等教育轉變中的問題[J].1973.
[3]鄔大光.論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J].中國高等教育,2006(19):14.
[4][美]弗萊克斯納.徐輝等譯.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5]樸雪濤.知識制度視野中的大學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