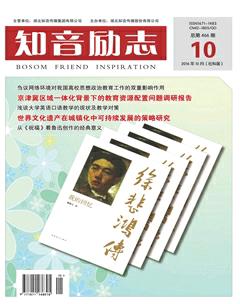探尋“讀”“寫”之道
陳瑾瑜
閱讀和寫作是中學語文教學的兩大支柱,是語文學習的主要內容。因此“讀”和“寫”也是我們語文教學過程中最常用的教學方法。相信每一個語文老師都曾諄諄告誡自己的學生:“要多讀書,多積累,作文才會寫得好。”于是,學生努力讀書,做摘抄,寫點評,但遺憾的是其實很少有學生真正獲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驚喜。究其原因,我認為還是在于學生“讀”和“寫”存在脫節現象,未能探得讀寫之“門道”,大部分學生通過閱讀吸納的營養未能有效地轉化為寫作能量。那么,如何讓學生的閱讀真正轉化為一種語文的能力,如何讓學生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閱讀的樂趣,從而真正愛上閱讀,愛上語文?本文結合自己的閱讀、寫作教學實踐,談談在探尋“讀”“寫”之道過程中的粗陋想法。
【關鍵詞】讀寫;語文課程
1 重新認識中學語文課程中的“讀”和“寫”
現行新課程理念指導下的教材編排,是以內容為中心的模塊和專題教學,在讀的方面強調文本內容的思想性,學生通過閱讀感悟和體驗文本的情感價值,吸納作品的思維成果,卻無暇顧及領會思想情感的載體——語言文字、構思技巧等,也即忽略了作品形成的思維方法和過程。
從寫作教學方面來說,由于教材缺少系列的寫作理論指導,教師缺乏開發作文課程資源的能力,導致寫作教學實際上處于語文課的邊緣,漸漸變得無序無范。
在處理讀和寫的關系時,我們習慣于將閱讀和寫作分成兩個相互獨立的板塊,閱讀課注重引導學生讀懂文本、鑒賞文本,理清層次結構,關注寫作特點;到了寫作課又另起爐灶,從選材到立意,從構思到表達,自有一套作文高分理論來指導。把作為基礎教育的中學語文這樣區分,實際上是一種人為的割裂, 導致很多教學中的“讀寫結合”“讀寫互動”淪為形式主義的表演。
所以我認為,中學語文課程中的閱讀,不是休閑消遣,也不是專題研究,而是一種知識經驗的積累。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思維過程、思維方式的物化形態,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吸納借鑒作家的思維方式,學習作品的遣詞造句,豐富自己的情感體驗,這就是學識、情感的積累過程。而中學語文課程中的寫作,就是把閱讀積累吸納的東西,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準確生動具體恰到好處地表現傾吐出來。寫作不是閱讀的附屬品,而是讀的效果顯現,是思想認識的結晶,是讀的物化形態。再者,在基礎學習階段,學生語文素養或語文能力檢測的主要依據就是寫作,“千讀萬讀,只為一寫”的說法或許有功利之嫌,但毋庸置疑,基礎教育階段的寫應該是讀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我們理應構建起由閱讀到寫作的整體把握的教學思維模式,努力引領學生積極探尋“讀”“寫”之道。
2 善教才善讀,善讀才善寫
葉圣陶先生說:“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可見閱讀是寫作的基礎,閱讀應該給學生寫作內容、構思方法、表達形式等方面的啟發與借鑒。如果我們把語文閱讀和寫作這兩大陣營看成是一條河流的兩岸,那么,老師就是這條河流上的擺渡者。從此岸到彼岸的擺渡過程中,努力做好以下幾點:
2.1 精選讀本,明確讀法
魯迅先生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密事。”可見,經典范文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作為語文教師,我們當然希望從中得到教學的啟發。下面就結合小說中 “香菱學詩”這一片段談一談教師如何指導學生閱讀。
聰明而又苦命的香菱進入大觀園前,閱讀有限,對作詩的方法知之甚少,更沒寫過詩,但后來卻一鳴驚人,所作的詩獲得一致好評,在大觀園內的一系列作詩活動中均有不俗表現。取得這樣的成績,和她在大觀園遇到的老師——林黛玉是分不開的。
黛玉老師首先說詩歌“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寥寥數語就講明了格律詩知識,整體構思、語言韻律皆有了要求;不僅定下了寫詩的“格調規矩”,同時又指出了可以“出格”的條件:語言(或素材)新奇。我想,學生閱讀首要想獲得的是前人學識、經驗的積累。所以,格調規矩、素材出眾應該是我們選擇范文的兩個基本標準,文質兼美則為經典范例。
接著當香菱表示“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有趣!”黛玉馬上明確指出:“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然后進行了具體的閱讀推薦:“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黛玉真是深諳讀寫之道,精讀教材有了,泛覽篇目夠了,才能打好扎實的寫作基礎。可見老師對學生的閱讀指導不能籠統地一言以蔽之“多讀書”,而要明確讀哪些書,讀到什么程度。
2.2 找準讀寫結合點,發揮閱讀文本的“范例”作用
在上述林黛玉教“香菱學詩”這個教學案例中,我們尤其不能忽視的是老師提出了很明確的閱讀要求:精讀篇目要“細心揣摩透熟”,作為泛讀的“底子”。而這些需要“細心揣摩透熟”的地方,往往就能作為讀寫的結合點,形成寫作契機。正如葉圣陶所說“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而已。”閱讀的意義就在教會學生表達,教學中老師要善于捕捉這些寫作契機。
2.2.1 圈點精華處,借鑒仿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也說過,語文技能“只有通過正確的模仿和反復的實踐才能養成”。經典范文,有很多可圈可點處,細心揣摩這些地方,選擇一個角度進行仿寫訓練。從細節上說,古典詩詞中的字詞推敲,名家散文中的傳神敘寫,議論說理時的詼諧幽默、入木三分,都能成為學生借鑒模仿的對象,提高遣詞造句的能力;從整體上看,模仿作品高遠的格調、精巧的構思有利于提高學生謀篇布局的能力。總之,取其精華模仿,聯系生活創作,這種尋找相似點,生發新內容的仿寫訓練,就像一座由積累、繼承走向創新寫作的橋梁,真正的貫通了閱讀和寫作,并且當妙語佳句在筆下流淌時,學生會充分體驗到模仿與創作的快樂和滿足,進而迸發更高的寫作熱情。熟能生巧,漸漸從讀寫中領悟到寫作規律。
2.2.2 發現留白處,想象補寫
現象學美學家英伽登認為:作品是一個充滿了未定點和空白圖式結構,需要讀者通過創造性想象去確定和填補。例如在歐亨利的《最后的常春藤葉》中,作者沒有正面描寫老畫家貝爾曼是如何畫出他的“杰作”的,教學時可讓學生在閱讀中展開想象,合理地補寫出貝爾曼畫藤葉的情景。補寫過程中,學生不僅有了場景描寫、人物細節刻畫能寫作能力訓練,而且能體會到貝爾曼的善良人性,更能通過自己的思考展開與文本、作者的零距離對話,體會普通人之間的無私情誼,獲得心靈震撼。再如《邊城》的結尾,翠翠最后還守著渡船,等待著自己心愛的人歸來……有情人能終成眷屬嗎?抓住情節空白,探討翠翠今后的命運,何愁無話可寫?教師善于這些利用文本空白引導學生“作文章”,并進行舉一反三,串聯其他文本的閱讀,就能不斷讓思維得以訓練,學生的讀寫能力就會不斷提高。
2.2.3 設計比較處,研究探寫
比較是最樸素的認識事物的方法,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群文閱讀比較,易拓寬學生的視野,在異同點的對比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例如我們把蘇教版教材中的《短歌行》《赤壁賦》《滕王閣序》《蘭亭集序》組建為一組群文。充分閱讀之后設計幾個比較點,引導學生思考、探寫。一是“求同”:作品流露了相同的思想,即面對宇宙的無窮,生發人生短暫、虛無的悲涼之感。二是“求異”:作者釋懷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有人生苦短,要及時享受清風明月;有生命有限,更要有為……三是“求深”:這些釋懷方式有無高下之分,孰優孰劣,都應探尋思想根源。《蘭亭集序》的思想探究可結合魏晉文化中的玄學思想,而用老莊哲學解讀《赤壁賦》,則更能領悟主客對話中傳達的大智慧。最后若能跳出這一組群文,跳出人類固有的“生命有限,宇宙無窮”的情感困境,把劉慈欣的《三體》、霍金的《時間簡史》等推薦給學生,讓學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更廣闊的視野感受生命的意義,感受時代的進步。我想,堅持這樣的閱讀、思考、寫作訓練 ,學生的寫作視野,胸襟氣度都將產生質的飛躍。
3 把握契機,厚積薄發
“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廣泛的閱讀、思考,打好了知識、精神的底子,頭腦中對人對事自然有了一定的想法;閱讀過程中老師的引導、點撥又讓學生獲得了一定的寫作技法。“有想法”、“有技法”可以說是動筆寫作的兩個基本要求,從心理上說,這時也是孔老夫子所提倡的“憤悱”狀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美好愿望才能實現。2015年江蘇高考“智慧”滿分作文《農之月令》,作者就是憑著對自然節氣的熟知,對鄉村文化的關注,深厚的語言表達功底,巧妙的表現了對農人生活智慧的禮贊,獲得了閱卷組的青睞;再如當年一鳴驚人的湖北考生的滿分古體詩歌《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讓人拍案叫絕,很多人猜測這篇考場作文 “早有準備”,但我想這里的“早有準備”,就應該是長年累月的閱讀積累。當有了表達的契機,厚積薄發,水到渠成。
當學生享受到了作文成功的喜悅,或是生活中有了感同身受,獲得頓悟,從此愛上閱讀,這也是契機。記得在高二議論文寫作訓練時,學生曾寫過《沉默是金》,我提醒學生,在觀點明確的前提下,這篇文章可以從原因入手分析,然后一起討論了“沉默”一些原因:不讓說、不敢說、不便說、不該說、不必說、不屑說……,以及這些原因背后的人性本質,學生也認可,但作文說理時明顯空洞無力。但有一天,一個學生滿臉激動的捧著本書跑過來,大為驚奇的嚷嚷:老師,周國平也這么說的!大有相見恨晚之憾。他用熒光筆圈劃了整整一段:“……沉默就是不說,但不說的原因有種種,例如:因為不讓說而不說,那是順從或者憤懣;因為不敢說而不說,那是畏怯或者怨恨;因為不便說而不說,那是禮貌或者虛偽;因為不該說而不說,那是審慎或者世故;因為不必說而不說,那是默契或者隔膜;因為不屑說而不說,那是驕傲或者超脫。這些都還不是與語言相對立的意義上的沉默,因為心中已經有了話,有了語言,只是不說出來罷了。……”我想說的是,這個同學從此愛上了周國平的哲理散文,同時也學會了議論文中的原因分析!或許“讀”與“寫”之間有時就需要這么一個契機。
元代教育家程端禮曾把閱讀與寫作比喻成銷銅鑄器,讀書是銷銅過程,作文是“隨模鑄器”,所以“勞于讀書,逸于作文”。確實,閱讀積累的過程漫長、繁瑣,見效甚慢,學生容易懈怠放松甚至畏難放棄。所以在學生閱讀過程中,老師要不斷啟發、點撥和引領,努力創設和探尋讀寫契機,爭取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要努力創設條件,讓學生感受作文之“逸”,從而堅定信心,收獲讀書之樂。
作者單位
江蘇省錫東高級中學 江蘇省無錫市 21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