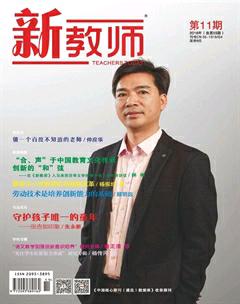淺談漢字教學中的“ 形義”結合
葉斌
據統計,東漢許慎編纂的《說文解字》收錄漢字9353個,其中的形聲字有8057個,占82%。在現代7000個通用漢字中,形聲字也占80%以上。因此,可以說,掌握了形聲字構字特點,便是找到了識寫漢字的竅門。那么,在小學語文教學中,如何更好地教好形聲字?如何幫助學生在“形旁”和“字義”間建立起聯系,從而有效防止、消除錯別字呢?
一、夯實基礎:由“形旁”推想“字義”
一年級上冊“識字”“課文”交替安排,有關識字方法的教學,較多地集中在“語文園地”中。識字(一)《口耳目》一課,運用圖示、象形字和現行漢字進行比較、連線的方法,展示漢字演變的大致過程,由此引導學生學習幾個簡單的獨體字,形象直觀,便于理解和識記。更重要的是,由“圖示、象形字”,學生初步了解了漢字的造字方法,這對今后漢字的理解和識記起到很好的奠基作用。
在一年級諸多“語文園地”中,較多地開始識字寫字方法的教學,比如:加一加、減一減,換個偏旁成為新字,通過漢字各個部件的拆解與合成,幫助學生初步建立漢字大多是由形旁、聲旁構成的意識。課本安排的“扌、、艸、木”等偏旁,在眾多的形聲字中多為表形的。一年級學生認識了這些偏旁,對今后漢字的學習和識記,能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因此,在教學中,不能只是認識或會寫課本中出現的那些字,還應對此類偏旁的字做歸納和總結。像一年級下冊“語文園地四”有個提示“我發現目字旁的字和眼睛有關”,就是引導學生發現漢字規律和方法的練習。4組字分別是含有“月、、目、扌”等偏旁的字。有學生說他發現目字旁的字和眼睛有關。教師可以就此進行啟發:我們還發現什么呢?學生可能發現了足字旁的字和腳有關,月字旁的字和身體有關,木字旁的字和樹木有關……在學生暢談發現的基礎上,教師小結規律:“形聲字,分兩半。形一半,聲一半。形旁相同是同類,形旁不同意思變。”再由此推而廣之,對先前學過的字進行一次復習和提升。如,帶“讠”的字,多與語言有關;帶“纟”的字,多與絲線有關;帶“氵”的字,多與水有關等等。這樣,形旁意識就會在學生腦海中牢固地樹立起來,學生將來就能通過字形推想其字義,也可以根據字義推想其字形,這是非常重要的識字方法的教學,是將來語文學習的根基,是可以讓學生受用終生的。
可以說,第一學段的語文教科書,在由“形旁”推想“字義”方面,體現了循序漸進的原則,教師應充分利用教材,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識字方法,為后續的學習和掌握漢字打下扎實的基礎。
二、提升認識:由“字義”推想“形旁”
在央視“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上聽寫“社稷”一詞時,一位優秀的選手卻將“稷”的“禾字旁”寫成了“示字旁”。第二現場的錢文忠教授說得好:“如果這個孩子知道‘稷是指古代一種糧食作物,他就不會把它寫成示字旁,真可惜!”類似的現象在小學生中同樣常見。比如“神、祥、禱”等字,學生就常寫成了“衣字旁”。這樣的字為何會寫成“衣字旁”呢?第一學段的教材中清清楚楚地進行過相應的教學:“衣字旁的字,都與服裝、被子等有關。”難道“神、祥、禱”都與衣服有關嗎?衣字旁的字,都與服裝、被子等有關,那么示字旁的字,都與什么有關呢?……筆者分析,產生上述錯別字的主要原因,是回生現象。學生升上中高年級,學習的內容更廣了,對原先已識的字以及所掌握的識字方法、規律會逐漸淡忘。因此,應適時對所學的識字、寫字方法進行復習、鞏固,同時還需要向更深更廣處提高和發展。《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也指出:“識字、寫字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是第一學段的教學重點,也是貫穿整個義務教育階段的重要教學內容。”由此可見,義務教育階段的識字、寫字教學就應該在方法上做足文章。遺憾的是,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第二、三學段在這方面并沒有給予有效的導引,除了三年級有7次“讀讀認認”“形近字組詞”“形近字比較”等出現在各組的“語文園地”之中,其方式方法也是沿用第一學段“加一加、減一減、換一換”等,并沒有新鮮的、體現更加深入的方式方法。
曾聽到于永正老師執教的一節五年級語文課《祖父的園子》,課伊始,檢查預習,于老師請兩名學生到黑板前,聽寫兩個字:“帽、拋”。兩位同學很容易地寫出了這兩個字。于老師評點:“帽”字右上角,不是“日”也不是“曰”,下邊的兩橫不能挨到兩邊的豎,并在黑板上畫出了“■”,說,這個部首單念“mào”,是個象形字,“王冕”的“冕”的上部分也是“mào”。接著,展示書法家手寫的“帽”字進行賞析,然后,所有同學伸出右手,跟著教師寫“帽”。教師邊寫邊提示,“巾”的一豎要寫得長一些,“冒”字上寬下窄,最后,全班同學齊讀“mào”。一個簡單的“帽”字進行這樣不簡單的教學,這給我們許多啟示。
名師在前邊引路,我們普通教師也要加強學習和修煉。“示”在甲骨文中像祭神的石柱,所以,“示字旁”的字與神有關。古人崇尚信仰,認為吉兇禍福由神主宰,因此與吉兇禍福有關的字都用“示字旁”表示所含的意義。“祥”是吉祥的意思,“禱”是指教徒或迷信的人向天、神求助……理解了帶“示字旁”的字的字義,就可以推斷這些字都是“示字旁”,而不會再寫成“衣字旁”。問題是,類似這樣的匯總與梳理,該在第二、三學段的什么時候進行呢?這樣的匯總與梳理也可能因教材沒有安排而缺失,那么,留在學生腦海中的就是一片混沌,他們拿起筆就信手而寫,是對是錯只能交由運氣決定。
所以,教師在閱讀教學時,千萬不可在“文章解析”上大動干戈,而把“識字寫字”視作兒科。要根據不同年級、不同教材,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對一些生字進行歸類與梳理,引導學生將字的“形義”結合起來,由“形旁”推想“字義”,再由“字義”推想“形旁”,從而提高自主識字能力。很多教師在這方面已積累了相當好的經驗。比如“辨、辯、辮和瓣”等字的辨析,有的教師就很巧妙地運用“形義”相結合的辦法編成“順口溜”:點撇似眼睛,能把物分辨;有言把話講,辯論道理清;頭發編成條,絞絲是辮子;瓜地花兒香,瓣瓣沁心脾。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不一而足。更有教師在生字教學時,相應地出示這個生字由甲骨文的象形字到金文、到隸書、到楷書的演變過程,如果能同時對此做相應的指導和說明,學生對這個字的識記書寫,印象就一定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