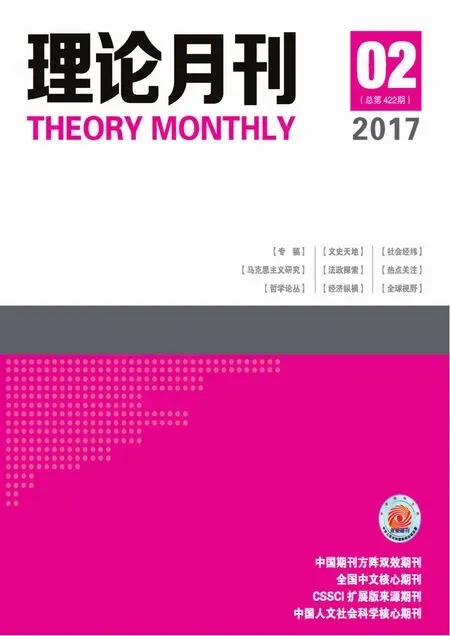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實證研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張遠為,嚴飛
(1.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2.湖北經濟學院經濟學系,湖北武漢 430205)
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實證研究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張遠為1,嚴飛2
(1.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2.湖北經濟學院經濟學系,湖北武漢 430205)
本文運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提取率指標,利用2007年9月至2016年6月我國14家上市銀行股票日收益率數據,研究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研究發現,在銀行股票收益率最低的三個時期,提取率都很高,并且提取率的上升先于股票收益率的下降。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提取率可作為我國監管當局監測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系統性風險;主成分分析;提取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損失。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風險的微觀審慎監管對金融風險監管來說是必要但并非充分的。為防范金融危機,必須監測系統性金融風險,對金融體系實施宏觀審慎監管(Bernanke,2011)[1]。在這一背景下,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成了學術界和監管部門關注的焦點,人們提出了多種測度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法。
當前,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以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在資金融通中仍占主要地位,監測和防范銀行系統性風險對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采用一種測度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新方法——主成分分析法來測度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雖然國內已有不少學者研究過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但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文獻目前還沒有。本文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國在系統性金融風險領域的研究成果。
1 文獻回顧
研究系統性金融風險,首要的任務是如何定義它。不幸的是,對于系統性金融風險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De Bant和Hartmann’s(2000)將系統性風險定義為對大量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產生沖擊、從而嚴重影響金融市場功能正常發揮的事件[2]。該定義強調傳染性,一個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的經營失敗會嚴重地傳染給其它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Monica Billo等(2012)將系統性風險定義為威脅到金融系統的穩定或公眾對金融系統的信心的事件[3]。根據這一定義,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票市場的暴跌不是系統性金融風險,而2010年5月6日美國股市暴跌屬于系統性金融風險,因為后者引起了公眾對金融系統信心的喪失但前者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9)將系統性風險定義為金融系統大面積遭受損失并造成大范圍的金融服務供給中斷、給實體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風險[4]。
雖然學者們對系統性風險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從不同角度的定義具有共性。首先,系統性風險不是關注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而是關注金融體系整體的風險;其次,系統性風險具有傳染性的特點,一個金融機構(或市場)的風險會傳染給其它機構(或市場)、甚至傳染到實體經濟。
為有效地監管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準確及時地測度它的大小。測度系統性風險的方法有很多,這些方法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大類。
第一類方法是基于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聯性來衡量系統性風險,這類方法根據金融機構之間資產負債表的關聯建立一個網絡,并據此來模擬風險由不同節點在正向或負向沖擊下風險擴散的特性來測度系統性風險。基于該方法的文獻主要有:Furfine(2003)運用美國聯邦基金數據來研究美國大型銀行破產所引起的傳染效應,得出市場傳染性不大的結論[5]。Well(2004)對英國銀行的系統性風險進行了研究,得出個別銀行的破產很少會傳染給其他銀行、傳染性的大小與違約損失率以及貸款結構分布有關的結論[6]。Lehar(2003)通過模擬銀行資產的波動情況,運用銀行資產間的相關系數來測度金融風險的傳染,計算出系統性風險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的概率[7]。Billio等(2012)用主成分分析法和Granger因果網絡法研究了美國基金、經紀、銀行和保險四大金融行業資產收益率的關聯性,研究結果表明,在市場崩潰時,四大行業資產收益率之間的關聯性增加。[8]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市場下行時與市場上行時相比,市場的相關性會增加(Brunnermeier等(2012)[9]、Battiston等(2012)[10]、Antonio等(2014)[11])。國內學者,范小云(2011)研究了單個銀行對銀行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大小和相對系統重要性程度[12]。劉紅忠等(2011)通過構建銀行系統性風險測度模型來研究樣本銀行的風險占總風險的比率,研究結果表明:相對于中小銀行來說,國有大銀行在系統重要性中占有主要地位[13]。歐陽紅兵和劉曉東(2015)采用最小樹生成法對我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該方法可以對系統性風險傳導潛在路徑的識別以及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提供有效的手段[14]。
由于銀行的資產負債數據一般較難獲得,再加上資產負債數據的時效性不強,使得基于資產負債表的網絡分析法實用性不強。
第二類方法是基于市場數據的測度方法,這類方法力圖從市場數據(包括股價和CDS價差等)中推導出市場對風險相關性的預期,如CoVaR方法、SSCA方法、DIP模型和EVT-GARCH-CoVaR模型等。Giulio Girardi和Tolga Ergun(2013)用改進的CoVaR模型,研究了四大金融行業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貢獻大小以及金融機構的特性與貢獻大小之間的關系[15]。Hua Chen(2014)等基于信用違約互換價差的日數據和股票價格的日內數據,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研究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的相互關聯性,結果表明銀行對保險公司的影響比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更大并且時間上更持久。壓力測試也證實銀行給保險公司帶來了顯著的系統風險,但不存在反向的影響[16]。Acemoglu等(2015)的研究結果表明,金融傳染呈現出階段變化性,也即是:如果負向沖擊很小,這時金融機構之間的緊密關聯能夠增加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然而,當負向沖擊超過某一臨界值后,金融機構之間的緊密關聯會使沖擊更易于擴散,使金融系統變得更脆弱。他們強調,同一要素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有助于使金融系統恢復穩定,但在另外條件下卻會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來源[17]。Lamont Black等(2016)用DIP模型度量了歐洲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該模型綜合考慮了銀行規模、違約概率和關聯性大小。他們研究發現: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主權債務違約的擴散增加了歐洲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并且意大利銀行和西班牙銀行在歐洲銀行體系中系統性風險貢獻度顯著上升[18]。國內學者,鄭振龍等(2014)利用中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數據,研究了平均相關系數與系統性風險的關系,發現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的平均相關系數衡量了系統性風險[19]。張蕊等(2015)運用EVTGARCH-CoVaR模型,利用股票市場數據,對極端市場條件下單個金融機構對中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及其隨時間變動的趨勢進行了動態測算[20]。李志輝等(2016)運用優化后的SCCA方法以我國10家上市銀行為樣本研究了我國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認為“單個銀行的邊際預期損失分布和不同銀行之間的風險相依結構具有時變性。如果忽視風險相依結構的變化,簡單地對系統內所有機構的損失進行加總,并以此作為系統性風險的度量和監測指標,可能使決策者對風險形勢出現誤判”[21]。
基于市場數據的系統性風險測度方法有以下優點:首先,市場價格的變化反映了市場對未來的預期,故采用市場數據具有前瞻性;其次,市場數據會及時發生變化,因此具有及時性;第三,市場數據相對于資產負債數據來說更容易獲得。因此,近年來,基于市場數據的系統性風險測度方法受到了學者和監管當局的青睞。
本文采用基于市場數據的方法來測度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股票收益率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法來提取銀行股票收益受某幾個因素影響的程度大小(即銀行之間關聯緊密程度的大小),從而測度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大小。
2 模型與數據
主成分分析是一種多元統計方法,它可用來分析變量之間相關性的大小。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運用少數幾個主成分來解釋多個變量的內部結構,也即是,從初始的多個變量中導出少數幾個主成分,讓這少數幾個主成分盡量多地保留原始變量的信息,并且這幾個主成分互不相關(張文彤,2004)[22]。主成分的概念由Karl Pearson于1901年提出,以后經眾多學者的發展逐步完善。自20世紀中期以來,得益于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主成分分析在眾多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
人們運用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對原始數據進行壓縮。在科學研究中,為研究事物之間的關系,人們需要觀察、收集多個變量的數據。雖然這些數據攜帶了反映事物之間關系的信息,但由于變量很多,給數據分析帶來了不少困難;另外,這些變量之間也許存在較強的相關性,變量的觀測數據所攜帶的信息,可能有一部分是重復的。主成分分析就是要在盡可能少損失原有信息的情況下,將原始的多個變量濃縮為少數幾個主成分,這幾個主成分能夠高度涵蓋原始數據中的信息,從而達到既減少了變量個數,同時又能夠再現事物之間關系的目的。
假設初始變量的個數為p,每個變量觀測值的個數為n。主成分分析所運用的方法是將初始p個變量的線性組合作為新的綜合指標,即主成分。如果將選取的第一個線性組合即第一個主成分記為F1,則F1中能反映的初始變量的信息越多越好。包含的“信息”的多少怎么度量呢?最經典的方法是用F1的方差Var(F1)來度量,方差Var(F1)越大則表示F1所包含的初始變量的信息越多。因此,在全部的線性組合中,第1個主成分的方差應該是最大的。如果研究者認為第1個主成分所涵蓋初始變量的信息不夠,則可以考慮選取第2個線性組合F2,即第2個主成分。依此類推,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選取第3個、第4個、……主成分。選取的這些主成分方差是遞減的,并且它們之間互不相關。在實際研究中,一般只需要選取前面幾個最大的主成分就夠了。雖然主成分分析損失了少量信息,但減少了變量的數量,也即是抓住了研究問題的主要矛盾,有利于對問題的分析和處理。
假設初始變量的個數為p,每個變量觀測值的個數為n,初始數據矩陣為:X=(X1,X2,…Xp),令∑為協方差矩陣,令協方差矩陣的特征根值為λ1≥λ2≥…≥λp,所以有Var(F1)≥Var(F2)≥…≥Var(Fp)≥0,向量l1,l2,…lp為相應的單位特征向量,則X的第i個主成分可以表示為:

由于協方差矩陣往往是未知的,我們可以用其估計值S(即樣本協方差矩陣)來代替它。另外,由于數據的量綱可能不同,因此在計算前一般要將初始數據標準化來消除量綱的影響,此時:

根據上式可以計算出相關矩陣,從而得到特征值并進行主成分分析。對于含有n個變量的數據,原則上可以提取出主成分的最多個數為n個,但如果將它們全部提取出來則失去了主成分分析簡化數據的意義了。通常的做法是根據貢獻率的大小提取前k個主成分,多數情況下提取出前2-3個主成分已包含了原始數據80%以上的信息,其余的則可以忽略不計。
主成分分析可用來研究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大小。一般來說,當銀行收益之間的相關性增大時,銀行系統性風險隨之增大。因為,銀行收益之間的相關性越大,意味著銀行之間的關聯越緊密。在不利沖擊發生時,銀行系統遭受全面損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直接用銀行收益之間的相關系數來測度系統性風險有其局限性,特別是相關系數只能反映銀行收益兩兩之間的關系,不能反映銀行整體的關聯程度,從而也就不能反映不利沖擊對整個銀行體系收益的全面影響。而主成分分析法,能夠提取出對銀行系統整體收益產生影響的背后因素,即主成分(一個主成分可能代表利率、匯率或其它,也可能是它們其中幾個的組合)。少數幾個主成分能解釋的銀行整體收益變動的比例越大,則意味著銀行之間的關聯越緊密。這樣,當不利沖擊發生時,不利沖擊在銀行之間的傳染會更快更廣泛,少數幾家銀行遭受損失,會引起銀行系統遭受全面損失,因此銀行系統性風險越高。
本文用提取率(the rate of extraction)作為測度商業銀行之間關聯緊密程度(即系統性風險)的指標。我們將提取率定義為:

上式中,ROEt表示t時期的提取率,n表示提取的主成分的個數,N表示商業銀行的數量,σ2Ei表示第i個主成分的方差,σ2Aj表示第j個商業銀行收益率的方差。提取率衡量了銀行收益率變動中能被提取的幾個主成分解釋的比例。
一個高的提取率,意味著少數幾個因素(主成分)可以解釋商業銀行體系大部分收益率的變動,這幾個因素對商業銀行存在普遍影響,商業銀行之間關聯的緊密程度高,金融風險在商業銀行之間的傳染會更快更廣泛,因此系統性風險較高。但需要指出的是,高提取率不一定意味著商業銀行的普遍虧損和銀行危機的爆發;高提取率只意味著,如果有不利沖擊發生,由于商業銀行之間的關聯程度高,風險的擴散會更快更廣泛,一家銀行的虧損或倒閉會導致其他銀行大面積虧損或倒閉。
本文采用我國上市銀行的股票收益率數據來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數據來源于銳思金融研究數據庫。截止2016年,我國上市銀行共有16家。這16家銀行中,2006年以前上市的僅有5家,2006年至2007年上市的有9家,2010年上市的有2家(光大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如果數據從2006年以前開始選取,銀行家數太少,缺乏代表性;如從2010年開始選取,數據期限又太短。故本文數據的選取從2007年9月開始,至2016年6月為止,共選取除光大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以外的14家上市銀行的股票日收益率作為研究對象。
3 實證結果分析
主成分分析,要求觀測值的個數不少于變量的個數。本文選取的銀行數量為14家,進行主成分分析時以20個交易日作為一期。有些交易日,某些銀行日收益率數據為空值,本文研究時剔除這些交易日。不同的時期,收益率有空值的天數不一樣,如2008年剔除空值后剩下224個交易日,而2010年剔除空值后只剩下125個交易日。剔除空值后,本文選取從2007年9月至2016年6月的1 800個有效交易日進行研究,每20個有效交易日為一組進行主成分分析,一共進行90組主成分分析。
本文用Stata12.0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圖1顯示了分別選取一個、兩個、三個主成分時能解釋的銀行股票收益率變動的比例。

圖1 :主成分解釋股票收益率變動的比例
從圖1可以看出,基于本文的數據,選取一個主成分就能解釋大部分銀行股票收益率的變動。在某些時期,一個主成分甚至能解釋90%以上的銀行股票收益率變動,這說明某一因素就能對銀行整體收益產生大的影響,銀行之間的關聯緊密。經計算,在整個樣本研究期間,選取一個、兩個、三個主成分平均能解釋銀行股票收益率變動的比例分別為79.4%、86.5%、90.5%。用主成分分析法時,一般要求選取的主成分能解釋原始變量變動的80%以上,故本文在下面的研究中選取兩個主成分。
圖1中橫坐標相鄰兩個刻度之間均對應剔除空值后的200個交易日,但由于不同時期空值數量不一樣,故相鄰兩個刻度之間對應的自然日期天數并不相等(圖2也是如此)。
圖2顯示了樣本期間的提取率和銀行股票收益率之間的關系。左邊縱軸度量用公式(3)計算的提取率,右邊縱軸度量14家銀行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從圖2可以看出,股票收益率最低的三個時期,分別是2008年底至2009年初、2013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這三個時期,也是提取率高的時期,并且提取率的上升先于股票收益率的下降。在提取率相對較高的2010和2011年,銀行股票的收益率也很高。結合我國當時的經濟背景分析,以上三個時期我國商業銀行股票收益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08年底至2009年初,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商業銀行遭受較大損失,銀行股票收益率大幅度下降。2013年我國宏觀經增長動力不足,經濟部門負債率高企,受此影響,銀行部門利潤受到很大影響。2015年,受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突出、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影響,銀行部門利潤下降,系統性風險顯著加大。

圖2 :提取率與股票收益率之間的關系
以上實證結果表明,提取率是測度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一個很好指標,在銀行股票收益率下降之前,提取率往往會上升。然而,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高收益率不一定意味著銀行系統的全面虧損或危機的爆發,但反過來,即銀行危機爆發之前提取率很高是正確的。
4 研究結論
準確及時地測度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是防范風險在銀行間傳染、保證銀行體系高效穩健運行的前提。本文采用我國14家上市銀行的股票日收益率數據,運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提取率指標,對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取率定義為少數幾個主成分能解釋的銀行股票收益率變動的比例。一個高的提取率意味著銀行之間聯系緊密,少數因素會對銀行體系收益產生普遍影響,銀行系統性風險大。相反,一個低的提取率意味著銀行體系之間的聯系松散,少數因素不會對銀行體系收益產生普遍影響,銀行系統性風險小。
本文研究發現,在樣本期間的2007年9月至2016年6月,14家上市銀行股票收益率最低的三個時期(2008年底至2009年初、2013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對應的提取率都很高,并且提取率的上升先于股票收益率的下降。在提取率高的2010年和2011年,銀行系統股票收益率也高。以上結果表明,高提取率意味著銀行之間聯系緊密、系統性風險高,銀行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增加。但高提取率并不意味著一定會爆發銀行危機,高提取率加上不利沖擊才會導致銀行危機的爆發,也即是,高提取率是銀行危機爆發的一個必要但并非充分條件。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提取率可作為我國監管當局監測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一個很好的指標。本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的另一個優點是使用股票市場數據,時效性強。金融監管當局可以通過對提取率的測度來及時監控銀行系統性風險的變動狀況,在系統性風險上升時可以及時采取相關措施防范銀行危機的爆發。
[1]Bernanke,B.Implementing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47th Annual Conference on Bank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Chicago,2011.
[2]De Bandt,Hartmann,P.Systemic Risk:a Survey[R].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35,2000.
[3]Monica Billio,Mila Getmansky,Andrew W.Lo,Loriana Pelizzon.Econometrica Measures of Connectedness and Systemic Risk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Secto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104):535-559.
[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s[R].April 2009.www.imf.org
[5]Furfine C.Interbank Exposures:Quantifying the Risk of Contagion[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3(35):111-128.
[6]Well S.Financial Interlinkages in the United Kingdom’s Interbank market and the Risk ofContagion.2011-01-05.http://ideas.repec.org/p/boe/ boeewp/230.htm l
[7]Lehar A.Measuring Systemic Risk:a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 and Finance,2003(10):2577-2603.
[8]Billio,M.,Getmansky,M.,Lo,M.,and Pelizzon,L.Econometric Measures of Connectedness and Systemic Risk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Secto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 104(3):535-559.
[9]Brunner Meier,Markus K.and Martin Oehmke.Bubbles,Financial Crises,and Systemic Risk[M].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George M.Constantinides,Milton Harris,and Rene M.Stulz,eds.),2012,(2),North Holland.
[10]Battiston Stefano,Domenico Delli Gatti,Mauro Gallegati,Bruce Greenwald,and Joseph E.Stiglitz.Liaisons Dangereuses:Increasing Connectivity,Risk Sharing,and Systemic Risk[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2(36):1121-1141.
[11]Antonio Cabrales,Piero Gottardi,Fernando Vega-Redondo.Risk-Sharing and Contagion in Networks[R].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715,March 16,2014:1-71.
[12]范小云,王道平,方意.我國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貢獻測度與監管:基于邊際風險貢獻與杠桿率的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1(4):3-20.
[13]劉紅忠,趙玉潔,周冬華.公允價值會計能否放大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J].金融研究,2011(4):82-99.
[14]歐陽紅兵,劉曉東.中國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及系統性風險傳染機制分析:基于復雜網絡的視角[J].中國管理科學,2015(10):30-37.
[15]Girardi Giulio,Tolga Ergün,A.Systemic Risk Measurement:Multivariate GARCH Estimation of CoVaR[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3(37):3169-3180
[16]Hua Chen,J.David Cummins,Krupa S.Viswanathan,Mary A.Weiss.Systemic Risk?and the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Banks and Insurers:An Econometric Analysi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14(3):623-652.
[17]Acemoglu Daron,Ozdaglar Asuman,Tahbaz-Salehi Alireza.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2):564-608.
[18]Lamont Black,Ricardo Correa,Xin Huang,and Hao Zhou.The Systemic Risk of European Banks during the Financial and Sovereign Debt Crise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6(63):107-125.
[19]鄭振龍,王為寧,劉楊樹.平均相關系數與系統性風險:來自中國市場的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4(3):1047-1064.
[20]張蕊,賀曉宇,戚逸康.極端市場條件下我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度量[J].統計研究,2015(09):30-38.
[21]李志輝,李源,李政.中國銀行業系統性風險監測研究:基于SCCA技術的實現與優化[J].金融研究,2016(03):92-106.
[22]張文彤.SPSS統計分析高級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3-233.
責任編輯 許巍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20
F830.22
A
1004-0544(2017)02-0111-06
張遠為(1971-),男,湖北大冶人,經濟學博士,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副教授;嚴飛(1970-),男,湖北武漢人,經濟學博士,湖北經濟學院經濟學系教授。
湖北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研究中心課題基金項目(2016Y003);湖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計劃項目(B201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