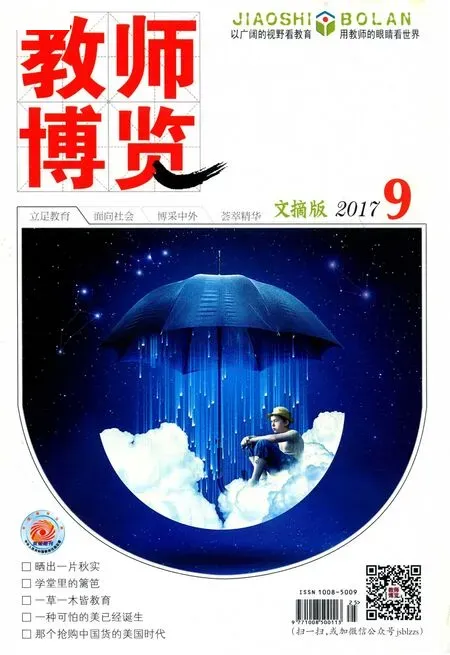高職院校思政課活動德育模式的新探索
徐 嵐,高惠林
(常德職業技術學院,湖南常德 415000)
高職院校思政課活動德育模式的新探索
徐 嵐,高惠林
(常德職業技術學院,湖南常德 415000)
思政課教學是高校德育的主陣地。相比傳統理論灌輸式的思政課教學效果不能令人樂觀,活動德育模式的效果相對較好。既然如此,我們很有必要自覺運用活動德育模式。然而,深入挖掘活動德育模式的理論依據是我們自覺運用該模式的理論先導。不僅如此,在互聯網日漸普及的背景下,我們又不得不積極順勢而為,順應時代要求,努力探索借助網絡工具和平臺,利用好學生喜用手機和愛好上網等特點,“回到”學生熟悉的“生活世界”當中去,讓學生進入“意義學習”的軌道,從而開啟互聯網背景下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學活動德育模式更好效果的新路徑。
互聯網+;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學;活動德育;理論依據
毋庸置疑,德育在成人成才的教育中十分重要,而思政課堂是高校德育的主陣地。在當前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中,當傳統理論灌輸式的思政課教學模式之效果不能令人樂觀的情況下,我們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嘗試,發現“活動德育”是一種能有效提高思政課教學效果的路徑。不過,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擬借助新的網絡工具和平臺,開啟“互聯網+”時代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學中活動德育模式的新探索。
一、活動德育模式的理論依據
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角度來看,實踐是認識得以發生的基礎。正因如此,活動德育模式才在高校思政課教學中有著傳統理論灌輸模式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而德育模式的理論依據將是我們在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學中自覺踐行活動德育模式的理論先導。
1.從人的思維能力的產生和發展的角度來看,不能沒有充分的實踐活動。理解這一點,對于理解活動德育模式的重要作用具有根本的意義。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在其《發生認識論原理》中講“認識的心理發生”時,就深刻揭示了“感知運動”對嬰幼兒正常發育的關鍵作用。如果嬰幼兒沒有充分的實踐活動,他(或她)就不能很好地接觸外在世界,就不會有充分的感知信息使大腦得到發育,當然也就不能很好地建構自己內在的精神世界,那么,就無法達到正常的認識水平,也無法獲得正常的認知能力[1]。其實,我們根據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基本規律不難理解,不僅在人的思維發生的歷史過程中,實踐的作用巨大,也即嬰幼兒的認識發生基于實踐活動,而且當我們每一個人在面對新的事物即認識發生之時,思維的邏輯過程也是以實踐經驗為先在條件的。也就是說,一個毫無相關實踐經驗基礎的人,在嶄新的環境中是會茫然無助的。如我們在一個全新的語言環境中遇到一個陌生的語詞,由于語音完全不能勾連起大腦中的過往實踐經驗記憶,我們的理解過程就不會發生,而當面對完全陌生的文字時情況也是一樣。此時,完全陌生的語音或文字,都只是成了我們“觸目”的對象,而沒有進入意義得以發生的理解之思維過程。正是因為認知發生的相關實踐經驗在理解的思維發生過程中具有優先地位,所以實踐活動的直接經驗、體驗、實驗、閱歷等等便會在理解我們的思政課理論時起著基礎性作用。
2.從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的角度來看,最典型的實踐活動就是勞動,理解了恩格斯所說的“勞動創造了人本身”[2],也就能很好地理解實踐活動對于人意識觀念的建構作用。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有力地論證了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一觀點。恩格斯的論證非常深刻地凸顯了實踐活動對人肌體的發育以及思維能力的發展具有巨大作用,因而是我們活動德育模式之所以有效的內在機制[3]。“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話之深刻不僅在于,勞動滿足了人的物質需要,使人生存了下來,促進了人的肌體的發育,使得人猿相揖別,而且更在于勞動這種實踐方式,建構起了人類社會豐富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人的意識觀念逐漸豐富起來,人的思維能力也日益發達起來。因此可說,沒有勞動,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本身,就不會有人類社會,我們人也不會有現代水平的正確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能力。很顯然,當我們進入社會時,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感知運動”,深入地與社會人打交道,才能夠逐漸形成對社會的正確認識,才能通過實踐活動的方式來推動我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刻理解和自覺踐行,我們的德育工作才算落到實處。
3.從教育傳承的角度來看,沒有實踐活動的支撐,思政課理論的學習就是空洞的、僵死的和無用的虛構。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念,之所以非常強調“做”,核心思想就在于要突出“做”或“實踐活動”對于“學”的重要性。在此方面美國大教育家杜威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放風箏的男孩,必須注視著風箏,注意放風箏的線對于手的不同壓力,他的感官所以是知識的通道,并不是因為外界的事實不知怎么地‘傳到’大腦,而是因為它們被用來做一些有目的的事情。他所看見和接觸到的東西的性質和所做的事情有關,這些性質很快被理解,也就有了意義。”[4]也就是說,人在實踐活動中對鮮活世界的感官知覺,會在主觀目的的牽引下積極主動地與觀念世界聯結起來,從而建構起我們的意義世界。不難理解,“只有在經驗中,任何理論才具有充滿活力和可以證實的意義。一種經驗,一種非常微薄的經驗,能夠產生和包含任何分量的理論(或理智的內容),但是,離開經驗的理論,甚至不能肯定被理解為理論。”[5]我國古人陸游的育兒詩,“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便以樸素的方式道出了其中的真諦。事實上,我們的德育過程,對學生來說,就是指符合社會要求之思想政治道德理論的理解過程,當然也就是其逐漸內化為學生的思維邏輯的過程。如果缺乏應有的實踐經驗基礎,那些理論就是空洞的道德教條,就會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這樣的教育就是身心二元分裂的錯誤教育。對此杜威也曾鄭重地指出:“希臘教育所以取得卓越成就,其主要原因在于希臘教育從來沒有被企圖把身心分割開來的錯誤觀念引入歧途。”[6]由于我們所說的“活動”總是在特定“環境”中的“德育”過程,無疑都是身心一體的德育活動,必然有利于學生“思考”或體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蘊含的道理,并促使其內化。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們盡管理論學說各不相同,但沒有不重視實踐活動的。
二、借助網絡工具與平臺創新活動德育模式的時代要求
眾所周知,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巨大福祉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科學技術儼然就是一臺巨型的“座架”,我們人類身處其中已經無法逃離卻往往并不自知。而這臺科學技術的巨型“座架”已經進入了虛實結合的互聯網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互聯網+”的時代。如果說知識教育還能勉強在傳統灌輸模式中堅持下來的話,那么德育肯定會是最先堅守不住的,因為德育更多地需要“情感”和“意志”的投入而不僅僅是“理智”的運用,也即德育無疑是更需要“知、情、意”相統一的教育,所以德育較之知識教育肯定是要先回到以學生為主體的路徑上來的,而這又不得不要求思政課教師應該設法率先進入到學生的生活世界當中來籌劃。正因如此,好好了解學生的生活世界,積極運用網絡工具與平臺來上好大學生的思政課,是當今科學技術時代發展的趨勢和需要。
首先,我們要懂得“回到”“生活世界”在教育中具有重要意義。著名心理學家奧蘇貝爾在其代表作《教育心理學:一種認知觀》中寫道:“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學所有的內容簡約成一條原理的話,我會說:影響學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學生已知的內容。弄清了這一點后,進行相應的教學。”[7]奧蘇貝爾這里所說的“學生已知的內容”其實就是已經內化到學生精神世界當中去了的知識體系、學生的實踐經驗或親身體驗等。“學生已知的內容”之所以會成為影響學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教育者一旦把握到了“學生已知的內容”,就是“回到”了學生熟悉的“生活世界”當中,學生就會對所教的內容感到熟悉和認同,知識的同化或內化過程就會大大加快,學習效果當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生活慣了的世界感到最為熟悉和適應,而對突然變換的環境感到陌生和不適,原因在于熟悉的“生活世界”中的事物一般已為我們所理解,因而建構起了相應的“意義”。“理解”的過程就是“意義”的建構過程,沒有“理解”的過程就是缺乏“意義”的機械學習過程。正因如此,奧蘇貝爾教育理論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意義學習”。按照奧蘇貝爾的意思,學校里的課堂學習,應主要采用意義接受學習。有意義學習的兩個先決條件是:①學習者必須具有有意義學習的心向,即把新知識與認知結構中原有的適當觀念關聯起來的意向;②學習材料對學習者具有潛在意義,即學習材料可以和學生認知結構中的有關觀念聯系。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就會導致機械學習[8]。由此可見,即使知識教育都應該注重“意義學習”,而德育工作因其對“知、情、意”相統一的要求也就更加應該注重“意義學習”的方式,更加應該努力“回到”學生的“生活世界”當中去,從而才能在知、情、意等方面滋養學生的身心,促使其向善言行的形成。
多年以來,在高校的思政課教學中,高職院校應該是最先從傳統灌輸模式中跳出來尋找出路的。因為我國高等教育多年來一直不是簡單的分類教育,而是分層教育。理論學習水平相對較差的高職院校學生對灌輸式的思政課教學模式更加感到不適。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師多年以來的嘗試,從較早的“Powerpoint”上圖片的運用到其后“Flash”的插入,再到各種相關視頻的節選,較之傳統的黑板、粉筆模式的確顯得色彩斑斕、形式多樣,信息量也大大增加了,德育效果也確實有較大改善。但是,由于信息技術的大步向前發展,新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們在其生活世界中接觸的又是更新的信息傳播媒體,所以這些年思政課教學競相追逐的所謂多媒體教學又開始顯得有些老套了,德育效果也打了折扣。對此進行分析,特別是根據前面已經揭示出了“回到”學生“生活世界”當中去的重要意義,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多是在互聯網環境中長大的,他們對這種環境的融入性極高,尤其是高職院校的學生,相對來說更多地接觸互聯網,甚至于沉迷。因此,對于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講,思政課教師借助網絡工具與平臺,營造好虛實結合的課堂,開拓互聯網背景下新型的活動德育模式,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其中來理解與領會思政課的理論內容,是提高思政課教學效果的不二選擇。
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盡管有不少涉及高校思政課的“活動德育模式”,但是,幾乎都是理所當然地運用該模式,而深入系統地揭示“活動德育模式”理論依據的文章很少見。而事實上,深刻理解“活動德育模式”的理論依據是我們自覺運用各種實踐性、互動性、體驗性手段,幫助學生們及時“回到”自己的“生活世界”當中去的理論先導。只有這樣才能盡快讓學生進入“意義學習”的軌道,從而有效提高高職院校思政課的教學效果。如果沒有對“活動德育模式”理論依據的深刻理解,就很可能只會機械地模仿一些活動方式,而缺乏與時俱進、順勢而為的持續創新能力。正因如此,隨著互聯網的日益普及,大學生們尤其是高職院校的學生們的“生活世界”在不斷改變,我們無疑應該將“活動德育模式”的“活動”擴展為虛擬與現實相結合的“活動”模式,從而將過去有效的“活動德育模式”在新的時代要求下進行到底。
自2015年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以來,高校積極響應,互聯網進教室、進課堂已是大勢所趨。高校已有部分思政課教師自覺運用各大網絡工具和平臺,讓學生們在課堂內外積極參與互動,形成了互聯網時代的新型活動德育模式,大學生們尤其是高職院校的學生上思政課的積極性明顯提高,德育效果也相對較好。
[1][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M].王憲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1-27.
[2]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49.
[3]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49-153.
[4][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6.
[5][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8.
[6][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5.
[7]施良方.學習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1.
[8]施良方.學習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2.
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互聯網+’背景下高職院校活動德育模式研究”(17B13),是湖南省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提升工程資助的研究成果之一。
徐 嵐(1974—),女,湖南常德人,常德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政法思政教育;高惠林(1964—),男,湖南臨澧人,常德職業技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
責任編輯鄧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