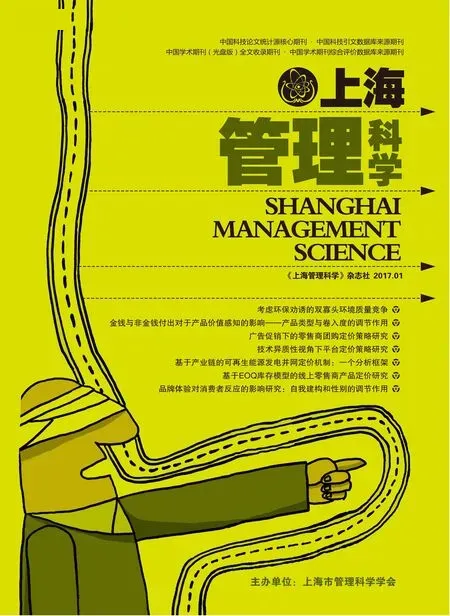基于產(chǎn)業(yè)鏈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定價(jià)機(jī)制:一個(gè)分析框架
孔令丞 梁 玲 李 仲
(1.華東理工大學(xué)商學(xué)院,上海 200237;2.上海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會(huì)展與旅游學(xué)院,上海 201620;3.上海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上海 201620)
基于產(chǎn)業(yè)鏈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定價(jià)機(jī)制:一個(gè)分析框架
孔令丞1梁 玲2李 仲3
(1.華東理工大學(xué)商學(xué)院,上海 200237;2.上海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會(huì)展與旅游學(xué)院,上海 201620;3.上海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上海 201620)
可再生能源商業(yè)化應(yīng)用能夠?qū)崿F(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下的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但商業(yè)前景取決于其與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成本之間的差距,而定價(jià)機(jī)制的合理設(shè)計(jì)對(duì)彌合兩者的成本差距起著決定作用。本文從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產(chǎn)業(yè)鏈的多方主體利益關(guān)系入手,研究供電量波動(dòng)條件下多方主體合意的價(jià)格契約,據(jù)此設(shè)計(jì)符合產(chǎn)業(yè)鏈規(guī)模匹配和技術(shù)銜接的定價(jià)機(jī)制;在此基礎(chǔ)上,綜合可再生能源的發(fā)電類型、地區(qū)稟賦、技術(shù)手段與地區(qū)需求等因素,選擇基于主體利潤最大化的執(zhí)行方式;通過考察定價(jià)機(jī)制在“干中學(xué)”和規(guī)模報(bào)酬下的成本效應(yīng),研究多方主體的跨期價(jià)格契約。為政府制定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約束下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的中長期規(guī)劃提供理論分析框架。
碳強(qiáng)度;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產(chǎn)業(yè)鏈;定價(jià)機(jī)制
1 文獻(xiàn)綜述
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和能源危機(jī)成為全球的熱點(diǎn)問題之后,世界各國都對(duì)此相繼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的價(jià)格機(jī)制和相關(guān)的刺激政策。總結(jié)相關(guān)文獻(xiàn)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1 國外的定價(jià)政策研究
為了彌合可再生能源與傳統(tǒng)能源技術(shù)應(yīng)用成本差距,傳統(tǒng)的定價(jià)導(dǎo)向政策設(shè)計(jì)大多都是通過價(jià)格干預(yù)機(jī)制來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Valentine,2010)。因此,為了保證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逐步滲透到傳統(tǒng)能源發(fā)電市場,共同保障電力市場的供電需求,多數(shù)國家在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初期都規(guī)定了高于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的強(qiáng)制并網(wǎng)電價(jià)(Feed in Tariff);或?qū)稍偕茉窗l(fā)電實(shí)行平價(jià)并網(wǎng),但按所計(jì)量的電量(Net-Metering)發(fā)放綠電證書(Trading Green Certificate),在證書市場通過交易來獲得收益。為了實(shí)現(xiàn)讓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對(duì)碳減排的貢獻(xiàn)能夠滿足國家和地區(qū)的目標(biāo)(Buckman,2010),幾乎每個(gè)國家的相關(guān)部門對(duì)定價(jià)機(jī)制的設(shè)計(jì)都會(huì)考慮到其發(fā)電地可再生能源的稟賦狀況,從而設(shè)計(jì)不同的政策導(dǎo)向、力度并實(shí)現(xiàn)政策間的協(xié)調(diào)匹配。
歐盟規(guī)定,電網(wǎng)必須接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但并網(wǎng)會(huì)對(duì)電網(wǎng)在輸變電、擴(kuò)容、調(diào)峰、儲(chǔ)能等方面提出挑戰(zhàn),因此,很多政策都是基于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產(chǎn)業(yè)鏈下游而設(shè)計(jì)的。在歐洲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市場,Voogt,et.al.(2006)認(rèn)為發(fā)電指令能有效激勵(lì)歐洲可再生能源在電力市場的占比,但產(chǎn)業(yè)鏈下游并網(wǎng)價(jià)格缺乏明確的政策導(dǎo)向,就會(huì)減少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為了保證電網(wǎng)接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必須重塑并網(wǎng)定價(jià)規(guī)則,補(bǔ)貼電網(wǎng)以確保提高并網(wǎng)配置能力(De Joode ,et. al.,2009)。但強(qiáng)制并網(wǎng)電價(jià)(FIT)政策效果表明:基于行業(yè)基準(zhǔn)收益率的補(bǔ)貼具有很高的政策代價(jià)(Lesser & Su,2008),而西班牙實(shí)踐發(fā)電基金管理,成功執(zhí)行歐盟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指令(Del Rio,2005)。而凈電量計(jì)量(NM)由于對(duì)分布式發(fā)電具有較大的邊際效用,由此成為太陽能發(fā)電系統(tǒng)在所有實(shí)時(shí)電價(jià)中最有競爭力的政策(Carley,2009)。就證書(配額)交易(TGC)而言,研究認(rèn)為:長期合約有利于推動(dòng)可再生能源發(fā)電(Paolo,2007)。
中國近年來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市場發(fā)展迅猛,但相關(guān)研究學(xué)者認(rèn)為,中國雖然已成為全球風(fēng)能和太陽能發(fā)電的領(lǐng)軍梯隊(duì),但是由于未有效解決并網(wǎng)和低效運(yùn)行問題,造成“高裝機(jī)容量、低發(fā)電量”并存的現(xiàn)實(shí)怪象(Wang et. al.,2010)。為了解決這個(gè)問題就必須要求提高并網(wǎng)政策框架的完善性Martinot(2010),但是目前國內(nèi)大多研究僅集中在并網(wǎng)定價(jià)機(jī)制及配套政策方面,如何提高并網(wǎng)政策框架的完善性的相關(guān)研究還應(yīng)考慮規(guī)模報(bào)酬的成本效應(yīng),亟待探索電力發(fā)輸送各環(huán)節(jié)協(xié)調(diào)的價(jià)格浮動(dòng)機(jī)制,從而達(dá)到間歇性能源發(fā)電和電網(wǎng)穩(wěn)定輸配要求之間的有效平衡(Munoz,et. al.,2007)。
1.2 國內(nèi)的定價(jià)政策研究
中國還處在第一碳排放量大國的身份和工業(yè)化中期的發(fā)展階段,其碳排放狀況對(duì)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力讓中國已經(jīng)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diǎn)。但是目前國內(nèi)可再生能源定價(jià)研究中,關(guān)于定價(jià)機(jī)制政策的經(jīng)濟(jì)論證可謂非常欠缺,學(xué)者們熱衷于討論歐美等國的政策介紹和對(duì)中國政策制定的啟示(汪文雋,2011);也有進(jìn)行技術(shù)經(jīng)濟(jì)分析來研究可再生能源產(chǎn)業(yè)鏈結(jié)構(gòu)和電力市場規(guī)制(耿亞新,2011),等等。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多是比較分析,研究視角也僅從法理、法規(guī)的角度而沒有對(duì)可再生能源產(chǎn)業(yè)鏈定價(jià)機(jī)制的經(jīng)濟(jì)論證。因此,對(duì)減排目標(biāo)的政策規(guī)劃與效果評(píng)估,就成為中國對(duì)國際社會(huì)減排承諾置信檢驗(yàn)的宣言。
1.3 技術(shù)進(jìn)步、能源替代和動(dòng)態(tài)政策研究
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會(huì)隨著技術(shù)進(jìn)步和規(guī)模變動(dòng)產(chǎn)生成本效應(yīng),相應(yīng)的定價(jià)也應(yīng)隨之調(diào)整,固定并網(wǎng)電價(jià)(FIT)的設(shè)計(jì)和調(diào)整也才有據(jù)可依。Wang(2009)認(rèn)為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技術(shù)雖然正不斷從實(shí)踐到成熟的發(fā)展,但需要進(jìn)行技術(shù)成本經(jīng)濟(jì)性遴選,依據(jù)電力市場的供求關(guān)系變化,決定何時(shí)大規(guī)模應(yīng)用。因?yàn)榧夹g(shù)創(chuàng)新投入具有規(guī)模報(bào)酬遞減的特性,嚴(yán)重制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亟待制定有針對(duì)性的激勵(lì)政策,加速技術(shù)進(jìn)步的成本降低效應(yīng)(Usha,2010)。但如果考慮碳排放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成本,就會(huì)影響能源生產(chǎn)成本,從而帶來能源價(jià)格的相對(duì)漲跌,刺激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同時(shí)還可以平抑規(guī)模報(bào)酬遞減(Michael,et. al,2002)。從目前來看,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huì)對(duì)能源與環(huán)境的干預(yù)結(jié)果,都能提高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對(duì)傳統(tǒng)能源的邊際技術(shù)替代率,但是提高到一定臨界值后,就需要進(jìn)行定價(jià)機(jī)制的合理調(diào)整,保證產(chǎn)業(yè)鏈的創(chuàng)新技術(shù)和運(yùn)營規(guī)模的動(dòng)態(tài)匹配。
但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未來的發(fā)展思路與現(xiàn)實(shí)存在一定差距,其對(duì)傳統(tǒng)能源的替代效率存在一定的替代彈性,這將對(duì)能源需求產(chǎn)生影響。因此研究技術(shù)進(jìn)步和規(guī)模報(bào)酬的綜合成本效應(yīng)以及如何準(zhǔn)確估計(jì)并動(dòng)態(tài)化彌合可再生能源和傳統(tǒng)能源發(fā)電之間的成本差距,將是未來的研究重點(diǎn)。因?yàn)槿绻麑?duì)可再生能源和傳統(tǒng)能源發(fā)電之間的成本差距未能準(zhǔn)確估計(jì),會(huì)導(dǎo)致產(chǎn)業(yè)鏈結(jié)點(diǎn)之間由于價(jià)格補(bǔ)貼與成本之間的異動(dòng),產(chǎn)生新一輪的“瓶頸約束”。
2 分析框架和解決思路
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確定后,可再生能源的發(fā)電量對(duì)目標(biāo)貢獻(xiàn)也由此確定。由于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技術(shù)無法與常規(guī)能源的展開競爭,因此政府會(huì)對(duì)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產(chǎn)業(yè)鏈各個(gè)環(huán)節(jié)進(jìn)行不同程度的鼓勵(lì)。政府的介入對(duì)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上游的材料和設(shè)備供應(yīng)商、中游發(fā)電商、下游電網(wǎng)接入等主體的利益關(guān)系產(chǎn)生影響。上中下游的各企業(yè),均會(huì)依據(jù)自身技術(shù)實(shí)力、商業(yè)化前景、稟賦狀況等條件,按國家政策導(dǎo)向來確定相應(yīng)的產(chǎn)量。形成了由政府主導(dǎo)的產(chǎn)業(yè)鏈節(jié)點(diǎn)行業(yè)間新的利益關(guān)系。
2.1 供電量波動(dòng)下多方合意的價(jià)格機(jī)制設(shè)計(jì)
理論上,政府所規(guī)定的價(jià)格政策激勵(lì)幅度,應(yīng)能夠彌合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成本CRES和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成本CFE之間的差距。即激勵(lì)幅度至少要滿足CRES-CFE。
提高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對(duì)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的貢獻(xiàn),需要其下游電網(wǎng)全額或按配額收購其所發(fā)電力。由于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存在間歇性和反調(diào)峰性的特征,在預(yù)測準(zhǔn)確性制約的現(xiàn)實(shí)下,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電量存在不確定性,電網(wǎng)需要從擴(kuò)容、調(diào)峰和儲(chǔ)能等方面滿足并網(wǎng)需求。這都會(huì)增加成本CG。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多方合意的價(jià)格激勵(lì)效果PE,應(yīng)能彌補(bǔ)電網(wǎng)接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所增加的成本,并使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企業(yè)至少獲得和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企業(yè)同樣的利潤,即PE=CRES-CFE+CG。
盡管政府規(guī)定電網(wǎng)負(fù)責(zé)調(diào)峰,但由于電網(wǎng)的壟斷特征,調(diào)峰成本依然由發(fā)電方承擔(dān)。在水電調(diào)峰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火電調(diào)峰就成為目前唯一的選擇。即當(dāng)超過電網(wǎng)峰值電量時(shí),電網(wǎng)會(huì)要求發(fā)電企業(yè)關(guān)閉一定量的火電機(jī)組,來滿足可再生能源并網(wǎng)。而機(jī)組關(guān)閉和再開動(dòng)所產(chǎn)生的成本就由發(fā)電企業(yè)來承擔(dān)了。
如何讓電網(wǎng)在負(fù)責(zé)調(diào)峰的同時(shí)也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成本?一種辦法是政府將調(diào)峰成本補(bǔ)貼給電網(wǎng),但政府無法調(diào)查電網(wǎng)的真實(shí)的調(diào)峰成本。這可以從不完全契約和產(chǎn)權(quán)理論入手來尋求更有效的解決辦法。
對(duì)電網(wǎng)公司而言,由于其自然壟斷特征和提供公共產(chǎn)品義務(wù),是執(zhí)行政府強(qiáng)制并網(wǎng)政策的責(zé)任主體,與政府之間形成“委托-代理”關(guān)系;同時(shí),國家電網(wǎng)和地方電網(wǎng)之間又屬于“委托-代理”關(guān)系。在接收可再生能源并網(wǎng)上會(huì)表現(xiàn)出“表面合作”,但會(huì)盡量顯示高成本CG,或轉(zhuǎn)嫁成本;信息不對(duì)稱和并網(wǎng)前的預(yù)見成本、締約成本和之后的證實(shí)成本高昂,導(dǎo)致了契約的不完全,事前電網(wǎng)為實(shí)現(xiàn)并網(wǎng)所作的專用性投資無法寫入契約。
這時(shí)對(duì)事前的權(quán)利進(jìn)行機(jī)制設(shè)計(jì)就十分必要。通過資產(chǎn)所有權(quán)或剩余控制權(quán)的合理配置,來實(shí)現(xiàn)對(duì)電網(wǎng)進(jìn)行專用性投資的激勵(lì),從而提高電網(wǎng)接收可再生能源并網(wǎng)的成本控制激勵(lì)和技術(shù)能力。時(shí)間線如圖1所示。

圖1 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機(jī)制的時(shí)間線
就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環(huán)節(jié)而言,該市場結(jié)構(gòu)屬于寡頭市場,發(fā)電企業(yè)之間的競爭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非合作博弈;但為了爭取更優(yōu)惠的政策,在對(duì)待并網(wǎng)定價(jià)政策的態(tài)度上,發(fā)電企業(yè)會(huì)表現(xiàn)出對(duì)政策訴求的一致性而具有合作傾向。因此競合博弈適用這一情形的分析。博弈的第一階段是非合作博弈,即發(fā)電企業(yè)先是獨(dú)立選擇各自的競爭策略。政府可以通過引入類型相關(guān)的多代理人競爭機(jī)制設(shè)計(jì)信息顯示機(jī)制,如特許權(quán)招標(biāo);以及像重復(fù)博弈、信用機(jī)制和獎(jiǎng)懲等這類信息甄別機(jī)制,來消除信息的不對(duì)稱;或者按照不同資源區(qū)制定不同的價(jià)格,企業(yè)的競爭則是對(duì)資源區(qū)的選擇。這兩種情況在我國均實(shí)施過,目前所實(shí)施的是資源區(qū)定價(jià)。第二階段則是發(fā)電企業(yè)通過相互合作以提高并網(wǎng)電價(jià),通過建立可轉(zhuǎn)移效用的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數(shù),并由此建立分配規(guī)則,從中觀察合作的穩(wěn)定性。圖2為政府主導(dǎo)下發(fā)電企業(yè)之間的競合博弈模型框架。
因此,多方合意的定價(jià)機(jī)制取決于政府對(duì)電網(wǎng)的合約激勵(lì),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發(fā)電企業(yè)的競爭機(jī)制和信號(hào)顯示機(jī)制進(jìn)行設(shè)計(jì),由此產(chǎn)生了發(fā)電企業(yè)之間的競合博弈結(jié)果。

圖2 政府主導(dǎo)下的發(fā)電企業(yè)竟合博弈模型框架
2.2 產(chǎn)業(yè)鏈節(jié)點(diǎn)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契約執(zhí)行
定價(jià)機(jī)制確定之后,至少存在兩種可執(zhí)行的方式,在發(fā)電類型、資源稟賦、發(fā)電技術(shù)、電力需求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方合意的價(jià)格契約無論是對(duì)電網(wǎng)還是發(fā)電企業(yè),對(duì)利潤的影響完全相同:
第一,強(qiáng)制并網(wǎng)電價(jià)(Feed in Tariff)。即電網(wǎng)按多方合意的契約價(jià)格接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而高出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的部分,則規(guī)定電網(wǎng)公司從用戶收取可再生能源基金加以彌補(bǔ)。補(bǔ)償在發(fā)電企業(yè)和電網(wǎng)之間進(jìn)行分配。前者通過競價(jià)確定,或按資源分區(qū)定價(jià)執(zhí)行;后者則要確定接收并網(wǎng)所需的擴(kuò)容及調(diào)峰,按圖2的契約機(jī)制加以執(zhí)行。
第二,可交易的綠電證書(Trading Green Certificate)。即發(fā)電企業(yè)按市場價(jià)向電網(wǎng)銷售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電量經(jīng)政府授權(quán)的第三方獨(dú)立機(jī)構(gòu)進(jìn)行核準(zhǔn)后,給企業(yè)發(fā)放相等數(shù)額的可交易綠電證書。高出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成本的部分就可以在證書市場上出售證書得到補(bǔ)償。如圖3所示。
目前,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的強(qiáng)制并網(wǎng)電價(jià)和可交易的綠電證書等措施在很多國家已相對(duì)成熟,但不同發(fā)電類型和技術(shù)條件(內(nèi)部條件)、地區(qū)稟賦差異和地區(qū)需求(外部因素)等,均會(huì)導(dǎo)致同一定價(jià)機(jī)制在執(zhí)行效果上有所不同。產(chǎn)業(yè)鏈節(jié)點(diǎn)的主體按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適用的形式,由此形成了同一定價(jià)機(jī)制下的不同措施選擇。
其次,多方主體合意的契約價(jià)格下,國家電網(wǎng)以該契約接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并將任務(wù)進(jìn)一步分解給下屬地區(qū)電網(wǎng)。發(fā)電企業(yè)的發(fā)電類型、地區(qū)稟賦和技術(shù)條件等,會(huì)對(duì)發(fā)電成本產(chǎn)生影響;而地區(qū)的電力需求、電網(wǎng)規(guī)模和接入條件等,又會(huì)對(duì)電網(wǎng)接收并網(wǎng)的成本產(chǎn)生影響。地方電網(wǎng)執(zhí)行契約的臨界值取決于契約價(jià)格能否彌合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成本與常規(guī)能源發(fā)電成本之間的差額,以及并網(wǎng)成本變動(dòng);否則,會(huì)出現(xiàn)地方電網(wǎng)并網(wǎng)積極性缺失或者契約執(zhí)行成本上升,兩者均會(huì)降低政策效果。

圖3 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的契約形式
這就需要構(gòu)建強(qiáng)制并網(wǎng)(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價(jià)格由經(jīng)政府核準(zhǔn)的基于多方主體合意的契約價(jià)格確定)和證書交易(發(fā)電企業(yè)根據(jù)凈電量計(jì)量所核準(zhǔn)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量獲得證書,通過證書市場交易來補(bǔ)貼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高于當(dāng)?shù)厝济好摿驒C(jī)組發(fā)電成本的部分)的兩部模型,同時(shí)考慮地區(qū)(稟賦)和規(guī)模(技術(shù))的差異,分別測算這兩種執(zhí)行方式對(duì)可再生能源發(fā)電成本的補(bǔ)償效果。從而為不同地區(qū)和不同規(guī)模的發(fā)電企業(yè)、電網(wǎng)公司提供基于其利潤最大化的契約執(zhí)行選擇。如圖4所示。

圖4 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上下游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定價(jià)機(jī)制執(zhí)行選擇
2.3 成本效應(yīng)下的產(chǎn)業(yè)鏈價(jià)格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
發(fā)電企業(yè)和電網(wǎng)公司均會(huì)受“干中學(xué)”、規(guī)模報(bào)酬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交織作用的互動(dòng)所產(chǎn)生成本效應(yīng),會(huì)產(chǎn)生產(chǎn)業(yè)鏈節(jié)點(diǎn)的動(dòng)態(tài)跨期價(jià)格效應(yīng),從而形成可再生能源電力對(duì)常規(guī)電力的邊際技術(shù)替代率在不同時(shí)期的動(dòng)態(tài)變化。
但是,無論是發(fā)電企業(yè)還是電網(wǎng)公司,在多方合意的價(jià)格契約建立之后,均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勵(lì),這需要考慮在動(dòng)態(tài)情形下出現(xiàn)新的跨期收益變動(dòng)時(shí),對(duì)變動(dòng)后的收益進(jìn)行重新分配。因而有必要考慮多期的動(dòng)態(tài)契約優(yōu)化機(jī)制設(shè)計(jì)問題。
首先,政府為了提高電網(wǎng)公司對(duì)可再生能源的并網(wǎng)效率,只要在某個(gè)時(shí)點(diǎn)出現(xiàn)技術(shù)的商業(yè)化應(yīng)用概率足夠高時(shí)(采用可再生能源對(duì)常規(guī)能源替代率的跨期累積結(jié)果),即政府與電網(wǎng)公司之間的契約要在自然狀態(tài)βi (i=1,2,…n)出現(xiàn)時(shí)重新簽約,約定新的專用性投資的剩余分配權(quán)。時(shí)間圖(圖5)是在上一個(gè)時(shí)間圖的基礎(chǔ)上,考慮到動(dòng)態(tài)多期的收益變動(dòng)特征后,所形成的基于可再生能源并網(wǎng)技術(shù)商業(yè)化應(yīng)用的多期動(dòng)態(tài)契約優(yōu)化。

圖5 產(chǎn)業(yè)鏈價(jià)格多期動(dòng)態(tài)契約優(yōu)化時(shí)間圖
之后,重新簽約后同樣需要對(duì)并網(wǎng)電價(jià)進(jìn)行重新規(guī)制。政府通過設(shè)計(jì)多個(gè)代理人機(jī)制促使發(fā)電企業(yè)在電網(wǎng)和政府重新簽約后展開競爭。競爭結(jié)果使發(fā)電企業(yè)之間的成本信息得到披露,這構(gòu)成了跨期動(dòng)態(tài)競合博弈的第一階段,而政府就此設(shè)計(jì)新的并網(wǎng)電價(jià)預(yù)案。發(fā)電企業(yè)在對(duì)政府電價(jià)預(yù)案的認(rèn)領(lǐng)上又會(huì)產(chǎn)生訴求的一致性,表現(xiàn)出合作傾向。其結(jié)果取決于企業(yè)之間合作博弈后增加的總收益在發(fā)電企業(yè)之間分配的結(jié)果,這構(gòu)成了跨期動(dòng)態(tài)競合博弈的第二階段。
綜合應(yīng)用委托代理理論和博弈理論,建立在政府新的并網(wǎng)規(guī)則下,電企的兩階段競合博弈模型,從而構(gòu)建成本效應(yīng)下的產(chǎn)業(yè)鏈價(jià)格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
3 結(jié)語
從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項(xiàng)目的價(jià)格激勵(lì)政策來看,均能看出針對(duì)產(chǎn)業(yè)鏈某一環(huán)節(jié)的定價(jià)機(jī)制設(shè)計(jì),會(huì)由于產(chǎn)業(yè)鏈節(jié)點(diǎn)的規(guī)模不匹配和技術(shù)不銜接,造成產(chǎn)業(yè)鏈上某些環(huán)節(jié)產(chǎn)能過剩和產(chǎn)能不足并存現(xiàn)象。這不但無法實(shí)現(xiàn)政府碳強(qiáng)度的目標(biāo),并且還會(huì)在整個(gè)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造成資源浪費(fèi)。因此,設(shè)計(jì)一種產(chǎn)業(yè)鏈相關(guān)利益者各方主體合意的定價(jià)機(jī)制,才能保障在本土形成可再生能源電力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實(shí)現(xiàn)并網(wǎng)發(fā)電,有利于實(shí)現(xiàn)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定價(jià)機(jī)制設(shè)計(jì)合理性與否,取決于以下設(shè)計(jì)思路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首先,中國政府的碳排放目標(biāo)是基于強(qiáng)度而非總量,這使可再生能源產(chǎn)業(yè)的定價(jià)機(jī)制本身成為政府政策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因此,“定價(jià)機(jī)制”而非“價(jià)格機(jī)制”就是基于可再生能源發(fā)電領(lǐng)域的定價(jià)規(guī)則由政府參與制定的現(xiàn)實(shí),符合中國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的要求。
第二,中國的電力產(chǎn)業(yè)具有獨(dú)特性,即電網(wǎng)企業(yè)屬于國家控股企業(yè),因此兼具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雙重特性。那么如果借鑒委托代理理論來研究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強(qiáng)制并網(wǎng)機(jī)制設(shè)計(jì)以及激勵(lì)電網(wǎng)增加專用性投資的契約機(jī)制,是我國電力產(chǎn)業(yè)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借鑒其他國家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并網(wǎng)的經(jīng)驗(yàn):比如歐盟推行的強(qiáng)制并網(wǎng),美國的凈電量計(jì)量和證書交易制度。這兩種模式都是政府事前設(shè)計(jì)多個(gè)代理人的競爭機(jī)制,通過競爭顯示低成本;但由于所有的發(fā)電企業(yè)在政府電價(jià)政策的訴求上都具有一致性,因此,采用競合博弈模型來解釋并網(wǎng)電價(jià)對(duì)電企的合意性,具有邏輯的正確性和理論的可行性。
[1] Buckman Greg, Diesendorf Mark. 2010. Design Limitations in Australian Renewable Electricity Policies[J]. Energy Policy, Vol. 38(7):3365-3376.
[2] Feng Wang,Haitao Yin,Shoude Li. 2010.China's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J]. Energy Policy, Vol. 38(4):1872-1878.
[3] Lesser Jonathan A.,Xuejuan SU. 2008. Design of an economically efficient feed-in tariff structure fo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J].Energy policy,Vol. 36(3): 981-990.
[4] Valentine Scott Victor. 2010. A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Wind Power Development Policy Barriers in Advanced Economies[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Vol. 14(9):2796-2807.
[5] Carley Sanya. 2009. Distributed Gen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imary Motivators[J].Energy Policy,Vol. 37(5):1648-1659.
[6] De Joode J.,Jansen J. C.,Van Der Welle A. J.,2009. Increasing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And Distribute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The Need For Different Network Regulation[J].Energy Policy,Vol. 37(8):2907-2915.
[7] Del Rio Pablo. 2005. A European-Wide Harmonised 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 Scheme for Renewable Electricity: Is It Really So Beneficial? [J]. Energy Policy,Vol. 33(10):1239-1250.
[8] Martinot Eric. 2010. Renewable power for China: Past,present,and future[J].Frontiers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in China, Vol. 4(3): 287-294.
[9] Mihajlov Andjelka. 2010.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n SE Europe: SE European Energy Community Treaty[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Vol.14(2): 872-875.
[10] 孔令丞. 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推進(jìn)模式與效果評(píng)價(jià)[M].上海: 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2.4.
[11] 耿亞新. 太陽能光伏產(chǎn)業(yè)鏈垂直一體化構(gòu)建研究[D].西北大學(xué), 2011.
[12] 后勇,徐福緣,程緯. 基于可再生能源替代的經(jīng)濟(jì)持續(xù)發(fā)展模型[J].系統(tǒng)工程理論與實(shí)踐,2008(9):67-72.
Study on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Renewable Energy Power under the Goal
of the Carbon Intensity
Kong Lingcheng Liang Ling Li Zhong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can fulfill the goal of the carbon intensity under the economic growth, its prospect depends on the gap of the cost of the conventional energy, and the gap can be narrowed by designing rationally the pric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tries to (1) study the desirable price contract of the multi-subjec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fluctuation of power supply and according to this, design the pricing mechanism for the scales and the technologies matching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under the bound of the goal of carbon intensity and from the oblig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multi-interests subjects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power industrial chain. (2)To choose the operating ways which maximize the profit of the subjects in its industrial chain by synthesizing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power type, region endowment, technical measure and the demand. (3) To study on the intertemporal dynamic price contract between multisubjects therefore establish the price coupling mechanism of industries in the chain based on the cost effectiveness so as to give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adjustment the pricing mechanism dynamically. All the studies can provide the theory bases and the practice guides fo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plan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power for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bound of the goal of carbon intensity.
Carbon Intensity; Renewable Energy Power; Industrial Chain; Pricing Mechanism
F014.31
A
1005-9679(2017)01-0020-05
國家自科基金面上項(xiàng)目“碳強(qiáng)度目標(biāo)下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產(chǎn)業(yè)鏈的定價(jià)機(jī)制研究”(批準(zhǔn)號(hào):71273091);教育部人文社科規(guī)劃項(xiàng)目“基于產(chǎn)業(yè)鏈的太陽能發(fā)電政策研究”(批準(zhǔn)號(hào):11YJA790068)。
孔令丞,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博士和博士后,華東理工大學(xué)商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系副系主任,能源經(jīng)濟(jì)與環(huán)境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方向: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資源與能源經(jīng)濟(jì);梁玲,上海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會(huì)展與旅游學(xué)院管理學(xué)博士, 研究方向:運(yùn)營與供應(yīng)鏈;李仲,上海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管理學(xué)博士,研究方向:物流與供應(yīng)鏈、能源經(jīng)濟(jì)管理。
- 上海管理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基于工商管理教育實(shí)踐的教育供給側(cè)改革的內(nèi)在邏輯
- 制度環(huán)境、股權(quán)激勵(lì)與送轉(zhuǎn)股
- 關(guān)于機(jī)構(gòu)對(duì)A股股票評(píng)級(jí)變動(dòng)后市場相應(yīng)表現(xiàn)
- 創(chuàng)業(yè)投資A股上市退出回報(bào)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以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為投資對(duì)象的母基金的視角 - 打破節(jié)能家電中能效標(biāo)簽在中國的窘境
——標(biāo)注社會(huì)規(guī)范信息有效性探究 - 基于Cox比例風(fēng)險(xiǎn)模型的電梯保養(yǎng)決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