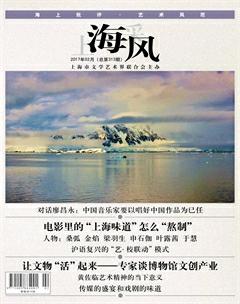由“上海閑話”熬制的“上海味道”
本期“文化熱點”由兩篇文章組成,聚焦“上海閑話”與“上海味道”。這源于某種程度的“上海話熱”:日前播映的滬語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在滬語背景觀眾群中口碑爆棚,緊接其后的《上海王》也是充斥著大量滬語,滿屏濃郁的上海味道。事有湊巧,近日在文藝會堂召開的滬語文化教育聯(lián)盟校長論壇的主題也是:“學(xué)語言,從愛曲藝開始”——熱議的是,如何通過方言為主的曲藝形式,從娃娃抓起,改變“上海小囡不會說上海話”的尷尬現(xiàn)狀。
這兩件事既無關(guān)聯(lián)又有關(guān)聯(lián)。無關(guān),一個說的是電影,一個說的是教育。有關(guān),兩個都關(guān)礙上海話。我們不妨設(shè)想,在“上海話式微”環(huán)境下長大的一代,他們?nèi)绾文芨惺苡捌醒笠绲摹吧虾N兜馈保扛卣搫?chuàng)作出上海意韻十足的文藝作品!這倒不是說,“上海題材”是上海人的專利,事實上“上海”早已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熱門題材,誰都可以拿它說事,取材于它。但總的說來,在眾多上海題材的影視中,上海往往只淪為背景而已,沒有那種扎到根子里的東西。倘若主創(chuàng)者有濃郁的上海情結(jié)和骨子里的本土文化,熬制出來的影視佳肴自然會有很大不同。
“上海味道”的組成,羅列起來方方面面,但“上海閑話”無疑是其核心部分。地域文化是建立在方言之上的,往往標志性的方言一起,立馬營造出一方水土和人情。當年“大力推廣普通話”本身是不錯的,可是從現(xiàn)在的視角看,倘若這種推廣一旦將方言置于敵對的位置,后遺癥就出現(xiàn)了。當本土的“上海小囡”不會用上海話表情達意時,在硬腔腔的語調(diào)背后,失落的不僅僅是一地方言,還有它所承載的一方文化生態(tài)。方言中隱藏和孕育著豐富的文化密碼,比如當人們聽到帶著蘇白的吳儂軟語時,其中的人情世故、民俗意蘊以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言外之意,只有在共同方言背景中浸淫的人們,才能曲盡其妙。
“上海話電影”的出現(xiàn)和崛起,讓人興奮。其實方言入電影早已司空見慣,東北話陜西話山西話河南話四川話山東話早都在影視中頻頻出現(xiàn),觀眾之所以沒有違和的感覺,乃因北方語系與普通話接近,聽著不會太累。而像粵語吳語等南方語系一旦進入影視,其局限性就會顯露。但是局限性恰恰又是獨特性,如果能控制局限張揚獨特,就有可能石破天驚,出現(xiàn)非同一般的特色作品。小說《繁花》的語言實踐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其找到了一條既展示方言之美、又與普通話對接融通的渠道,這種探索特別有價值。
《羅曼蒂克消亡史》和《上海王》的出現(xiàn),可謂近期中國電影的一個收獲,留下許多值得說道的話題。但總體來說,還是“老上海”被導(dǎo)演眷顧得多,出鏡率也比較高,而表現(xiàn)“新上海”的影視似乎較為鮮見,即便有,也不接地氣,故事搬到任何城市都行。正如著名主持人、如今踏入影壇的曹可凡所言,“像黃蜀芹導(dǎo)演的《孽債》這樣的作品,才真的反映了上海人的精神風(fēng)貌,深入刻畫了上海人的靈魂。當代生活是那么豐富,作為創(chuàng)作者對生活不能視而不見,不能沒有藝術(shù)感受力”。
上海這座城市,有老上海的想象,也有新上海的現(xiàn)實,有太多的歷史皺褶可以展開。藝術(shù)家們?nèi)绾伪M心竭力“熬制”出一桌桌散發(fā)著濃濃“上海味道”的影視大餐,既是觀眾的期待,也是時代的需求。在此也特別寄望于青年一代,盡管你們的上海話不夠純正,但是只要擁有一顆熱愛上海的心,懷有濃郁的上海情結(jié),一定能夠找到獨特的表現(xiàn)方式,“上海中年導(dǎo)演胡雪樺”的呈現(xiàn)方式和“非上海青年導(dǎo)演程耳”的呈現(xiàn)方式迥然不同,然而人們一樣沉醉在“上海閑話”和“上海味道”中,其間自有玩味之處。
同時希望,“從娃娃抓起”的上海話普及嘗試,能夠化為未來上海題材文藝創(chuàng)作的潛在力量。講上海話的人多了,上海故事才會深入人心。
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