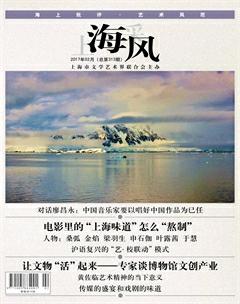晁玉奎:金戈鐵馬入筆來
劉莉娜



初見晁玉奎,他正在上海圖書館辦個人書法展——不是文化館,不是美術館,正是圖書館。但“懂的人懂的”,在“上圖”辦展,那是要有底氣的。我于午間到達,晁先生正好不在,便信步展廳到處看看——雖然自己于書法是個外行,但“外行看熱鬧”也是有感受的。中午時分展廳空曠,但一眼望去只覺得那些大大小小、疏密有致的漢字充盈了整個空間,竟使之半點也不顯蕭索,尤其是幾幅大字,四字一幅便占了一面展墻,卻也“撐得住”這一整面墻,真是氣勢萬千。而晁玉奎本人也“人如其字”,當他大步流星從門外走過來,特別用力地與我握手時,我立刻想起他“軍旅書法家”的特殊背景來,果然是經歷過金戈鐵馬的人,就算是如今舞文弄墨,也自帶一派闊達雄健呢。
說起來,軍旅生涯不止是晁玉奎的人生底色,也是他書法之路的開端。“我小時候雖然也學過書法,文革期間也用毛筆抄寫大字報,但這些后來就丟掉了。直到1987年,我們部隊駐在徐州,這里既是古戰場,也是漢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和集萃地,現在仍然是全國的書法名城,涌現出了張伯英、尉天池等一大批有名的書法家。我于此耳濡目染,每次走在大街上,看到好的匾額、門店招牌,總要駐足觀看,手摹心追。”這顆起源于“古戰場”的書法心,讓年輕的軍人晁玉奎忍不住買來筆墨,自己臨摹練習,因為部隊里平時的訓練紀律嚴明,無法想練就練,晁玉奎就利用每周休息的自由時間閉門寫字——都是正當青春、遠離家人的年輕人,其他戰友們都利用這少有的自由組織同鄉聚會,結伴逛街購物,晁玉奎卻是耐得住寂寞的,也漸漸“寫得像了點樣”。雖然在自己的書法之路上,年輕時候的這段熱血經歷甚至算不得“入門”,最多算“熱身”,但晁玉奎說,這段經歷卻對自己影響深遠,“因為它讓我意識到,求索之路上,一切的‘忙和‘不得已都不是借口,只要善于利用業余時間,一樣可以成才。”這讓晁玉奎在之后的軍旅生涯中,以及轉業后的政府工作中,事業再忙也沒有給自己找借口,工作再累也沒有放棄過書法,每天總是想方設法要么晚睡要么早起,擠出“業余時間”練習,這樣才能取得今日的成就。
當然,當年的辛勤也沒有白費。因為晁玉奎的字常常出現在食堂門口的黑板報上,一手好字引起戰友們圍觀,于是他對書法的癡迷也漸漸在軍中傳開了。上級知曉后,在一次人員調動中特意挑選了他去集團軍當了黨委秘書——隨從軍長郭錫章,而這位郭軍長正是個不折不扣的書法愛好者。因為軍長愛好書法,便常常讓秘書晁玉奎去給他買字帖,還積極組織機關學習,請徐州的書法家來部隊授課。這一切對于晁玉奎來說正是如魚得水。“因為軍長參加這類活動的積極性很高,我于是也常常隨他去聽書法課,就在這一次次的名家授課中,我對書法的本質有了深層次的認識,知道了用筆技法和章法要求。”晁玉奎回憶說,自己第一次對“書法是門藝術”醍醐灌頂正是源于一位受軍長之邀來部隊授課的書法家,在此之前和很多人一樣,他覺得書法就是把字寫得漂亮的能力。“我一直記得那位老師的開蒙第一句,他說,書法是什么?書法,是以漢字為對象的線條藝術。”從這時候起,晁玉奎開始真正與書法結緣,把它當作一門藝術來欣賞和追求。
1990年4月下旬,對晁玉奎書法之路影響深遠的軍長郭錫章被中央軍委任為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組織上委派晁玉奎同去,作為副司令員的專職秘書。彼時晁玉奎已經成家立業,在徐州已經扎根,但一想到南京是六朝古都,書法底蘊更加深厚,書法名家更多,晁玉奎還是選擇了同行。而這一次的選擇已然沒有辜負他的書法夢,當時江蘇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是武中奇,作為省會的南京市到處都是他題寫的匾額,這讓愛書法的晁玉奎簡直流連忘返,常常駐足不前。“有一天我們路過新街口,看到武中奇題寫的‘南京市新街口百貨商場,我說武中奇的字寫得就是好,剛勁雄強,推土機都推不倒。首長郭錫章說,他是一個軍旅書法家,在部隊當過團長,最近有空我們不妨去拜訪他一下。”這是個多么好的學習機會啊,晁玉奎立刻記下這件事,隨后就與武老先生家聯系,然而不巧的是當時他去山東了,這件事就拖了下來。到了那一年的年底,春節放假,郭副司令到底也是書法迷,心里依然記掛著這件事,又說:“我們去給武老拜個年,看他哪天方便。”晁玉奎趕忙再次聯系了武老,約在初一上午登門拜訪。這一次的見面讓晁玉奎很有收獲,“初一早飯后我們來到武老家,他滿面春風,沏茶讓座,在客廳里接待我們,談論的話題都是書法”。隨行的晁玉奎也借機問了個挺實際問題——對于初學書法的人來說,到底是臨碑好還是臨帖好?武老絲毫沒有因為這個問題太“初級”而略過,他說,中國書法是一門獨特的文化藝術,對初學者來說,臨碑臨帖都可以,但要側重一個方面,因為碑和帖在用筆技巧上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具備一定的功底,才可向碑帖兼融的目標邁進。一個多小時,武老談興很濃,晁玉奎也聽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淺。
除了名師的教益,晁玉奎說,其實自己的書法之路上還有一個需要感謝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原來,當晁玉奎從南京軍區轉業后,被調任上海,先后在精神文明辦和宣傳部任職,生活環境的變化加上新工作的忙碌,有一段時間,晁玉奎每天臨帖都感到不滿意,總是不得章法,急躁之下就有點氣餒,有點消極。這時候太太這個完全是書法門外漢的人卻對他說:“你不如每天都留下一張練習作品放在那里,不管滿意不滿意,一個月后再放到一起看一看,也許會有不同感受呢。”晁玉奎接受了太太的建議,一個月之后拿出厚厚一疊“每日一練”一看,第一張和最后一張相比,進步相當明顯。這個事實讓他一下子找回了自信,并且明白了何為“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從此在書法之路上走得更加沉靜踏實。
就這樣,到上海工作后,晁玉奎一方面投入新的工作,一方面繼續潛心習字,同時因地制宜對海派書畫潛心研習,其長篇論文《海派書法崛起的原因探析》見諸報端后,受到業內外廣泛好評。一個假日,幾位朋友喝茶時,提起當下海派書法怎么振興的話題,“新上海人”晁玉奎馬上談了三個方面的想法:一是繼承傳統既不“脫崗離譜”,又不能受條規的束縛。二要尋古求論,增強理論研討氛圍,發揮學術引導作用。三要倡導在技法和審美意趣上、在形式和內容上緊跟時代,適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要求,唯有這樣才能形成海派書法多元創新的格局。這份對海派書法的洞察和關切讓座上朋友都深以為然。
2012年10月,上海首次成立機關書法家協會,當時的上海市書法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晁玉奎當選為市機關書法家協會主席。對此,晁玉奎表示,書法是中國獨特的文化藝術,這一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創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能認為這只是書法家的事,機關干部要勇于擔當起這個歷史使命。“上海首次成立機關書法家協會,這對推進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對推動書法藝術大普及、大發展、大繁榮,對濃厚機關學習書法的氛圍,培養書法新人都具有積極意義。”在晁玉奎看來,中國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代表,在實施文化強國戰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要真正在上海掀起“書法熱”,必須進一步營造“機關帶頭,全民書法,翰墨天下”的濃厚氛圍。只有把群眾性書法的基礎做大做強,書法藝術的寶塔尖才會越高越穩固。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同年11月,晁玉奎應邀赴美國國會大廈、聯合國總部、美國丹佛大學、韋伯大學舉辦書法個展,期間他積極向世界展示和推廣書法這門古老而美麗的中國藝術,不僅在美國的大學和民間積極互動,更“驚動”了聯合國,為此聯合國總部還專門發行了一套印有晁玉奎書法作品的國際郵票。對此,上博館長陳燮君一言以蔽之:“晁玉奎對書法藝術的愛好和追求是發自內心的,幾十年來矢志不渝。”
在陳燮君眼里,晁玉奎獨具風格的書法藝術,來自于他對中國書法藝術傳統的深刻認識和理解。“他那以情掣筆、隨性揮灑、無障無礙、一往無前的精神狀態,他那勢如揮戈舞劍、八面出鋒、縱橫不羈、碑帖結合的用筆及渾勁酣暢、激蕩多變的線條運動,他那因勢利導、隨機應變的用筆及布白,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對此贊譽,晁玉奎深感知心,站在上圖簡約卻不失博雅的展廳里,這位從軍旅中一路走來的墨客心里平靜而滿足:“我辦這個展覽就是想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倒逼自己在書法創作中不能松懈,二是收獲良師益友,如此,兩樣都實現了。”
記者:能不能具體說說軍旅生涯對你書法創作的影響?并不是啟蒙意義上的那種。
晁玉奎:確實不少朋友問我,你在部隊三十多年,對你創作有影響嗎?我感到這方面的影響確實不小。人們常說,字如其人,功夫在詩外。由此可以看出,藝術家的經歷與創作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比如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他在出師北伐、壯志未酬的悲憤心情下寫的千古絕唱《滿江紅》《還我河山》如龍蛇奔走、有吞吐天地的氣勢,從字里行間可以感受到岳飛一身的浩然正氣和博大胸懷,至今令人振奮。再比如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當年也是領兵二十萬橫掃燕趙的將領,他在《祭侄稿》追敘侄子季明,在安祿山叛亂時挺身而出、堅決抵抗、被叛匪殺害時,心情極度悲傷,情緒難以平靜,隨情而書,不計工拙、時疾時徐、剎筆處戛然而止,連綿處似大河直下、一瀉千里、神采飛動,字里行間充滿英風烈氣。
我的書法當然不能與這些豐碑式的人物相提并論。但也深刻體會到,部隊嚴格緊張的生活,頑強拼搏、一往無前的精神,勤學苦練、一絲不茍的要求,雷厲風行的作風、積極向上的氛圍,對我都內化于心、外化于形,融入了我的生活,也融入了我的生命,鑄就了我的軍人氣質,在書法創作過程中,也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到書寫上,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記者:來到上海之后你就一直在機關任職,更被選為上海市機關書法家協會主席,你認為書法在當下知識分子或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中應占據怎樣的位置?
晁玉奎:中國書法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歷代帝王對書法的重視、推崇也是書法人才輩出的一大因素。典型的如南朝的蕭衍、唐代李世民、五代李煜、南宋趙構等,他們都是“皇帝”兼書法家于一身。上層官僚對書法的熱衷,形成了官府內“沒有書法本領,恐怕難以立足”的局面。嚴格地說,在古代,并沒有專業的書法家。歷代長于書法者,很多都是為官者或知識分子、機關干部,無非是將書法“玩”得更加得心應手。而如今歐風美雨、西學東漸,鉛筆、鋼筆、圓珠筆等各種硬筆代替了毛筆,毛筆書法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我認為,現在雖是信息化時代,可是作為機關人員,不僅肩負著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使命,而且通過研習書法可以進一步提升和完善人文知識和文化素養。如果機關人員愛好書法這門藝術,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記者:不止機關,其實書法在民間也一直廣有根基,近年的書法考級一直很熱,考生從8歲到80歲都有。你對當今社會的書法熱有何看法?
晁玉奎:的確,這幾年社會上出現了書法熱,這是一個好現象,是太平盛世的生活寫照。書法藝術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和魅力,是中國唯一沒有受到西方文化沖擊和影響的藝術。書法作為傳統的藝術,在新的歷史時期仍然具有審美、教育、認知、娛樂的功能。林語堂說:“在書法上,也許只有在書法上,我們才能看到中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我們應該乘勢而為,引導人們加深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與理解,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文化強國的進程中,繼承和創新中國的書法藝術,進一步提升國民素質。
記者:你說當年在南京與武中奇先生的一次面對面,讓你作為初學者收獲甚多。如今你作為上海書協的副主席,有沒有什么建議給我們的初學者們呢?
晁玉奎:務實的說,在我看來,學習書法最重要的就是“臨、摹、創”三個字。一是摹,是古人傳移模寫之法,或用雙鉤,或用影映、蒙寫,宗旨無非是不走樣不變形,摹的結果是外形準確、結構合理、筆畫到位。二是臨,有實臨、有意臨。實臨是學習書法的初級階段,如果一生以實臨為業,則必然成為“書奴”。意臨的意,又可分為物意、筆意、我意。書法中的字形字態為物意,輕重疾徐為筆意,合心適情為我意。意臨是“十分學七要拋三”,歷代書家都把“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作為臨摹法寶,把“神采為尚,形質次之”作為終極追求。三是創,由臨而入,憑古法而傳承,由臨而創,以傳統而出新。一般評價書法,要求師承有序,技法純熟,氣息高古,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