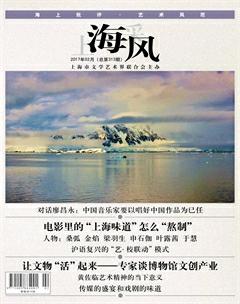傳媒的盛宴和戲劇的味道
丁羅男
壹
說當今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傳媒盛宴的時代,是毫不夸張的形容。今天我們確實處在各色各樣的媒體的包圍之中,除了傳統的報刊、廣播、電影、電視以外,數字化的網絡新媒介更以無孔不入的神力侵蝕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電腦、手機、視頻、微搏、微信……每天傳播著數以億萬計的“有聲有色”的信息,幾乎包攬了我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各個領域里的資訊、交流任務,甚至“越俎代庖”地充當起文學、戲劇、影視等文藝作品的超級傳播者,以至于這些傳統的文化娛樂產品在烹制出爐時也不得不考慮一下,是否適應數字媒體的特點,合乎“網民”的口味?當下的劇場演出顯然深受影響,越來越多的新媒體——從燈光、視頻,到電子音樂,紛紛登上舞臺,掀起一場場“聲色之娛”的狂歡。
其實,戲劇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在人類歷史上也曾扮演過社會生活中重要的媒體角色,比如古代希臘時期的戲劇競賽,成千上萬的民眾涌向偌大的競技場,只為欣賞、評判詩人的智慧才情和藝術家的表演功力;比如文藝復興至浪漫主義時期的歐洲劇場,從莎士比亞、莫里哀,到哥爾多尼、歌德、雨果,幾乎所有的文藝巨擘都曾以戲劇的形式與時代和人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從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的一段話里,我們不難體會到劇場在那個時代所具有的非同小可的影響力:
啊!戲劇詩人喲!你們所要爭取的真正的喝彩不是一句漂亮的詩句以后陡然發出的掌聲,而是長時間靜默的壓抑以后發自內心的一聲深沉的嘆息……那就是使全國人民因嚴肅地考慮問題而坐臥不安,那時人們的思想將激動起來,躊躇不決,搖擺不定,茫然不知所措;你的觀眾將和地震區的居民一樣,看到房屋的墻壁在搖晃,覺得土地在他們的腳下陷裂。(《論戲劇詩》)
直至20世紀初,“機械復制的藝術”——電影興起后,特別是廣播、電視以更大的覆蓋面積和更便捷的傳播方式登上媒體之首的地位后,戲劇才像“小作坊”遇到“大工業”,逐步退居到傳媒的次要位置上。然而,戲劇并沒有因此而消亡。在20世紀30年代有聲電影出現并發展迅猛之際,法國戲劇家馬賽爾·帕涅爾曾悲嘆,戲劇終將被電影所代替,但是歷史并沒有應驗這一預言。直至今天的數字化網絡時代,情況依然如此,戲劇——確切地說是劇場——仍在鋪天蓋地的文化傳播場域中占據著一席之地。
這至少說明了一點:戲劇藝術擁有其他形式無法代替的特質,在傳媒的盛宴之中,戲劇是一道味道獨特的“菜”。已故臺灣戲劇家黃美序曾經寫過一本書:《戲劇的味/道》,其中既有對戲劇藝術神韻的品味,又有對戲劇創作規律(道)的感悟。這是他作為一位資深的戲劇人,集畢生的編、導、戲劇教育經驗而寫成的現代劇場“啟示錄”,有許多關于劇場本質的論述,值得我們深加思索與體味。
貳
西方戲劇家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感受到新媒體的發展可能造成劇場藝術的生存危機。于是,許多人開始尋找和探索戲劇不可替代的特質,甚至追本溯源至戲劇的發生:“戲劇的本質機能,可以在作為未開化民族共鳴巫術的原始戲劇中看到。這是一種想要憑借恍惚狀態來克服生活不安的社會性的全體體驗……在這種原始的體驗之中,演員、作者和觀眾三要素渾然一體。”(尤里烏斯·巴普《戲劇社會學》);而格洛托夫斯基的表述則是影響最大的:“沒有演員與觀眾中間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關系,戲劇是不能存在的。”(《邁向質樸戲劇》)。這就是說,戲劇作為媒體的特殊傳播方式是在劇場里,演出與觀眾面對面的“活生生”的交流和對話。這種現場感、鮮活感和不可復制性是現代化的影視、網絡所沒有也不可能做到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戲劇在眾多傳媒的盛宴中,不是那種批量復制、真空包裝的罐頭、熟食,而是一道新鮮蔬菜。其信息量、傳播面和便捷度也許都趕不上各種新媒體,但劇場的存在無疑適應了人類天性的需求——人與人之間的會面、當場交流,以及滿足一種“集體體驗”(無論是儀式性還是游戲性的)的本能欲望。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當今社會緊張化、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下,在信息交流的距離日益縮短、娛樂方式如此多樣和方便的情況下,有許多人仍然會趕到劇場里去看戲,去享受一場虛擬化的表演。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劇場的表現功能確實大大增強了。各種新媒體的加入,使得戲劇表演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視聽效果。但是,多媒體的運用也需要恰到好處,即有利于戲劇本體功能的發揮,而不是取而代之。
以視頻投影為例。早年布萊希特、梅耶荷德等就曾在舞臺演出中放映過電影片斷,作為一種“間離效果”,或信息的補充,起到了配合總體演出的作用。三十年前,斯沃博達創造了“TV戲劇”的新形式,他在舞臺演出的同時,用同步攝像的方法,把不同角度的演員影像(如特寫、背影)及舞臺外(如后臺化妝間、走廊、劇場外大街)的“戲”直接投影到舞臺屏幕上,這不僅擴大了演出的空間,而且加深了觀眾對人物和劇情的理解。
在近些年的劇場里,我們也看到過不少成功應用視頻投影的演出,它們在拓展空間、烘托氣氛與補充敘事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探索。但也有一些演出并不能令人滿意:導演將預先制作好的大段視頻錄像在屏幕上“閃回”,讓觀眾(包括演員)一起觀看;或者用虛擬光影技術把整個舞臺弄成一個巨大的類似電影的影像空間,使演員顯得非常渺小,表演反而成了影像的陪襯。這樣的演出還能剩下多少戲劇本身的魅力呢?如果觀眾的目光不是聚焦于演員,不是體味“活生生”的真人表演,那么他們何必來到劇場?在電影院、在家里的電腦屏幕前,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眩人耳目的影像世界嗎?
以為在新媒體時代,劇場演出就應當讓聲光電化當主角,這實在是一種誤解。用毫無節制的投影、激光、音響制造所謂的“視聽盛宴”,結果只能把戲劇的本體特質扼殺了。這使我想起了曹禺先生晚年說過的一段話:
有人說,現在電影、電視把話劇壓倒了,我不相信。我認為舞臺藝術是不可能被代替的。舞臺上的戲與觀眾有直接的交流,電影、電視不是真人的藝術,它與觀眾還是機器與人的關系。雖然我們看的時候也哭,也笑,但大家總覺得隔一層,終究以為這不是和我們一樣的有血有肉的人。因此電影、電視是代替不了戲劇的。今后是否使舞臺和觀眾親近些,更親近些,使我們聽見他們的氣息,看見舞臺演員的眉目、神情,感觸到他們內心的顫抖。一個有血肉、有靈魂的人在我們身邊經受痛苦、悲哀和歡樂……(《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
藝術最終關注與表現的是人而不是物,戲劇尤其如此,這是它得天獨厚的長處。戲劇應該借助科技的進步不斷提升自己的表現力,但是與電影電視等媒體相比,戲劇對技術的依賴程度其實要低很多。在如今各種新媒體競相爭妍的時代,戲劇也不必自慚形穢,因為戲劇有別的媒體難以企及的“味道”,我們的導演也不必把注意力全放在用多媒體吸引觀眾的眼球上,倒是更應該思考如何發揮演員的表演特長,包括語言的、肢體的和一切有關人的精神領域的表現力。
叁
關于戲劇的本體,還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中,當代戲劇是否需要“去中心”?有人宣稱“后現代劇場”不再是傳統劇場的綜合藝術,因為中心已經“解構”,就無所謂綜合,只剩下相互沒有關聯、沒有意義可尋的“碎片”和“拼貼”。但劇作家的地位下降之后,導演者卻上升到“中心”——至少是個拼貼者;他們還主張后現代戲劇是反敘事結構、反文學語言的,因此傳統的(故事)表演藝術,走向了展示藝術、行為藝術;然而悖論在于,后現代主義是和消費主義的大眾文化結盟的,而作為商業戲劇又少不了“故事”與“明星”,那么,當代劇場到底有沒有中心?還要不要敘事?事實是,近年來中國戲劇舞臺上出現了許多“中心”——導演、明星、多媒體、音樂舞蹈等等,也出現了不倫不類、一片混亂的“敘事”。
根據我的理解,“去中心”是為了破除一元化、模式化的格局,帶來的是文化的多元并存。以戲劇而言,傳統的、經典的、商業的、實驗的,都應有一席之地,而且表現形式上也出現越來越多的融合與滲透。但一個具體戲劇作品的創作與演出,無論外顯的還是內在的,恐怕還是需要有中心和意義的。
戲劇要取消敘事,這一說法也是可疑的。按照后現代劇場理論的解釋,像貝克特《等待戈多》這樣的文本也是敘事的,那么后現代戲劇的反敘事會走得多遠呢?要知道,即使展示藝術、行為藝術,從敘事學角度來看也是在敘事!看來他們講的反敘事還是指摒棄有邏輯的故事情節,但這在現代主義戲劇中不是已經做到了么?不同的是,現代主義的反敘事是文學家所為,而后現代的反敘事則出于導演者的主張。
近些年來,一股貶斥文學、輕視劇本的思潮在國內劇界頗為流行。有些人打著“后現代劇場”的旗號,把文學驅趕出劇場,有些導演完全不把劇本創作放在眼里,隨意地將原作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我覺得應當引起警惕。 據我所知,西方后現代劇場并非完全排斥文學,只是反對傳統戲劇中文學所處的至高無上的中心位置,視演出為劇本的“二度創作”,而要求將文學放到與動作、音樂、視覺等戲劇手段平等的地位。比如在德國戲劇學家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所著的《后戲劇劇場》一書中,作者也一再強調,文本并沒有失去其重要性,而是“向劇場敞開了自己”。詞語被視為劇場中聲響的一部分;對話式結構被多聲部結構所取代;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也被視覺空間的拼接所取代,從而產生出一種詩意的效果。
如果說以文學語言為主體的對話式戲劇統治劇場的時代已經結束,這是事實,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因為戲劇歸根結底是劇場的藝術,演劇向觀眾傳達的是視聽綜合的總體效果,而不單單是語言為中心的文學。重建演出文本的工作早在阿爾托、布萊希特時代就開始了,經過彼得·布魯克、謝克納,直到一系列后現代劇場導演的努力,當代劇場的文本已經高度融合了文學、表演、音樂舞蹈及各種視聽藝術手段,變得極其豐富多彩。雖然大多數作品已經不是那種以大段對話語言構成的“文學戲劇”(但好的對話式戲劇依然能在劇場中贏得大量觀眾,這也是事實),文學的因素卻始終沒有離開過劇場,迄今為止劇場的最高境界還是“詩意”——“詩在一切藝術中流注”,黑格爾在《美學》中的這句名言應該沒有過時。
這里還有一個對“文學”內涵的理解問題。也許我們許多導演認為文學就是對話和文字語言,其實文學首先是一種精神與靈魂,是蘇珊·桑塔格所說的“思想的詩學”(《重點所在》)。文學還意味著對人生現實與人性世界的幽深的洞察力,意味著對形式美的敏感性與表現力,文字語言只是文學的特殊媒介而已,在劇場的審美創造中,道理卻是相通的。戲劇中的文學因素不等于“優雅”“高蹈”,不然,達里奧·福也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戲劇文本的創作也不妨從導演開始,不妨采用排練中的即興創作,這些都不是問題,關鍵在于導演作為戲劇文本創作的“中心”,是否有一個主導性的文學的靈魂,以及足夠的文學修養與功力。
很不幸,目前國內大多數導演與此要求的距離很遠,即便如此,要是他們對文學還有一份尊重,對戲劇敘事還有一番研究,那么所謂的“爛戲”可能會少很多。更不幸的是,他們中間又有一些人自視過高,缺少駕馭文學的能力,便以“新媒體”或任意的拼貼來救場,結果搞出來的“XXX導演作品”難免從思想到敘事都不堪卒睹了。
臺灣已故的著名劇作家姚一葦在十幾年前,曾對當代戲劇排斥文學的弊端提出批評。他責問道:“劇場與文學一刀兩斷了嗎?”——
后現代劇場不需要劇本,他們也就根本不需創作者;制作人或導演取代了劇作者,只需提出一些觀念,便任其自由發展。而形成此一現象的另一根本原因,乃是不重視語言或廢棄語言……反語言反得最徹底的是后現代,語言是不能溝通的,沒有意義的;語言成為劇場的障礙、枷鎖,必要自語言中解脫出來;演員可以完全自由的發揮和即興的處理其肢體。這就是今天所見到的無可名狀的后現代劇場……文學已自劇場排斥出來,劇本亦將成為歷史名詞。然而沒有文學的劇場實際上只是一個“空洞的劇場”,因為看過后,發現它不曾給我們留下什么,因為它本身空無所有。(《后現代劇場三問》)
當代劇場以導演代替“編劇”,以某個“創意”,憑幾頁“大綱”進行即興排練的情況確實很普遍,但成功的例子實在不多。難怪姚老先生談及此種現象火氣很大,因為,這需要導演和演員的腦子不是“空洞”的。導演手里盡管掌握著全部的媒介手段,但如果缺少深刻的思想、巧妙的敘事和把控全局的功力,這種“即興”排練只能變成多媒體的大雜燴,或者無聊的玩鬧。
而這一切恰恰說明,劇場終究離不開文學——不一定是劇本、語言為主的對話體形式,而是文學的精神與根底,當下中國大多數導演缺少的就是這些方面。如此以往,戲劇能否在現今傳媒的盛宴中繼續保持自己一份獨特的味道,倒成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