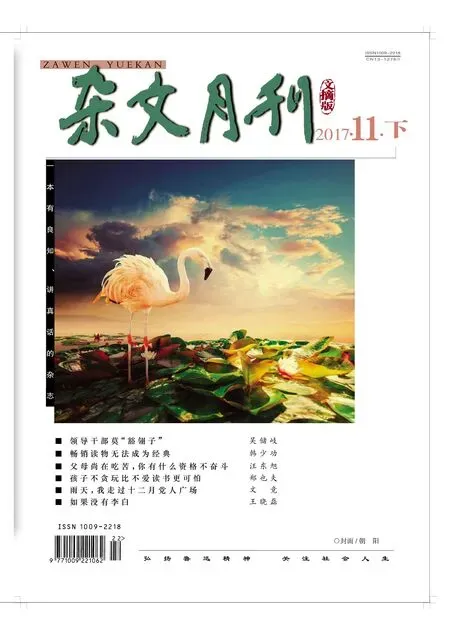興學(xué)貴誰
□樂朋
范仲淹一生傾力于發(fā)展教育。在中央,他曾主持國子監(jiān),并在慶歷改革中倡辦學(xué)校,在邠、饒、潤、越、蘇、青諸州,他都重視辦郡學(xué)。在他看來,當(dāng)時人才匱乏,原因就在“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若教育興盛,則人才涌流而出。范仲淹興學(xué)育才的治國方略,切中時弊,卓有遠(yuǎn)見。
景佑元年,范仲淹回故鄉(xiāng)、知蘇州。在發(fā)動紳民賑災(zāi)治水、興修水利之余,他仍關(guān)注鄉(xiāng)梓教育,在南園買地創(chuàng)辦郡學(xué)。南園這塊地皮,他本來打算是造屋安家的,但風(fēng)水先生勘察后稱,此處是吉地,會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聽了就改變主意,說:“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決定在南園建學(xué)舍、設(shè)郡學(xué),培育吳郡的讀書人。
科舉時代,范仲淹此舉的意義,就不只是為國育才,更顯現(xiàn)一種超脫一家一姓功名富貴的興學(xué)理念和教育觀。
舊時的士大夫,無不想世代公卿,永保富貴。他們醉心于興學(xué)、讓子弟讀詩書,為的就是使子孫后代走上科舉入仕、高官厚祿的道路;范仲淹迥然不同,他不以一家一姓之貴為榮,而以吳地一郡,乃至天下讀書人的富貴、發(fā)達(dá)為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觀,決定了他的興學(xué)、辦教育的宗旨。如果說,后來的慶歷新政,他所持的是“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的改革理念,那么他的興學(xué)、教育觀,亦可以一語蔽之:一家貴,何如一郡貴、天下貴。他要讓吳郡乃至天下的讀書人,都有一條奮發(fā)向上、進(jìn)取發(fā)達(dá)的光明大道。因他明白,如果只有一個最高學(xué)府的國子監(jiān),招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xué),那就既不能滿足治國的人才需求,且又剝奪了無數(shù)平民子弟上學(xué)求知、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同時也堵塞了他們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而一個社會的階層固化,失去流動性,它就罕有創(chuàng)新活力了。

范仲淹的興學(xué)理念和教育觀的形成,與他的切身經(jīng)歷大有關(guān)系。他雖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幼年喪父、母親改嫁、自己改姓、寄人籬下,以及流浪苦讀的求學(xué)生涯,使他對天下百姓生出濃烈的同情和憐憫之心。在仕宦40年之后,回望養(yǎng)他的長白山故地,范仲淹用“鄉(xiāng)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的詩句,寄語鄉(xiāng)人毋以其仕履為羨,而應(yīng)以詩書教育子孫后代為要。他深切地感知,一個窮苦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就是上學(xué)讀書,接受教育,舍此再無別路。他也從自己身上感悟教育的真諦:教育不該只是少數(shù)權(quán)貴長保富貴的特權(quán)或?qū)@仨毘蔀樯鐣鳎屘煜掳傩斩寄芸吹脚d旺發(fā)達(dá)的希望。
我不能說范仲淹具備了現(xiàn)代教育理念,但其一家貴何如天下貴的興學(xué)思想,不失為中國古代教育的民主性、人民性精華。他在蘇州辦郡學(xué),請名師,還和異母兄朱仲溫商議,在蘇州買田、置義莊,又手訂其管理規(guī)程等,以興辦學(xué)堂或資助族人子弟讀書應(yīng)舉,或做慈善事業(yè)。范仲淹首倡的義莊,集教育和慈善于一體,是史上最早見于記載的一個創(chuàng)造。
興學(xué)貴誰?是為少數(shù)人謀功名,還是為多數(shù)人謀福祉?即在今天,這個事關(guān)教育宗旨的大問題,依舊擺在國人,尤其是主政官員的面前。荀子云:“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王霸》)范仲淹能博得后世尊崇,其“天下同利”、以百姓子弟為念的教育觀,不能不說是他人生的一大亮點。他的這份文化遺產(chǎn),理當(dāng)好好繼承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