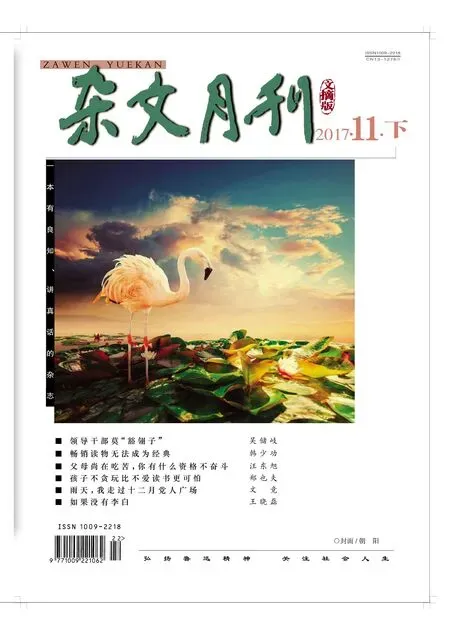雨天,我走過十二月黨人廣場……
□文 競

這里,歷史上曾有多個稱謂:元老院廣場、樞密院廣場、參政院廣場、彼得廣場……
但在一百九十多年前,三千二百余名全副武裝的禁衛軍官兵在這里集結誓師,高呼口號,宣讀憲章,要求廢除農奴制、實行民主與自由,并在這里與尼古拉一世派來鎮壓的軍隊殊死決戰,血染涅瓦河……為了紀念他們,彰顯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1925年,這里被正式命名為:十二月黨人廣場。
現在,這里綠茵鋪地,古木參天,是圣彼得堡難得的一片靜謐天地。2016年7月的一個下午,我來到了這里。站在青銅騎士躍馬揚蹄的塑像前,前面,越過馬路,是千年流淌的涅瓦河;左面,是俄羅斯憲法法院,也就是昔日的參政院(或樞密院)大樓;右面,穿過樹林草坪就是俄海軍部大廈;后面,則是世界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伊薩基耶夫大教堂。環顧四周,我覺得一百九十多年間,這里似乎變化不大。
多年來,我一直有個疑問:八個身著黑紅相間軍服的作戰方隊,一字兒在參政院門前排開,軍官刀出鞘,士兵彈上膛,那是何等的英武豪氣。為什么從早晨列隊到下午,就是不發起沖鋒、發起攻擊,非得等到尼古拉一世的軍隊發炮轟擊呢?傻呀?這還叫革命叫起義嗎?直到臨行前做功課,讀到學者王康的《高貴與美麗》,才知道這叫貴族精神。十七世紀以來,歐洲貴族盛行決斗,認為這是維護貴族榮譽和尊嚴的最佳方式。領導十二月黨人起義的軍官都是深受歐洲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俄羅斯青年貴族,他們認為沙皇的專制、農奴制以及俄國的黑暗愚昧、野蠻落后冒犯了他們的理想和信念,起義,是他們和沙皇帝國之間的一場集體決斗,因此,他們不搞暗殺,不搞突然襲擊,也堅持不開第一槍……
大概因為這里叫十二月黨人廣場,我以為總會有點與十二月黨人有關的東西,所以在青銅騎士塑像前拍完照后,我就開始在廣場四周尋找。但奇了怪了,找了半天,居然就沒找著。這個遍街都是雕塑的國家,怎么就沒想到在十二月黨人起義的事發地為他們立尊雕塑呢?
如果有這么一尊雕塑,我想我是會去表達一下我的敬意的。因為對我來說,認識他們已經很久很久了。那時,我還在四川大竹縣的一個鄉村當知青,就著煤油燈昏暗的光亮,我讀普希金的詩歌,讀涅克拉索夫的詩歌……在注釋中,我知道了他們。當然,那個時候讓我景仰讓我感動的還不是為理想為信念獻身的這些青年貴族軍官,而是站在他們身后的妻子——高貴、美麗、極富自我犧牲精神的俄羅斯貴族女性。是她們的驚世駭俗之舉、是她們感天動地的愛情將記憶深深地根植在了我的心底。
西伯利亞是什么地方?也許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飛過去不是個事。但那時,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有五千七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沒有汽車,沒有飛機,要走到那里需要一年多的時間。俄國畫家列維坦的名畫《弗拉基米爾大道》,畫的就是當年通往西伯利亞流放地的古道。看看那畫面的空曠、荒涼,看看那地平線盡頭的遙不可及,深不可測,你能想象它的恐怖和可怕嗎?冰天雪地,荒涼貧瘠,氣候酷寒,人跡罕至,那個時候,人們把西伯利亞稱作“被拋棄的世界”“沒有圍墻的監獄”“死亡和枷鎖之鄉”。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擋那些俄羅斯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那些巴黎上流社會的成功女士。作為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或情人,她們寧可放棄雍容華貴、養尊處優的生活,告別襁褓中的孩子和親人,也毫不遲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跟隨丈夫赴難。她們不怕西伯利亞的風雪肆虐、豺狼出沒,她們要與親愛的丈夫為伴。她們說:只要她們到那里,丈夫就不會太悲慘太寂寞……僅此一點,就足以讓今天的好多人流淚、汗顏。
時至今日,如果再來復述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故事,那就話長了。近兩百年來,她們的故事已被不同的國別、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學體裁反復吟詠反復歌唱。我只講一個細節:十二月黨人妻子中的沃爾康斯卡婭公爵夫人去世后,留下一本法文撰寫的《札記》。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在她的子女那里看到了這本《札記》。當夫人的兒子給涅克拉索夫翻譯這本《札記》時,涅克拉索夫感動至極,常常聽著聽著,就叫暫停,忍不住跪倒在地,像孩子一樣抱頭痛哭……涅克拉索夫的經典長詩《俄羅斯婦女》,不是創作,而是改編,藍本就是《瑪麗婭·沃爾康斯卡婭公爵夫人札記》。所以,我敢斷言: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故事,絕對是人類愛情史上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只要有人愿意了解一下她們的故事,沒有誰不會為之動容。盡管這些偉大的女性現在已經遠去了,但是,她們——卡特琳、瑪麗婭、穆拉維約娃、唐狄、波利娜、列丹久……就像天上的星辰,將永遠在歷史的時空中閃爍。
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里有一幅克拉姆斯科依的油畫《無名女郎》。多年來,人們一直對畫中的女性有多種猜測。有人說她是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有人說她就是一位演員,因為背景上隱約可見圣彼得堡著名的亞歷山大劇院;還有人說她就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我寧肯相信最后一種說法。看看坐在敞篷馬車上的那位貴族女郎,高貴的氣質、剛毅的面容、淡淡的憂傷,睥睨一切的目光……不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是誰?
有人說,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所作所為是把愛情的意義升華到了時代的最高度,她們“殉”的不只是愛情,還有自由和解放。我覺得有點拔高。十二月黨人妻子中最后辭世的亞歷山大拉·伊萬諾芙娜·達夫多娃曾說:“詩人們把我們贊頌成女英雄。我們哪是什么女英雄,我們只是去找我們的丈夫罷了……”這話實在、質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也許并不完全理解她們丈夫的信念和追求,很多妻子事發前甚至不知道她們的丈夫在干什么,但因為那是她們的丈夫,她們就覺得有責任有義務去呵護他去溫暖他。哪怕冰天雪地,哪怕海闊山重,哪怕親友規勸,哪怕沙皇命令,她們也非去不可。在俄語中,“愛”一詞的含義,不是簡單的“愛戀”,更有“憐惜”之意。俄羅斯女人與生俱來母性十足,最善溫暖失意者的心,她們是男人天然的守護神。這一點,只要去看一看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塔吉揚娜,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阿克西妮亞就會明白。所以,蘇聯時期的歷史小說家索洛涅維奇才說:俄羅斯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它是由俄羅斯女性塑造的……
雨,又開始稠密起來了。我沒帶傘,只得匆匆往回走。我想,再過九年,就應該是十二月黨人起義二百周年了。一百周年的時候,這里有了命名,那么,二百周年的時候,俄羅斯又將以怎樣的方式來紀念她們的優秀兒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