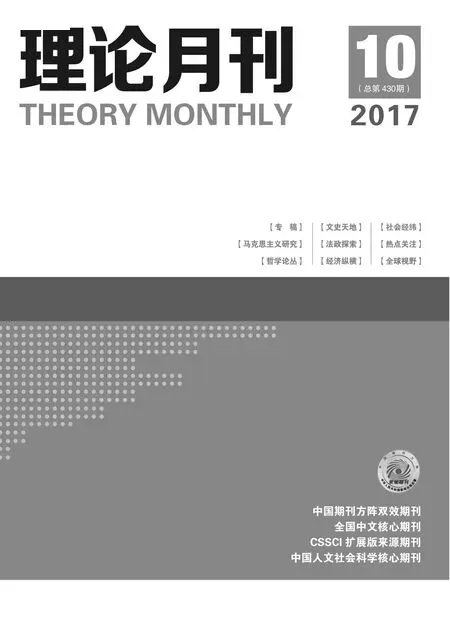我國“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民主”的本質區別
□ 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委托課題(“西方憲政民主”錯誤思潮辨析)課題組
(河南工業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1)
我國“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民主”的本質區別
□ 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委托課題(“西方憲政民主”錯誤思潮辨析)課題組
(河南工業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1)
我國“依憲執政”源于我國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其正式提出是社會主義憲政思想與我國當下國情形勢相融合的產物,中國語境下的“憲政”有其特殊的語義,也需要對其有特定的解讀方式。我國“依憲執政”在前提、過程、效果上不同于“西方憲政民主”,有其獨特的生長機理與作用方式,我國“依憲執政”不是政治斗爭的武器,其目標更具國情性,“依憲執政”的全面推行必將帶來執政理念的變化。
依憲執政;西方憲政民主;執政理念;國情性
從字面來看,“依憲執政”本身并不難理解,作為執政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依照憲法的精神和具體要求來執政。但是,這種理解又不能過于直觀,需要結合我國當下的國情,并且注意與“西方憲政民主”的區別,只有這樣,才能在同樣是依據憲法而治理的表象背后找到兩者根本的不同所在。
1 我國“依憲執政”的由來及其義解
1.1 “依憲執政”的歷史基礎
我國現行憲法頒布于1982年。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憲法在序言中提到:“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①1999年的第十二條憲法修正案將其中的“都”字去掉,改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②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二條和2004年第十八條憲法修正案分別增加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③2004年該部分表述又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之后增加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此外,1993年第四條憲法修正案還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不論如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憲法序言中得到了確認與體現。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進行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并且領導著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統一戰線,來共同完成未來國家的根本任務。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通過憲法的確認和選舉等一系列憲法程序,黨的執政地位的合憲性被確定無疑。而促使這種革命成果和民主事實法律化之后,憲法又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根據。所以,憲法在肯定完上述史實之后,在其最后一段中明確,“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中國共產黨本身作為政黨,是憲法主體,應該遵守憲法,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政黨本身就是以政治活動為目的,中國共產黨又是領導黨、執政黨,因此,憲法必然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活動準則。
1.2 “依憲執政”的正式提出
2002年12月4 日,胡錦濤同志在《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實施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這是執政黨首次提出“依憲執政”的概念。習近平同志2012年12月4日在《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被學者總結為四條要求,“一、人民民主;二、依法治國;三、人權保障;四、憲法至上”[1]。具體來說,就是“根據憲法治國理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2]。
“依憲執政”在黨的全會文件中得到了系統的解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這就進一步明確了憲法對黨依法執政的重要作用,也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必然要求。從“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上述《決定》也明確了“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這實際上從另一方面肯定了執政者也必須從一種平等的價值觀來對待自己和群眾的關系,執政活動也必須依照憲法來進行,沒有特權,這也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所必須遵循的另一項原則。
具體來說,要把憲法法律列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堅持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至上;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黨組織要領導和監督本單位模范遵守憲法法律;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要帶頭依法辦事,保障憲法法律正確統一實施;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這是對不同主體的工作要求。
1.3 “依憲執政”的具體要求
而在 “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方面又要“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這又具體體現為兩項與憲法直接相關的工作,即“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和“完善立法體制”方面。前者具體的表現為:“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這也是我國現行憲法的直接要求,執政的具體工作在這里又被重申必須依憲進行,同時,為了完善憲法實施保障制度,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這也是將我國憲法做“活”的重要路徑,塑造“活的憲法”。為此,“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確立軟性的“憲法理念”,以此來強化“依憲執政”的意識。后者“完善立法體制”,主要是發揮憲法在立法中的指導和引領作用,不僅要堅持修憲程序這一憲法慣例,還要通過完善立法體制來進一步實現憲法和立法法等憲法相關法的精神,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基礎牢固和法制統一,為依法執政確定制度依據和法律基礎。
2 我國語境下的“憲政”提法與觀念現狀
2.1 “憲政”:中國語境下的曾有概念
中文“憲政”一詞來源于日文漢字,我國首次提起并予以介紹者是晚清學者黃遵憲。黃遵憲1887年在其《日本國志》一書中介紹“立憲政體”,而梁啟超對“立憲政體”即“憲政”的明確解釋,使得這個詞所代表的政治思想為中國人所認知①參見百度百科“憲政”詞條,http://baike.baidu.com/view/36850.htm.訪問時間:2017年7月13日。。梁啟超在1899年《各國憲法異同論》和1901年《立憲法議》中對“憲政”思想特別作了介紹,提出“有憲法之政”。但這里將制定憲法作為“憲政”的核心要素。所以,清末進行所謂的君主立憲改革時,也是以此為標準進行的,先后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而后的各路軍閥也是以此為基準進行所謂的“有憲法之政”。毛澤東1940年曾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對“新民主主義憲政”進行了系統的評講和介紹,認為頒布憲法并不是憲政,他引用“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同志的話說,“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也為他后續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打下了基礎。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共產黨人張友漁1944年曾著《中國憲政論》,介紹孫中山的憲政思想、國民大會、地方制度、人民自由權利等方面的內容[3]。劉少奇同志1954年在作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時,指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堅決主張經過革命來實現他們所期望的民主憲政,也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憲政。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這正是在用歷史的觀點看待當時的問題。這也符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50多年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同志曾經在2005年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和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兩次提到了2004年憲法修正的問題,即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確定下來,把黨的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方針政策寫進憲法,是我國“憲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②分別參見吳邦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會工作報告——2005年3月9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載《人民日報》2005年3月17日,第1版;吳邦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會工作報告——2008年3月8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載《人民日報》2008年3月22日,第1版。。這實際上也是前文劉少奇報告中所提及的“對我們提出的憲法草案也是中國近代關于憲法問題和憲政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的一種回應。以上史實說明,“憲政”一詞在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并且一度起到過相應的作用。
2.2 對“憲政”的現實看法
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目前關于“憲政”概念還是存在不同的看法,既有“棄用論”,也有“續用論”[4],但真理越辯越明,正是這種學術的爭論讓我們更明確地看到“西方憲政民主”的本質,了解我國“依憲執政”提法的合理性與合乎國情的特征。拋開學術爭論不說,從實際的民眾觀點來看,不同知識結構、閱歷和經歷可能會對“西方憲政民主”的認識產生不同的結論。在課題組2015年底對本校師生展開的一次調研中,高校教師對“西方民主對發生‘阿拉伯之春’國家和‘顏色革命’國家的影響”一題的回答與高校學生就有明顯區別。教師參與調研的194人中,認為謀求所謂“西方憲政民主”的“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破壞穩定的占到了66.49%,而相比之下學生選擇“加速民主”的則占到了其參與調查總數的47.01%,僅此一點,就說明我們對“西方憲政民主”的教育尤其是高校學生群體的教育仍然任重道遠,需要由深明其理的教師廓清迷霧,完成這項重要的艱巨任務。而在對“憲政”概念本身的認識上,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調研結論中主張對其取精華和去糟粕的都占到了六成以上,而學生在此問題“去糟取精”的贊成比例甚至達到了3/4以上。這也說明了我們對我國語境中出現的“憲政”一詞應該有多層面、多視角的把握,利用其積極效用來引導民眾,而對于“西方憲政民主”所鼓吹的一套說辭要能夠揭露本質,這樣才能讓更多人看到所謂的“西方憲政民主”的真正本質。
3 我國“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民主”的本質區別
3.1 我國“依憲執政”前提上不同于“西方憲政民主”
前文曾提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地形成的。這種地位實際上取決于我們黨在建黨初期所采取的成長路徑和奮斗目標,也是很多無產階級政黨所擁有的共性特征之一。但是,中國共產黨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特殊形勢,一方面采取了與其他國家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革命路線,即農村包圍城市,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堅持的“黨指揮槍”和“槍桿子中出政權”在革命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黨通過自己組織武裝力量,逐漸成長壯大,并最終發展成為領導黨。更重要的是,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往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快速進發。也就是說,在建黨9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對中國革命的預估,作出準確判斷,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將工人階級、農民等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連成一片,以工農聯盟這種特殊階級基礎締造了新中國的政權,并且采取民主聯合政府的形式形成了新的政府,采取了人民民主專政這種符合國情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種政權組織形式政體,保證了整個國家政權的穩固,同時朝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斷邁進,在幾十年之內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完成的任務,并且保持著正確的前進方向。這種來自于歷史的基礎和民間的支持并不是通過物質犒賞和利益交換就能夠獲取的,其執政思路也不是簡單的政黨利益或集團利益,并不是通過簡單的競選承諾來變現。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11月總結了 “三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基礎上,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文化自信”,補足了“四個自信”,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總結成了“四個全面”。特別是針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問題,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四個足夠自信”,即中國共產黨在反腐敗斗爭上的決心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取得的成績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夠自信。這些都說明,中國共產黨有著堅定的奮斗目標,也有著為了實現目標的足夠勇氣,憑著這種勇氣敢于對自身開刀。而這種“開刀”的依據就是憲法,而這些“目標”也要通過相應的憲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甚至變為憲法修正案的條文,進入到憲法之中,以此來作為我們下一步奮斗的指針和動力,也就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到的 “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也就是全面踐行“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的精神。
3.2 我國“依憲執政”過程上不同于“西方憲政民主”
3.2.1 我國“依憲執政”不是政治斗爭的武器。“西方憲政民主”本身包含了兩院制、三權分立等機制,這種機制本身就包含著權力之間的抵牾與相互制約,雖然表面上這種制度設計是為了制止腐敗,但從實際的效果而言,這種制度已經成為權力之間相互掣肘的工具。有時被眾議院通過的決議在參議院無法通過,有時國會故意在某些問題的表態上與跟自己不屬于同一黨派的總統不保持一致,黨派政治摻雜其中,使問題變得日益復雜。不同黨派背后有著不同的利益群體,而黨派想要獲得自身背后的利益群體和選民的支持,不惜以國家利益為代價,為了上臺也是絞盡腦汁,故意拖延某些決策的通過。2015年2月,美國國會在沒有通知白宮的情況下邀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國會演講,這引發了美國白宮和總統的強烈反應①《以色列總理決定在美國國會演講 遭白宮顧問批評》,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226/13515461_0.shtml.訪問時間:2017年7月13日。。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權力決策歸屬不一致給國家帶來的不利。而在具體的決策過程中,一些議員為了避免一些決議迅速通過,采取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方式展開長時間拉鋸戰②為了阻攔1964年的民權法案,南方民主黨參議員們還曾進行過75小時的冗長發言,其中,羅伯特·伯德一人喋喋不休地講了14小時零13分鐘。2011年6月在加拿大國會中,加拿大新民主黨議員曾發起達58小時的冗長辯論,藉以拖延通過郵務工人復工議案。參見百度百科“冗長辯論”詞條,http://baike.baidu.com/item/冗長辯論。訪問時間:2017年7月13日。,一些人為了作秀甚至上演“全武行”,動手甚至動槍,而背后這些作秀者又會勾肩搭背,言歸于好,主要還是為了做給選民看,這些實際上都暴露了“西方憲政民主”的真實本質。
3.2.2 我國的“依憲執政”的目標更具國情性。當前,“依憲執政”是我國“依法執政”的前提和基礎,我國的“依憲執政”是為了更好地樹立憲法的權威,推進憲法的實施,實現憲法之中的黨和人民的意志。從我國憲法的內容來看,138條的憲法條文和31條憲法修正案組成了有機整體,通過“總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國家標志”這種架構形成了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關系的規范和預設,是對我國國情和歷史文化的忠實反映,并且與時俱進。而從西方有些國家的憲法實施狀況來看,已經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但竟然無法得以根本扭轉①以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保護持有與攜帶武器的權利”為例,其目的是為了反抗暴政,也是憲政文化所說的“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規定公民權利”的表現,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持槍自由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秩序和安全的最大弊病,成為有些人犯罪和濫殺無辜的最佳武器。美國多任總統想要將其廢止卻又奈何不得,原因就在于它代表的是美國建國初期的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文化,但時過境遷,今日普通的受害公民的安全和權利又從何得以保障呢?參見柳絲:《新華國際時評:控槍,為啥奧巴馬自己都頭大》,http://www.jx.xinhuanet.com/review/2016-01/19/c_1117818949.htm.訪問時間:2017年7月13日。。
3.3 我國“依憲執政”效果上不同于“西方憲政民主”
“依法執政”的提法最早是在黨的十六大被提出,其提出是為了更多地控制中國共產黨的自身行為,從而更便于依照法律來進行自我約束,推進依法治國,這種影響不僅表現于法治行為之上,還表現于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之上。比如,在行政法領域,有學者就提出應該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中推行正當法律程序,以之來規范黨的執政行為[5],而正當法律程序正是行政法的精髓,這種理念一旦梳理起來,將會影響更多的權力的控制,如黨管干部的權力等。這也成為當代中國“新行政法”發展的一種模式與路徑[6]。
從“依憲執政”的角度而言,它是“依法執政”的根本,它的提出和普及所影響的就不再是一般的法治觀念,將會是憲法觀念的質變,而在此之前,這也一直是我們的弱項。同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是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觀念,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我們更多的強調“管理”,不管是“黨要管黨”,還是“從嚴治黨”,都更多地強調作為整體的黨要更好地維護整體利益,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變化發生于權利方面,不管是國家立法還是黨內法規,都更多地側重了權利理念,從某些方面說,這可能恰恰是“依憲執政”推行所帶來的積極成果,起碼是與“依憲執政”相匹配的。正如前文的“正當法律程序”是行政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或行政程序權利的核心理念一樣,“依憲執政”的全面推行必將帶來官員執政理念的變化,人權、憲法權利等理念勢必更加深入人心,而憲法的實施和權威也就此得到強化,這也正是我國“依憲治國”的長期以來的一塊短板。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也必將帶動更多的學者關注“依憲執政”和“依憲治國”,用科研的力量進一步回饋和推動憲法實踐的進步②其實“依憲治國”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曾研究和提出過,參見莫紀宏:《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重要保證》,載王家福、劉海年等主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457頁。不能不說這種研究對后來“依憲執政”的正式提出也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目前,關于“依憲執政”的研究也在前面基礎上愈發清晰、透徹,如莫紀宏:《我國依憲執政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憲政》,載《理論導報》2014年第12期;莫紀宏:《“依憲執政”為何不能簡稱“憲政”》,載《紅旗文稿》2014年第24期;丁白,董航《求是網專訪 莫紀宏:“憲政民主”存在先天缺陷,不能與“依憲執政”類比》,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4-12/03/c_1113508278.htm.訪問時間:2016年2月17日。,要敢于深入探研,因為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良策[7][8],而開宗明義以正視聽才是我們面對疑問的正確態度。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著名憲法學者莫紀宏研究員所指出的那樣:“既要對我國現行憲法建立起來的 ‘憲政’事實表示充分肯定,同時也要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慎重應對各種形形色色非社會主義思潮利用‘憲政’概念可能導致的混淆視聽。”[9]
4 結語
“依憲執政”的提出及其與“西方民主憲政”的區別,一如多年前的“普世價值”是否成立之爭[10]。 “西方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共同目的,都是在于通過將其價值觀改頭換面并悄然植入發展中國家[11],是西方意識形態針對特定對象展開的思想滲透,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意識形態斗爭的突出表現[12]。隨著時代的推移,這種爭論的答案會逐漸明晰,此時更會顯出這種論辯的價值與效應,“依憲執政”也會在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構過程中更顯其真理性。
[1]李步云.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政之路[J].人民論壇,2014(4):48.
[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2.
[3]張友漁.中國憲政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1-2.
[4][7]韓大元.共和國六十年法學論爭實錄·憲法卷[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62-63,67-68.
[5]姜明安.正當法律程序:扼制腐敗的屏障[J].中國法學,2008(3):45-46.
[6]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0.
[8]許崇德.憲政詞辨[J].法學雜志,2008(2):25.
[9]莫紀宏.法治中國的憲法基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52.
[10]李開.“普世價值”之爭的焦點和啟示[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110-111.
[11]譚波.解讀“西方憲政民主”的前世今生[J].黨的生活,2017(7)上:27.
[12]侯惠勤.“普世價值”的理論誤區和制度陷阱[J].求是,2017(1):57.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01
D62
A
1004-0544(2017)10-0005-05
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委托課題(2016E069)。
執筆人簡介:譚波(1979-),男,河南商丘人,法學博士,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