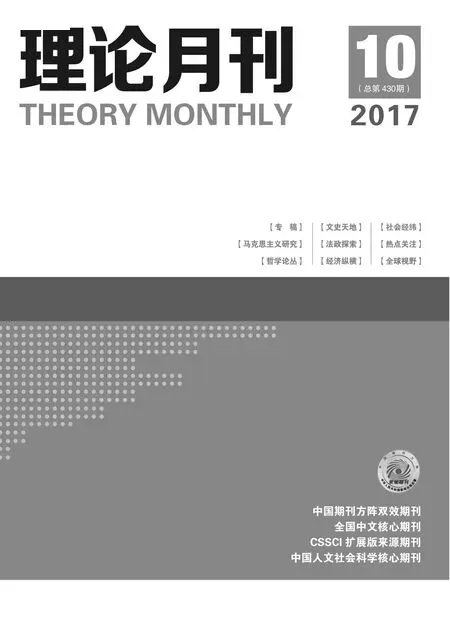論平等的限度
——基于此在存在“本意”的約束
□徐正銓
(吉林大學(xué) 哲學(xué)社會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論平等的限度
——基于此在存在“本意”的約束
□徐正銓
(吉林大學(xué) 哲學(xué)社會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平等是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在當(dāng)代西方政治哲學(xué)中平等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成為此論域中當(dāng)仁不讓的主詞。本文的論述聚焦于平等的限度問題:即平等的限度在于此在存在“本意”約束。借助于存在主義的視角解析人的此在存在論處境,以人的差異化事實為前設(shè)去對照平等之可能的籌劃,從“此在存在自身的約束”“自我所有的邊界”“公正合理的限度”三個維度來展開對平等之限度的思慮,意圖呈現(xiàn)一種能夠平衡自我與他人權(quán)益的平等觀。
平等;權(quán)利;社會公平正義;此在存在;自我所有
在當(dāng)代 “任何一種看似合理的政治理論都分享著同一種終極價值——平等”[1]。平等的觀念古而有之,興于近代,顯于現(xiàn)代,盛于當(dāng)代。隨著20世紀(jì)70年代初羅爾斯《正義論》的發(fā)表,有關(guān)平等的研究再次興起,經(jīng)德沃金和阿馬蒂亞森的推進(jìn)而成為當(dāng)代政治哲學(xué)中無法回避的主題。前者提出的問題是“平等是什么”[2],而后者的問題是“什么的平等”[3],這兩個問題都直指平等關(guān)注的核心。對于“什么的平等”而言:平等是指向機會的還是指向結(jié)果的?是指向資格的還是指向資源的?是指向權(quán)利還是能力?或者是各種指向的“中和”?這之間各有所指并不清晰,如此便有了平等的界限問題:站立在平等的通貨背后的平等之價值源自何處?是出于平等自身還是獲自他處?就“平等是什么”來說:平等所要求的是一種權(quán)利,高揚機會卻指向結(jié)果,堅守資格卻指向資源;平等所不能要求的是對結(jié)果的固守而陷入平均主義,對資源的偏執(zhí)而落入冷漠主義。僅有平等之機會卻不指向平等之結(jié)果,則平等將流于形式;空有平等之資格卻不擁有平等之資源,則平等將徒有其表;此二者都辜負(fù)了“作為社會的原則和信條”[4]的平等。而平等之所以能夠要求什么是基于“對人的平等關(guān)照和尊重”的權(quán)利觀,而之所以不能要求什么是基于此在存在“本意”的約束性限制。而平等所不能要求之處就是平等的限度所在。
1 此在存在的“本意”
順應(yīng)存在本意是所有涉及此在存在之理論論述的言說語境和首要前提。一種政治學(xué)說無論它在邏輯上有多么自洽,只要它違背了此在存在的本意,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也就是說,當(dāng)我們在生存中籌劃可能性時,作為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有所領(lǐng)會地對這一存在有所作為時,要回到此在存在的生存論前提中來。凡是違背此在存在本意的理論假說不論它在邏輯上多么自洽都是不足取的,并且可以把是否符合存在本意作為檢驗它是否具有可欲性與可行性的標(biāo)準(zhǔn)。
那么,什么是此在存在的本意?“此在”(Dasein)特指人這種不斷超出自身的存在者[5]。而“存在的本意”是指存在本身所蘊涵的意圖:使存在存在。就此在存在而言,通過對它的領(lǐng)會,認(rèn)識到“此在生存著”[6],并且是“在生存的可能性中的存在者”[7],即是此在存在的本意。此在作為一種存在者:它的存在是隨著它的存在并通過它的存在而對它本身開展出來的;它所包含的存在向來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個存在;總是從它本身的可能性——去是它自身或不去是它自身——來領(lǐng)會自己本身[8]。此在總是基于對存在本身的領(lǐng)會獲得此在存在的規(guī)定,總是在生存活動中去弄清生存的問題,使此在必然要接受存在本身所蘊涵的意圖,即存在本身必然蘊涵存在訴求:去在,去能在。此在就是為這個能存在之故而存在的[9]。
此在向來就是以能在的方式處在這種或那種可能性中[10]。這些可能性或者是自己挑選了的,或者是早已陷入其中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種可能性是如影隨形的、“最本己的、不可逾越的”。這就是死的可能性:“終結(jié)懸臨于此在”[11],死亡是此在本身不得不承擔(dān)下來的存在可能性[12]。“在向死存在中此在對它本身之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為。”[13]此在對終結(jié)的恐懼與提防伴隨著此在存在的全過程,此在以“別具一格的能在”籌劃自身,而籌劃的目的就是使此在“能在”。
“能在”的具體路線是有所作為于“善在”:人們在存在之中面臨同時涌現(xiàn)的諸多訴求,為了回應(yīng)存在之內(nèi)在訴求,就要全面把握自身的存在處境,深刻領(lǐng)會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便找到順應(yīng)此在存在本意的“能在”之道——善在。這具體地表現(xiàn)在:就個體而言是以一種“好”的方式,使生命不被自己和他人無端地傷害乃至終結(jié),善待自己并且力求以自我超越的方式實現(xiàn)自身的獨特價值,從而過上一種良善生活;共同體而言是以一套公正合理的規(guī)則體系,獲取內(nèi)部和彼此之間的善治,實現(xiàn)民族國家和整個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達(dá)成一個良序社會。
作為一種權(quán)利,平等總是有它的邊界:這個邊界首先源自存在本身的“存在論的約束”,就此在存在而言,“此在的‘本質(zhì)’根基于它的生存”[14]。 正是此在本質(zhì)的生存約束,不但召喚出了包括平等在內(nèi)的諸多價值訴求,也同時為這些訴求框定了各自邊界,即所有的價值訴求不能違背此在存在的內(nèi)在訴求,不能違背此在存在本意。這就產(chǎn)生了平等的限度問題。其次在“本質(zhì)上此在自己本來就是共同存在”,“共在也在生存論上規(guī)定著此在”[15]。共在的世界自然存在著他人的權(quán)利要求,而平等的邊界就源自他人或者自身的同等權(quán)利的要求,因而需要在自我和他人之間于“自我所有”問題上獲得某種“限度”。最后作為“與他人共在”的社會性的存在,平等的邊界源也自社會公正合理的要求,如果說他人或自身的同等權(quán)利要求是一種基于自在之善在的要求,那么基于社會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一種基于共在之能在的要求。
2 此在存在自身的約束
一切偉大的思想家所面臨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此在存在本身意味著什么?”自蘇格拉底開啟“認(rèn)識你自己”的命題以來,哲學(xué)的后續(xù)就成了對這一命題的注解。當(dāng)人們對自我的理解出現(xiàn)偏差時,其對自身的認(rèn)識也就會有問題,并且很容易將人類的實踐引入歧途,給人類的生存造成災(zāi)難。正因為如此,“如何理解自我”對于此在存在自身而言就成了根本性的命題。正視此在存在及其存在處境的差異化事實,是我們正確地理解自身的前提。平等的訴求及其限度問題的發(fā)端于此在存在的自我認(rèn)識命題,如何理解人自身是關(guān)涉到如何平等問題的關(guān)鍵。
人“作為領(lǐng)會的此在向著可能性籌劃它的存在”[16]。在伴隨此在展開的諸多可能性之中,對于平等之可能性的籌劃是“它的存在”的重要籌劃之一。人們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上展開對平等的籌劃:一是從自然狀態(tài)中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開始向著平等的理想邁進(jìn);二是從自然狀態(tài)的平等到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再想回到平等的世界中去。兩種籌劃的差別在于對自然狀態(tài)中人之處境的設(shè)想不同:到底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這呈現(xiàn)了人們對自身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后一種籌劃包含了對平等更大的期許,前一種籌劃則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于差異化的此在存在處境中展開平等可能性的籌劃。可以說,在平等的問題上,此在存在的差異化事實是我們籌劃平等之可能性是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而現(xiàn)已提出諸多的平等訴求恰恰在人之差異化的存在事實上呈現(xiàn)著不同程度的、有意無意的回避或疏忽。平等主義會不會犯功利主義同樣的疏忽:“沒有足夠低考慮到每一個個體所具有的獨特性”[17],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功利主義就是一種粗魯而偏執(zhí)的平等主義。所以“每個個體的獨特性”,也即是差異化的此在存在,就是此在存在的最大約束。
首先,差異化的此在存在表現(xiàn)為一種肉身性存在。身體是此在遭遇世界的主要方式,盡管在世界之中,此在被世界包圍,緣起又湮沒。但是身體畢竟是此在首先和實在的依靠,是此在的家園與墳?zāi)梗彩谴嗽谒行袨楣δ苷0l(fā)揮的物質(zhì)基礎(chǔ)。此在的肉身性也造成了此在存在所不可突破的物理邊際和生理斷代。由獨自面對生與死情緒蔓延開來,只能是不可替代的人生旅程和生命體驗。因此每個人的肌膚就把過分的平等要求抵擋在身體之外,任何人也不能以平等的名義去索取他人的身體器官。因此“每個人只活一次”,任何人也不能替代另一個人去生活,去綻放“別具一格”的人生。我們每個人都作為個體而出生與生活,每具軀體在出生、死亡、營養(yǎng)、痛苦和快樂方面都跟其他軀體相分離[18]。此在存在這樣一種基于“軀體”之“分離”的個體性,也訴說著生命的差異性與脆弱性。生命的脆弱性由它的肉身性所延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里蘊涵了人類境遇的本質(zhì)[19]。這樣的人類境遇同樣既召喚平等也約束平等,構(gòu)成了平等之限度的一個根據(jù)。
其次,差異化的此在存在表現(xiàn)為一種關(guān)系性存在。此在共處于世界之中,“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20],此在是關(guān)系中的個體共處于群體之中,是“自在中的共在”,也是“共在中的自在”。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開屬于共在[21],共在在本質(zhì)上已經(jīng)在共同現(xiàn)身和共同領(lǐng)會中公開了[22]。 在“共同現(xiàn)身”狀態(tài)和“共同領(lǐng)會”行為的此在展開過程中,“能在”有所作為的訴求進(jìn)行了持續(xù)性地籌劃。就平等的籌劃而言:“共在”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自在”提出了對平等之限度的要求。這兩種要求都是此在存在“本意”的要求,唯此才能使此在存在“能在”。沒有平等的要求,無視此在存在的共在性事實,“能在”難以維持;僅有平等的要求,忽視此在存在個體的差別,則“能在”難以為繼。一個以“共在”的方式而存在的人之處境中,我們始終要面對個體或群體以及彼此之間如何“能在”的問題。而唯有“善在”方能“去在”,才得“能在”。平等的限度問題所著眼的正是:共在關(guān)系中的“自在”如何在“共在”中“善在”以求“能在”的問題。
最后,差異化的此在存在表現(xiàn)為一種歷史性存在。此在不可還原為一般存在,是時間的自在性和空間的共在的合一。作為一種自我理解的存在者,人常常在自我的理想中展開自我理解。自我的理想所包含的正是“共在中的善在”如何可能的命題,也即存在“能在”本意命題。這種自我理解既可以是個體意義上的,也可以是類存在意義上的。在始終是差異化的個體生命存在處境中,領(lǐng)會“好生活”之于每個獨特生命存在而言,其實質(zhì)就是看顧好自我權(quán)益防范“積極平等”對于個體正當(dāng)權(quán)益的侵犯;在始終是共在化的群體生命遭遇處境中,領(lǐng)會“好生活”之于每個族群存在而言,其實質(zhì)就是看顧好他人權(quán)益防范“積極平等”對于共同體“持續(xù)存在”根基的侵蝕。只有把握好平等的限度,使一種平等的權(quán)利始終在它的權(quán)利邊界內(nèi)實踐,才能實現(xiàn)平等社會的美好理想。因此一種平等主張,只有成為一種有限度的權(quán)利,才能顧及個體存在差異化現(xiàn)實,才能受到存在本意的約束,才能使此在存在得以“存在”。
3 自我所有的邊界
此在存在的差異化現(xiàn)實很自然地延伸出自我所有的邊界問題。可以說,這是自洛克以降各時代的思想先驅(qū)們思考的核心關(guān)注,并且始終置于自由、平等和財產(chǎn)權(quán)等問題的追問之中。在當(dāng)代,尤其是20世紀(jì)70年代之后,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給人較深印象的就有羅爾斯、諾奇克和G.A.柯亨。柯亨甚至認(rèn)為,諾奇克哲學(xué)的首要任務(wù)并不是自由權(quán),而是自我所有論[23]。借助于自我所有的視角,通過強調(diào)此在存在及其在世處境的差異,守立自我所有的邊界,并力圖以此來把握對作為人之權(quán)利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和闡釋。主張只有在自我所有的邊界內(nèi),才能更適宜地籌劃出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杜絕突破此邊界所可能走向的奴役之路。
就平等主義而言,其籌劃的難題在于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要么是不可消除的,要么只能是有限度地削弱。差異化的個體存在方式始終是一個存在論事實,而且對這一事實的某些消除行動在價值層面上是不可欲的。因為此在存在的某些差異甚至是其存在的價值前提,故而“別具一格”的“差異”是價值生成重要因素,“認(rèn)真對待差異”是我們應(yīng)有的態(tài)度。因此,對于由平等主義所主張的,對此在存在差異的消除行動必須有足夠的警醒,這也是平等之限度的應(yīng)有之義。
當(dāng)代自由主義內(nèi)部的代表人物羅爾斯和諾奇克之間的爭論其實質(zhì)即是如何看待平等。羅爾斯認(rèn)為正義總是意味著平等,從而不平等是應(yīng)該而且能夠加以解決的。諾奇克則主張正義同平等無關(guān),正義在于堅持個人權(quán)利[24]。他們的爭論內(nèi)容呈現(xiàn)為支持其平等或不平等的理由,而焦點就是“自我所有”問題,自我的邊界到底應(yīng)該劃在何處?其實質(zhì)是:是否允許再分配,再分配是否是對個人自我所有權(quán)的侵犯,這種侵犯是否被允許?兩位大家對此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羅爾斯認(rèn)為正義是先在的,基于正義所作的制度安排有必要進(jìn)行合理的再次分配,以維持合作社會的良序永存。因此對個人所有權(quán)的某種限度的侵犯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對他人的救助主要是國家的事情(以制度的方式予以安排),不排除基于個人自愿的慈善行為,救助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部分人的基本權(quán)利。諾奇克則主張權(quán)利是先在的,基于權(quán)利而確定的東西是無論以何種理由,他人、群體和國家都不能任意剝奪的。因此個人所有權(quán)是堅決地不容有絲毫侵犯的,基于國家主導(dǎo)、政府操作的再次分配就既不被允許也無必要。而對他人的救助則僅僅是基于個人自愿的慈善行為,它與國家無關(guān),政府也只需維持在最弱的意義上充當(dāng)“守夜人”的角色就足夠了。如果國家違背個人的意愿,對財富進(jìn)行再次分配則是對個人所有權(quán)的嚴(yán)重侵害,因此是不正義的。簡單地說,我們可以把前者稱為正義話語體系,它將權(quán)利話語收納于正義體系,后者則恰恰相反,我們可稱之為權(quán)利話語體系,它將正義話語收納于權(quán)利體系。
同時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正義話語體系還是權(quán)利話語體系,就羅爾斯和諾奇克而言都是一種自由話語體系,區(qū)分出正義話語和權(quán)利話語只是表征了他們各自話語的側(cè)重不同而已。羅爾斯就明確表示“完全實現(xiàn)兩個正義原則的條件并不存在”[25]。正是基于此才使“差別原則”的存在富有意義,而“條件的并不存在”也從另一側(cè)面暗示了平等受制于現(xiàn)實處境的界限之所在。所謂現(xiàn)實處境既指向此在存在的個體化差異,也指向日常生產(chǎn)活動中對“效率原則”[26]的顧及。 “差別原則”作為最具羅爾斯特色的原則,在“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7]上既彰顯了平等主義的傾向,也流露了平等主義的無奈。因為羅爾斯的“條件的并不存在”已表明,違背“個體存在的差異化”和“日常生產(chǎn)的效率原則”的平等并不可行。對“差異化”的無視將危及此在存在的價值承諾,人的 “自尊以有差別的特性為基礎(chǔ)”[28];對“效率原則”的忽視將使所有人的權(quán)益受損,反效率理論將有悖于“持續(xù)存在”尤其是在一個競爭性的存在處境中。
人類社會縱然是由無數(shù)個人組成的,但個人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具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29]。社會存在如果不是為了個人那么它將失去存在的價值。這里的問題在于,個人是分離的,自我是獨立的,其所有權(quán)因而是屬己的。因此基于個人所有的某些權(quán)利是不可與自我相分離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生命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以及維持此類權(quán)利的財產(chǎn)權(quán)。至于生命權(quán)的不可剝奪性就劃出了一條明顯的自我所有權(quán)的界限,即使以平等的要求也是不可能地去分有他人的身體或身體的一部分 (自愿的器官捐獻(xiàn)除外),任何人沒有權(quán)利剝奪他人的生命權(quán),除非是因為對他任意剝奪了另一個生命的懲罰。至于財產(chǎn)權(quán)的不可剝奪性則產(chǎn)生了比較大爭議,諾奇克根據(jù)其“持有正義”[30]理論,主張正當(dāng)持有的財產(chǎn)也具有完全的不可剝奪性;而羅爾斯則根據(jù)“差別原則”設(shè)定了有限度的財產(chǎn)再分配方案,強調(diào)社會合作中產(chǎn)生的財富其分配應(yīng)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但也僅止于“有利于”,從而是一種關(guān)照所有社會階層利益的帶有平等主義傾向的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因此依據(jù)財產(chǎn)權(quán)所劃出的界限并不明晰,但存在這樣一條界限的論斷是被予以公認(rèn)的:不能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實。即平等總是對每個人的自我和他人權(quán)益的平等關(guān)照,它不允許借由他人之平等權(quán)益的名義而無視自我的基本權(quán)益,從而造成對個人屬己之根本利益的嚴(yán)重侵犯。
“權(quán)利都是同別人處于某種關(guān)系的權(quán)利,而別人在這種關(guān)系中也擁有一種成為對方的權(quán)利。”[31]這即是說,關(guān)系中權(quán)利的相互性是權(quán)利限制的來源,平等作為一種權(quán)利也受到相互性的“他者”限制。而基于自我所有權(quán)的界限就劃出了平等所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使是借由平等的緣故也不能要求對他人身體的分有,即使是憑借平等的權(quán)利也不能對他人的財產(chǎn)提出均分的要求。如此,則必須在把握人類自身特性承認(rèn)自身存在處境,從而在兼顧各方利益的公平正義的制度性安排下去實現(xiàn)平等主義的社會理想。
4 公正合理的限度
平等的概念是在“自我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得到說明的。正是基于“自我與他人”的邊界性界定的權(quán)利,平等意指平衡地照看“自我與他人”的權(quán)益,因此作為一種權(quán)利的邊界就隱含在這樣的關(guān)系之中。甚至可以說,如果自我的“積極自由”的邊界是他人的“消極自由”的話,那么他人的“積極平等”的邊界就是自我的“消極平等”;如果說自由之界限的設(shè)立是為了保護(hù)每一個“他人”的自由權(quán)利,平等之界限的設(shè)置是為了保障每一個“自我”的平等權(quán)利。在涉及這樣的權(quán)利之間的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范疇時,如何平衡自我與他人的權(quán)益,如何使某種平衡更具合理性,這關(guān)涉到對人自身及其存在處境的理解。
首先,人在生存論上是一種差異化的存在。正如盧梭所洞見的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32]的存在。尼采也在《偶像的黃昏》中憤憤地說“給平等者以平等,給不平等者以不平等”“決不把不平等者拉平”[33],他所拒斥的也正是這樣一種無視人在生存論上之差異化事實的觀念。其次,人在價值論上是一種“開放性”存在。這種特殊的存在方式意味著此在存在,始終是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而且這種生成是可以被向?qū)В丛谶@樣的生成過程中會有足夠的“主觀能動性”施展的空間。最后,就人之存世處境而言,人既是一種群體性共在,又是個體性自在。從“人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界定來看,則是一種共在中的自在,而且共在是先于自在的(有父母之共在始而有我之自在后而得三者共在),故而非共在無以自在。
基于此在存在的“差異化”生存論事實,平等到底是一種理想,不平等卻是一個現(xiàn)實。一方面處身于此世中的我們,內(nèi)在地要求基于現(xiàn)實來構(gòu)建理想,再以理想來指引現(xiàn)實。我們寄居于自己的理想從而返歸自己的現(xiàn)實,扎根于自己的現(xiàn)實從而認(rèn)清自己的理想,進(jìn)而在審視、質(zhì)疑、批判、想象、選擇的過程中直面現(xiàn)實與理想;在面對自身處境時,作出“審慎”又“適宜”的應(yīng)對。當(dāng)面對這種在事實上不可抹殺的“不平等”時,我們必須把它作為一個前提而予以承認(rèn)。另一方面,類的理想作為一種群體性的理想,其特殊性在于它不能向彼此差異的個人理想進(jìn)行還原,而要以通達(dá)個體的方式,規(guī)范個人理想的差異性,以便形成和實現(xiàn)自身。因此作為類的理想的平等,必須充分考量個體存在處境的差異性,對于平等理想的追求,無論如何都不能漠視個體在存在論意義上的優(yōu)先性。因為人類共同理想的構(gòu)建并不是為了取消個體生命的存在,而是要借助于類的自我理解通道,更為深刻地理解個體生命的存在論現(xiàn)實。而個體生命的存在論現(xiàn)實顯然是平等的一個限度。忽視這一限度,不但會消磨人類的進(jìn)取之心,而且會導(dǎo)致生產(chǎn)效率的低下,從而削弱平等主義社會理想得以實現(xiàn)的可能性。
基于此在存在的“開放性”價值論取向,人的生命是一個能夠在時間鏈條上自主地展開的行動。在時間之鏈上生命伴隨著選擇而涌現(xiàn)各種可能,并最終落實于理想與現(xiàn)實得以相伴相生、相反相成的存在論空間。通過對自身不斷的“能動”形塑,展開此在存在的整個過程。就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個人的現(xiàn)實活動怎樣,他的品質(zhì)也就怎樣”[34]。而以如此方式所展開的生命過程,毫無疑問地增加了此在存在和相伴而生的社會存在的復(fù)雜性與不確定性。同時也表明了此在存在的自主性,人的“生命是終極和自決的實在”[35],既然此在存在擁有這樣一種基于過去與現(xiàn)在,而指向未來的“向死而生”的獨特存在方式。也就意味著伴隨自主性選擇而來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shù)牟豢苫乇苄裕x擇“貶低人的自主和人對其行為的首要責(zé)任是一條危險的路線”[36]。因此,一種平等主義的路徑選擇只能止步于某種限度。而且就人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時間性存在的個體存在,還是作為歷史性存在的類存在,都必須顧及一種“歷史原則”的主張,“過去的狀況和人們的行為能夠產(chǎn)生對事物的不同資格或不同應(yīng)得”[37]。而且按照基于過去的歷史原則也能通過現(xiàn)在的行為引導(dǎo)未來的事態(tài)。因此無視選擇主體自身責(zé)任的“超限平等”,無視“歷史原則”的歷史性維度的“目的—狀態(tài)”[38]的平等追求,只能導(dǎo)致對自身存在“本意”的背叛。
基于此在存在處境的考量,只有一種“自我”與“他人”權(quán)益得到合理平衡的方案,才能使“共在”關(guān)系中的“自在”的“善在”成為可能,使“自在”聯(lián)合成的“共在”的“能在”成為可能。正義話語體系關(guān)涉彼此群體性共在之能在的可能,關(guān)注的是每一個個體的善在之可能,是把個體理解成關(guān)系處境中的個體。相比較而言,權(quán)利話語體系關(guān)涉首先定位于個體自身的利益訴求,關(guān)注的是個體自身之獨善的可能(此種“關(guān)注”可能導(dǎo)致的個體間沖突使得“獨自善在”并不可得),是把個體理解成原子處境中的個體,這有可能易于打破此在存在的“本意”。因此,從此在存在的“善在”以成“能在”的立場看來,以群體性維度的正義話語來涵蓋個體性維度的權(quán)利話語似乎更為合理。正義為先,方有權(quán)利,權(quán)利的問世也正是“出于”“共在”中“自在”的“善在”,以公正地“共在”來成就“自在”的普遍“善在”。如此把“平等權(quán)”納入正義的話語體系,那么它就受到了“正義”的約束,基于平等之權(quán)利訴求不允許無限擴展以致突破正義的限度,而陷入自我與他人之間權(quán)益失衡的泥潭。不平等有悖于正義的理想,“越界的平等”照樣有悖于正義的理想,所以平等必須被限制在不失公正合理的范圍內(nèi)。這樣,平等獲得了公正合理的限度。
5 “自我他人”權(quán)益平衡的平等
如果,平等的限度的實質(zhì)正是在于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人性以及他們的利益和相互關(guān)系[39]。需要明白的是:為什么人應(yīng)該受到平等的尊重與關(guān)照,什么樣的行為最能展現(xiàn)出這樣一種“被平等對待”的“關(guān)照與尊重”。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平等是可欲又可行的平等?一種既具可欲性又具可行性的平等應(yīng)該受到哪些約束?它的可欲性來源于哪里?它的可行性將去往何方?
平等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價值,其可欲性源于人類社會的理想。勒魯就認(rèn)為“平等是自然萬物的萌芽,它出現(xiàn)在不平等之前”,并且“將會推翻不平等,取代不平等”,相信“從社會的起源和終止這兩方面來看,人類精神統(tǒng)治著現(xiàn)實社會,并把平等作為社會的準(zhǔn)則和理想”[40]。追求社會的平等,實現(xiàn)對每個社會成員的平等關(guān)照與尊重一直是人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平等的理想性是其可欲性的來源,因為但凡一個理性的存在者沒有不希望被平等對待的。而平等的可行性卻必須接受此在存在“本意”的約束,經(jīng)受個體的“自我所有”和社會的“公正合理”這兩個維度的限制,才能走向具有明顯平等主義風(fēng)尚的 “自我與他人”權(quán)益平衡的理想社會。如果沒有這樣的限制,則正如金里卡所言“如果試圖使手段平等,卻反而阻斷了人們實現(xiàn)自己目的的可能性,我們就徹底失敗了。”[41]因此,無論是平等還是自由的價值都是受到此在存在“本意”約束的,當(dāng)自由或平等的權(quán)利沒有侵犯他人或自我的正當(dāng)權(quán)益時,它們將有益于存在的“去在”;反之,當(dāng)自由或平等的權(quán)利突破了各自的限制,則存在自身就難以為繼。哈耶克曾針對自由說過“自由之成為可能,正是因為這些限制”[42]。我想:平等之成為可能,也正是因為這些限制。
總之,一種平等之可能性的籌劃,需要充分領(lǐng)會此在存在自身的存在處境,領(lǐng)會“生存”的根基和“共在”的世界對于平等的召喚與約束。這需要充分考慮到自我與他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邊界,又顧及到對社會公正合理的共在之能在的存在訴求,只有如此這種平等的籌劃才是即可欲又可行的。要而言之,平等可以要求的是自我與他人權(quán)益平衡看顧,不可以要求的是對此在存在“本意”的違背。
[1][39][41]威爾·金里卡.當(dāng)代政治哲學(xu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4,48,84.
[2]RONALD DWORKIN.What Is Equality?Part 1:Equality of Welfare [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81(10).
[3]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1[G]//McMurrin.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
[4][40]皮埃爾·勒魯.論平等[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8:20,15.
[5][6][7][8][9][10][11][12][13][14][15][16][20]
[21][22]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539,71,48,17,112,350,308,309,311,149,153,187,151,157,204.
[17][18]瑪莎·C·納斯鮑姆.正義的前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6:198,166.
[19]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追尋美德[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56.
[23]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81.
[24][28][30][31][36][37][38]羅伯特·諾奇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8:譯者前言,24,293,183-184,316,256,186,186.
[25][26][27]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8:302,67,83-84.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32]讓-雅克·盧梭.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與基礎(chǔ)[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45.
[33]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黃昏[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14.
[34]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37.
[35]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33.
[42]F·A·哈耶克.致命的自負(fù)[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0:53.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09
B086
A
1004-0544(2017)10-0050-06
徐正銓(1980-),男,浙江蘭溪人,吉林大學(xué)哲學(xué)社會學(xué)院博士生。
責(zé)任編輯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