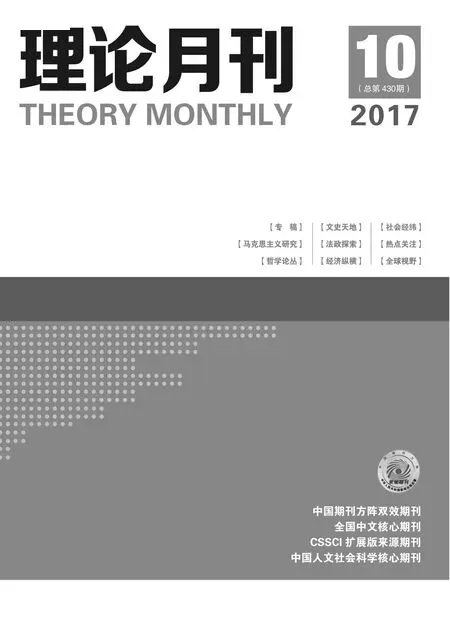介入醫患糾紛:醫務社會工作發展的“雙刃劍”
□苑曉美,賴志杰
(1.南開大學 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天津 300350;2.江西財經大學 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介入醫患糾紛:醫務社會工作發展的“雙刃劍”
□苑曉美1,賴志杰2
(1.南開大學 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天津 300350;2.江西財經大學 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醫務社會工作對其功能有自身的專業定位,而政府則將其功能定位為介入醫患糾紛。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可以發揮預防糾紛發生、降低沖突烈度與彌合醫患裂痕的作用,是醫務社會工作獲得政府和社會以及醫療衛生機構承認以獲取快速發展的現實捷徑。但介入醫患糾紛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陷入角色沖突與倫理困境而喪失專業自信,同時因在現有醫療衛生體制下作用有限而喪失自我承認,從而阻礙醫務社會工作的長遠發展。
醫務社會工作,醫務社會工作者,醫患糾紛,促進,阻礙
醫務社會工作基本完成了恢復重建,迫切需要獲取進一步的發展。從專業角度來看,醫務社會工作有豐富服務領域與服務對象,但政府出于醫患糾紛頻發的形勢,將其功能定位為介入醫患糾紛。本文從醫務社會工作功能的自我定位與政府定位入手,介紹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所能發揮的具體作用,重點分析迎合政府和社會以及醫療衛生機構的介入醫患糾紛的需要對醫務社會工作發展效果的正反兩面性。
1 醫務社會工作功能的專業定位
醫務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個實務領域,同時也是社會工作所有服務領域之中對專業化程度要求最高的領域之一。從專業的角度來看,醫務社會工作是指社會工作者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和專業倫理的指導下,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理論、方法與技巧,在醫療衛生機構中作為醫療團隊的一部分,協助有需要的病患及其家屬,有針對性地解決就醫過程中產生的心理、社會問題[1]。在醫療衛生機構內,醫務社會工作者與醫護人員的服務對象雖存在交叉重疊,但兩者在專業角色和定位上大相徑庭,前者關注心理疾病(心理健康)以及社會疾病(社會健康),后者專注于生理疾病(身體健康),同時兩者在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和角度上也截然不同。醫務社會工作的職能還可以擴展到健康照顧領域中,以健康促進和公共衛生為目標,開展與疾病預防、保健、康復等相關的專業服務活動,從而整體提高人們對疾病的預防和保護意識。由此可見,醫務社會工作的工作場域不局限于醫療衛生機構,除了在醫療服務機構直接提供服務外,醫務社會工作還將服務范圍延伸到醫療衛生機構以外的家庭、社區、社會等廣泛間接層面。相對應地,醫務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十分廣泛,除去患者及其家屬,其服務對象還涵蓋醫護人員、社區居民等群體。同時,醫務社會工作的實務范圍涉及到疾病預防、疾病治療、回歸康復、家庭和社區健康等領域[2]。
2 醫務社會工作功能的政府定位:介入醫患糾紛
當前醫患關系緊張、醫患糾紛頻發,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錯綜復雜,普遍認為與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社會化改革不無關系。政府降低了對醫療衛生機構的財政投入,將其推向市場以為居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方式來獲得經濟補償,導致醫療衛生服務的公益性、福利性以及可及性大幅下降。此外,醫患溝通不當、醫患信任下降以及媒體炒作誤導等也是導致本來在社會地位、資源占有、利益分配和思想觀念等方面差異較大醫方和患方之間嚴重失和的重要原因[3]。近年來各地傷醫、殺醫等惡性事件頻頻曝光于媒體,反映出醫患關系緊張態勢不減反增,社會影響愈加惡劣。
通過前文對醫務社會工作功能的專業定位分析可見,病患及其家屬是醫務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服務對象,由此確實可以衍生出改善醫患關系、預防醫患糾紛的功能。然而從官方的政策文本來看,出于上述醫患關系緊張的現實,醫務社會工作改善醫患關系、預防醫患糾紛的衍生功能被工具化為介入醫患糾紛。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了 “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戰略方針,社會工作制度的建設提高到了國家層面,醫務社會工作也隨之步入恢復重建時期。為此原衛生部人事司開展了衛生系統“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現狀調查與崗位設置政策研究”,研究報告的基本結論認為醫務社會工作是改善公共關系和醫患關系,預防和減少醫療糾紛的最佳途徑,醫務社會工作制度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關系最有效的舉措[4]。被譽為拉開新一輪醫改序幕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09]6號)中明確提出,將開展醫務社會工作作為完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增進醫患溝通的重要方式之一,以構建健康和諧的醫患關系。2010年司法部、原衛生部、保監會聯合頒發的《關于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司法通[2010]5號)也提出發揮社會工作者的作用,將其納入到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員隊伍。
3 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的具體功能
目前各地不少醫療衛生機構設置了醫務社會工作部門或崗位。從已有實踐來看,醫務社會工作者運用專業方法與技巧在醫患關系日常維護、醫患糾紛事中調處與醫患關系事后修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
3.1 參與醫患關系日常維護,預防糾紛發生
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的首要任務是預防沖突的發生,事前預防階段也是醫務社會工作介入的最佳契機,在此階段醫務社會工作者能夠擔任教育者、咨詢者和策劃者等角色。在教育者角色方面,醫務社會工作者面向的是醫療衛生機構的全體醫務人員,通過安排醫患關系、醫患溝通、醫療法規等相關的課程或講座,借助豐富的相關案例,對醫務人員開展培訓,增進其對醫患關系的敏感度,削減醫患糾紛發生的可能性。在咨詢者角色方面,醫務社會工作者面向的是病患及其家屬,提供包括就醫流程、醫院布局、藥費報銷、社會福利政策等相關的信息咨詢服務。在策劃者角色方面,醫務社會工作者同時面對醫護人員和患者及其家屬,開展小組工作搭建醫患溝通的平臺,通過組織“病人課堂”“健康知識講座”“醫患溝通會”等活動,邀請醫護人員向病患者及其家屬介紹醫療護理知識、解答診療問題、講解臨床照顧技巧等,增加醫患溝通的機會,防止沖突的發生[5]。
3.2 參與醫患糾紛事中調處,降低沖突烈度
病患及其家屬在醫患關系的沖突階段與醫療衛生機構發生糾紛,醫患關系通常會急劇惡化,此時醫患糾紛的調處對降低醫患沖突的烈度乃至醫患關系的事后修復至關重要。醫療糾紛是醫患糾紛的最主要形式,醫療糾紛的傳統處理主要有協商、調解與訴訟三種方式,其中訴訟被認為是效率最低的方式[6]。在訴訟外調解,包括當前政府大力推廣的人民調解與醫療責任保險結合的第三方調解中,醫務社會工作依然有重要作用。醫務社會工作者在醫患糾紛調解階段可以充當輔導者、調查者、協調者等角色。在輔導者角色方面,由于處于醫患沖突階段的病患及其家屬、醫護人員均易產生負面情緒而采取極端處理方式,故而醫務社會工作者在此階段最主要的任務是進行情緒輔導治療,發揮同理心,給予適當的安撫和支持,幫助其克服情緒障礙,緩和尚未擴大的醫療糾紛[7]。在調查者角色方面,醫務社會工作者通過調查、談話等方式及時、全面地了解糾紛或沖突的癥結所在,反饋給醫療衛生機構及醫護人員,幫助其作出綜合判斷。在協調者角色方面,醫務社會工作者在保持價值中立的前提下,依據相關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引導醫患雙方達成解決糾紛的方案[8]。
3.3 參與醫患關系事后修復,彌合醫患裂痕
隨著解決方案的達成,醫患糾紛的調處隨之結束,往往忽略了因糾紛而緊張甚至破裂的醫患關系的修復工作。即使是人民調解與醫療責任保險結合的第三方調解也通常隨著賠償金的給付而戛然而止。有調查研究表明,比起經濟賠償,患方更看重醫方的道歉和解釋,即患方更需要獲得感情上的撫慰[9],因此從構建和諧醫患關系角度來看,還要做好彌合醫患裂痕的工作。醫務社會工作者此時可以繼續充當解釋者、調解者的角色,陪同醫護人員或代表醫療衛生機構向病患及其家屬做好相關事項的解釋工作,撫慰醫療意外或沒有達到預期調解期望的病患及其家屬的負面情緒。
4 介入醫患糾紛是醫務社會工作發展的 “雙刃劍”
上述分析可見,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關系確實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醫務社會工作的功能的自身定位不同于政府定位,對介入醫患糾紛所能產生對醫務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
4.1 短期發展的“助推器”
我國的醫務社會工作伴隨北平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的興建由美國傳入中國。美國率先引入專業醫務社會工作的麻省綜合醫院社會服務部與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同步誕生,兩者同時還有一定的淵源。前者正式設立于1919年,后者成立于1921年;后者的主任、中國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先驅者浦愛德曾于1920—1921年間在前者的負責人坎農的指導下進行為期一年的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學習,也正是坎農從中捍衛了醫務社會工作在北平協和醫院的專業地位[10]。可以發現,中國醫務社會工作的發端與早期發展與專業醫務社會工作的發源地美國幾乎保持同步。但伴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以及1950—1978年社會工作教育的停滯,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處于中斷狀態。此后隨著社會工作教育的恢復重建,醫務社會工作也逐漸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但不得不承認發展速度是較為緩慢的。
中國的醫務社會工作要獲得快速的發展,在宏觀層面上要獲得政府和社會的承認。王思斌認為政府和社會的承認對社會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他們對社會工作服務效果的判斷是社會工作獲得承認的決定性條件[11],這同樣適用于醫務社會工作。如前所述,醫患關系緊張、傷醫殺醫等惡性事件頻發的背景下,政府和相關部委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對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的功能進行定位,這直接反映了政府和社會對醫務社會工作的承認以及對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服務效果的期待。但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還要在微觀層面上獲得醫療衛生機構的承認。醫療衛生機構中已經有工作人員在處理醫患關系方面的事務,或者說已經有非專業、半專業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存在。這部分群體主要由醫療衛生機構中的行政人員或醫護人員轉崗而來,雖沒有經過或只經過基礎性的醫務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培訓,但他們熟悉醫療衛生機構的環境,有的甚至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在為病患及其家屬提供疾病知識、解答診療問題,維護機構正常秩序等方面具有優勢。概言之,一方面,介入醫患糾紛是醫務社會工作當前獲得政府和社會承認的最現實、最便捷的途徑;另一方面專業醫務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效果需要在較大程度上優于非專業、半專業醫務社會工作群體,否則依然難以得到醫療衛生機構的認可并獲得更廣闊專業實踐權。正是這種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境遇,迫使專業醫務社會工作者必須注重醫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強化社會工作技能技巧的實踐,這在客觀上對完成恢復重建的醫務社會工作在短期內迅速進入發展快車道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4.2 長期發展的“絆腳石”
介入醫患糾紛可以同時獲得政府、社會與醫療衛生機構的承認,可以在短期內助推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但從長遠來看,將介入醫患糾紛作為實踐的唯一或關鍵領域,也將阻礙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
4.2.1 介入醫患糾紛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陷入角色沖突。目前在醫療衛生機構設置醫務社會工作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醫院編制內設置醫務社會工作崗位,另一種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醫務社會工作者以第三方的身份進駐醫療衛生機構。不難發現,第二種設置方式有利于保證社會工作者的獨立性,但實際上這種設置方式鮮見,而且醫務社會工作者由于是編外人員難以得到醫療衛生機構的認可,難以協調資源開展活動[12]。第一種設置方式是目前醫療衛生機構設置醫務社會工作的主流方式,這種設置方式下的醫務社會工作者是醫院的員工,在介入醫患糾紛時容易以維護醫方的利益為出發點開展工作,以解決當前的問題為目的,難以確保自身中立者的角色。換言之,從職業生存層面來看,維護醫方利益、減少醫方的損失、得到醫方的肯定,才能得以立足。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有賴于社會工作專業使命以及醫療衛生機構的接納和支持,醫務社會工作的專業使命要求醫務社會工作者幫助弱者、維護病患及其家屬的利益,醫務社會工作者在維護醫方利益與患方利益間容易陷入兩難的境地而產生角色沖突。
4.2.2 介入醫患關系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陷入倫理困境。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往往需要承擔溝通協調的工作,醫療衛生機構、醫護人員、病患及其家屬均對醫務社會工作者抱有期待,因為各自的出發點有所差別,導致醫務社會工作者常常陷入倫理困境。案主自決原則要求醫務社會工作者鼓勵案主自我作主和自我決定。當醫患糾紛尤其是醫療糾紛發生時,基于對權威的依賴,病患及其家屬傾向于征詢醫務社會工作者的意見,甚至期望其代為判斷或處理。若基于案主自決原則進行回避,患者及其家屬會誤認為醫務社會工作者推卸責任,互相信任的專業關系難以建立;若進行積極干預,在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中難免代入個人的價值觀,難以保持價值中立,由此陷入倫理困境[13]。保密原則要求社會工作者有義務保護在專業關系中獲得的信息,在醫務社會工作者介入醫患糾紛時,既要為患方的個人信息、家庭狀況等信息保密,又要為醫方的診療過程、診療決定等狀況保密。特別是當醫護人員在診療過程中出現操作失誤時,醫務社會工作者礙于未被授權不能告知患者及其家屬醫療過失的事實真相,難以成為患者及其家屬的權利捍衛者,往往讓醫務社會工作者陷入兩難的境地。
4.2.3 現有體制機制下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作用有限。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患糾紛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這些也只是所謂的“柔和劑”“潤滑劑”的作用。醫患糾紛在廣義上是指病患及其家屬與醫療衛生機構、醫務人員之間發生的所有糾紛,在狹義上是指病患因購買、使用或接受醫療服務而與醫療衛生機構、醫護人員發生的糾紛。一方面,醫務社會工作無法觸及導致醫患糾紛頻發的深層次體制方面的因素。從根本上緩解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有賴于增加政府投入、均衡醫療資源配置以扭轉廣大群眾看病貴、看病難的狀況。此外,醫患糾紛主要是在醫療服務的提供與消費過程中發生,這就決定了醫患糾紛的調處主要以醫學和法律人士為主體。另一方面,醫務社會工作在醫療衛生機構內受制于醫療與行政兩大傳統權威。在傳統醫療模式中的醫療團隊里醫生占主導地位,醫務社會工作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同時,醫務社會工作介入醫療糾紛的調處仍然需要風險預防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檢討和改善機制等一系列的配套機制,而這些機制的建立需要消耗一定資源,有賴于醫療衛生機構行政系統的認可與劃撥。
5 小結
醫務社會工作有其自身的專業功能定位,在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下注重病患心理疾病與社會疾病的治療,在慢性病為主的疾病模式中開展與疾病預防、保健、康復等服務。而在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形勢下,政府出于社會治理的需要將醫務社會工作的功能定位為介入醫患糾紛。醫務社會工作參與在醫患關系日常維護、醫患糾紛事中調處與醫患關系事后修復,對預防糾紛發生、降低沖突烈度與彌合醫患裂痕有所作用。
我國的醫務社會工作教育基本完成了恢復重建,醫務社會工作專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獲得各方面的承認。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與公共資源的掌握者,政府的承認對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的傾向性決定了醫務社會工作的優先發展領域;社會的承認對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社會對醫務社會工作服務效果的判斷決定著醫務社會工作實踐發展程度;醫療衛生機構是醫務社會工作主要的工作場域,醫療衛生機構的承認對醫務社會工作的發展有直接作用,醫療衛生機構直接控制著醫務社會工作的實踐權,介入醫患關系是醫務社會工作獲得承認的最現實、最便捷的途徑,對醫務社會工作的短期發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但如果將介入醫患糾紛作為醫務社會工作實踐的唯一或關鍵領域也將阻礙醫務社會工作的長遠發展。這是因為醫務社會工作者在糾紛調處過程中容易陷入職業者與專業者的角色沖突,在職業生存與專業使命之間而難于取舍,而案主自決與保密原則等也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陷入倫理困境而無所適從,長期來看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喪失專業自信。同時,醫務社會工作無法觸及醫患關系緊張、醫患糾紛頻發的根源性的體制因素,在醫療衛生機構內部也受制于醫療與行政系統,發揮的作用有限,長期來看將使醫務社會工作者喪失自我承認。
[1]王衛平,許麗英.關于醫務社會工作者在協調醫患關系中角色定位的思考[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0):167-169.
[2]劉繼同.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醫務社會工作的歷史回顧、現狀與前瞻[J].社會工作,2012(1):4-10.
[3]覃國慈.社會沖突理論視角下的醫患關系研究[J].江漢論壇,2014(3):140-144.
[4]衛生部人事司.中國醫院社會工作制度建設現狀與政策開發研究報告(摘要)[J].中國醫院管理,2007(11):1-3.
[5]張良吉,郭永松,李平,李秀央.醫務社會工作改善醫患關系的機制研究[J].中國醫院管理,2009(3):9-10.
[6]賴志杰,張瑞,徐芳芳,黑啟明.我國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的實踐考察與完善對策[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5):102-108.
[7]陳武宗,賴宛瑜,郭惠旻,林東龍.歷史宿命或時代使命: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介入醫療爭議事件之分析[J].臺灣社會工作學刊,2009(7):1-48.
[8]陳靜,欒文敬.醫療社會工作視角下和諧醫護資源網絡的構建[J].社會工作,2012(7):56-59.
[9]SUSAN JSZMINA, ADDIE M JOHNSON,MARGARET MULLIGAN.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 in Medical Malpractice:A Survey of Emerging Trends and Practices [J].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2008(1):71-96.
[10]賴志杰.浦愛德與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的醫務社會工作:兼談中國醫務社會工作的發端與早期發展[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18-28,50.
[11]王思斌.走向承認:中國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J].河北學刊,2013(6):108-113.
[12]卓美容.滬深兩地醫務社會工作發展模式比較[J].中國社會工作,2013(2 上):30-32.
[13]崔娟,王云嶺.論醫務社會工作本土化過程中的倫理困境及對策:以“案主自決”原則與中國本土價值觀沖突為例[J].中國醫學倫理學,2014(5):670-672.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29
C916
A
1004-0544(2017)10-0158-05
海南省教育科學規劃一般項目(QJY1251530)。
苑曉美(1989-),女,河北保定人,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博士生;賴志杰(1984-),男,江西尋烏人,社會學博士,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楊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