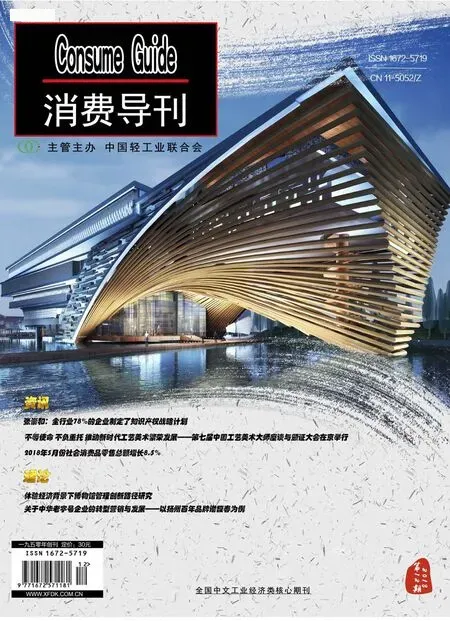公共政策視閾下對“雄安新區”建設的思考
孫可萱 北京郵電大學經理管理學院
公共政策視閾下對“雄安新區”建設的思考
孫可萱 北京郵電大學經理管理學院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省保定市設立的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以分擔北京的部分中心職能、紓解北京市過大的城市負擔。新區決定建立至今,已經可以看到相關政策的跟進實施,但整體的戰略布局還未完全展開。
雄安新區 公共政策
“雄安新區,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摘自百度詞條。
國家對于雄安新區的定位是將其建設為創新發展示范區。其中囊括了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范區和開放發展先行區這四個概念。
本文將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方面闡述雄安新區的發展思路。
政治方面,設立雄安新區意在探索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新路徑,促進轉變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模式。同時,不同于以往“北京對河北的輻射帶動作用”單純把北京的范圍擴大再擴大,雄安新區位于北京和保定中間,并將會是一個不依附于北京的單獨經濟體。雄安新區可以預見的蓬勃發展將毫無疑問地帶動廣大河北地區的發展。其綠色協調發展的模式也有望轉變河北地區現有的資源集中型的發展模式。從某種角度上說,這種“自立門戶,劫富濟貧”的模式,于首都北京而言緩解了過大的城市負荷,于河北而言則迎來了發展的重大機遇。所以有媒體形容雄安新區的建設是“既給北京添一翼,又給河北添一翼”。
但從另一種角度來看,縱使雄安新區的建設有國家的大力支持,但在如今一窮二白的土地上建設一座現代化的新城無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雄安新區發展前期不僅需要北京的傾囊相助,更少不了廣大河北地區的支持。這對于河北地區而言無疑是又一次財力物力和心智上的考驗。同時,新區一旦建成,面對的將是來自北京和河北兩方面的訴求。屆時年輕的新區如何應對訴求,如何在三方的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將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河北不應一味高興,因為雄安建設的投入期將會很長,雄安地區也不應沾沾自喜,因為他的紐帶任務任重而道遠。
經濟方面,我認為雄安新區的經濟建設較其他城市而言有更大的優勢。這不僅僅是因為國家的政策扶持,更因為雄安新區的發展理念中有很重要的“協調發展”這一條。這決定了雄安新區從發展規劃到實施再到完善的過程中將得到相關專家的幫助。專家集團將幫助雄安規劃一種更科學和具有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經濟發展模式。
雄安新區為首都北京紓解的一項重要職能為科技中心的職能。從產業鏈的完整性角度來看,伴隨著雄安新區科技研發水平的提高,該區將興起一批以科技技術水平為主導區位要素的新興企業。
另外,一大波央企已經蓄勢待發。截至4月8日中午,已有中核集團、中廣核集團、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重工、中國電科、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大唐、中國華電、中國三峽集團、神華集團、中國聯通、中國電子、國機集團、中國建筑、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招商局、中國中冶、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交建、新興際華、中國能建、中國國電等26家央企集體發聲“雄安新區建設不缺席,與發展政策同頻共振”。這就是所謂雄安新區發展“高起點”的體現了。
文化方面,教育功能的遷入將會帶動雄安新區整個教育產業鏈的發展。隨著首都部分高校的遷入,一系列教育資源將涌向新區,進一步將會吸引相關學術人才的涌入。除此之外,與高校相配套的一系列問題也將促使雄安新區的完善與發展。例如:高校教師的住房問題與戶口問題、教師家屬的就業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遷入勢必會帶動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發展,有力緩解河北現有的教育困境。現階段河北省的教育資源十分集中,“衡水一高”“衡水二高”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代表,衡水市更是全國少有的以教育為支柱產業的城市之一。且現階段河北省的教育完全偏向應試教育,與之毗鄰的北京則更偏向于素質教育。
我認為,雄安新區的設立將會打破這種固有的教育模式。隨著雄安新區的發展,將有大批從北京遷出的居民和從河北各地前來“淘金”的居民落戶雄安,這會極大地增加對教育資源的需求量。河北傳統的“衡中模式”將因不能適應這種大規模的需求而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將是一種更良性的教育模式。其次,從北京遷出的居民將不能適應河北的“高壓應試教育”而尋求轉變,雄安新區將亟需探索出一條將“河北傳統大班制應試教育”與“北京式素質教育”相結合的教育路徑。此外,我認為雄安新區這一“緩沖帶”的出現將有效中和北京與河北的文化格局。這對于雙方都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方面,雄安新區的設立對于北京、河北乃至整個華北地區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心態都有很大的影響。于北京市民而言,城市壓力的紓解會直接減小市民的生活壓力,北京的“邊緣人”也可以在新區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對于二者而言都是一種良性的轉變。于河北人而言,河北幾十年來都在為北京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卻回報甚少。雄安新區的設立是國家向滿懷怨氣的河北人發出的一個訊號,且不論新區的設立是否能全面惠及河北,但這已經讓河北人民看到了發展的希望。這種情緒紓解的作用與梅奧“霍桑實驗”中的訪談實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雄安新區的設立是否能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的我們還未可知,但這一政策的社會協調作用卻已經初露端倪。新政剛一出臺,廣大河北人民已經不再想盡辦法擠進北京,而是轉而尋求在即將迎來新生的雄安新區尋找發展機遇了。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新區的建設還未真正步入正軌,但一系列政策已經開始實施,例如新區的“限房令”等。從這些雷厲風行的政策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央政府將雄安新區建設為綠色的、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城的決心。
總的來說,雄安新區的發展雖然充滿機遇,同時也伴隨著隱性的挑戰。如何制定出一套合乎新區發展定位的政策是新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
孫可萱(1996.4-),女,遼寧營口人,漢族,北京郵電大學經理管理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