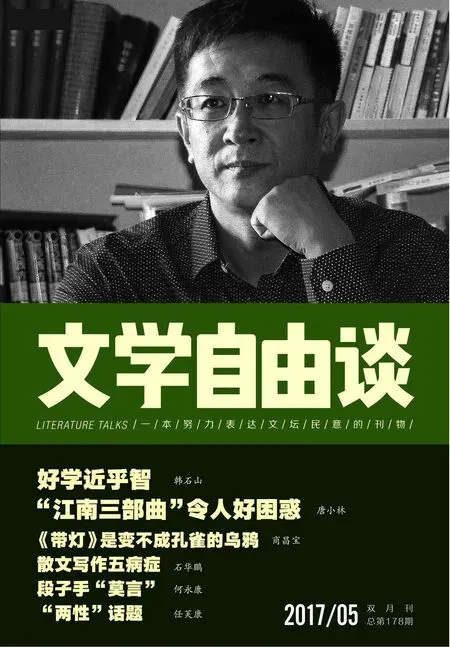如今的文學江湖
周思明
如今的文學江湖
周思明
A
如今的文學江湖,成了一個名利場。一些不入流的寫作者,削尖了腦袋,利用各種機會,極盡各種手段,想千方設百計,絞盡腦汁也要混進場子里去。去干嘛?沽名釣譽,出人頭地。一些人深知,欲達此目的,先要爭得一頂作家的桂冠——雖然,如今作家的名號已然大大貶值。
如今“作家”一抓一大把。一些自稱“作家”的人,雖然也常有“作品”面世,但這個“世”,并非國家、省、市那些具有一定準入門檻的正式刊物,更多的是沒有門檻、無需審查的互聯網、手機微信公眾號上,或者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報、小刊。
當作家,怎么也得出一兩本書吧?現在的人,似乎都不差錢。在正經刊物上發不出作品?沒關系,書卻是一本接一本的出,就像有些煙鬼,煙一根接一根地抽。這些人出書往往是個人出資,或有人贊助。出書之后,立馬成為“少年作家”“美女作家”“官員作家”“商人作家”……但隨便翻翻那些“大作”,又有多少文學性或文化含量呢?
浮躁的社會,制造出浮躁的寫作者;浮躁的寫作者,反過來更加劇了社會的浮躁之風。
曾經看到或收到一些個人出資的書,老實說,能達到一定審美層次、可稱之為文學的書很少。不少以小說散文名義出版的書,仍停留在自說自話、渲染“勵志”、炮制“雞湯”的層面,津津樂道于與生活平行的個體生活經驗,甚至習慣于從私我情緒出發,去演繹一個個淺薄的道理。
說到底,“出書熱”的背后,乃是一種浮躁風所致。在這樣的風氣熏染下,佳作闕如,庸作充斥。這種書的“新常態”一般是,剛從印刷廠出爐,沒被拆封就直接送去造紙廠打漿。
一些出書達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一本書,沒過幾年,就能拋出七八本甚至更多本書,乃以“高產作家”“著作等身”自詡。在筆者生活的城市,不乏這樣的“作家”,他們一般都不差錢,也有寫作的夙愿和狂熱,但就真正的文學寫作而言,乃是夏蟲與冰塊的關系。他們雖然接二連三地出書,詩集、散文集、長篇小說都有,但說得“狠”一點,書出得很熱鬧,但就是與文學、文化沒半毛錢的干系。
其實,沽名釣譽也好,出人頭地也好,這些都沒問題,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少匱乏寫作才華且又不自知者,總想通過旁門左道、歪門邪道來達到目的,這就有些“功夫在詩外”了。
B
如今的文學江湖,幾成一個大醬缸。跑馬圈地者依仗手中掌握的那點權力,把這個大醬缸攪得烏煙瘴氣。一些文學機構、組織的頭頭腦腦們,將其所管轄的組織機構,比如這個協會那個研究會之類,作為沽名釣譽的載體,當成跑馬圈地的利器。一些文學組織的領導者,以及一些雖然沒有文學組織的頭銜但手頭闊綽的附庸風雅的人們,最熱衷的便是文學研討會、新書首發式、作品發布會等等。這些人心里門兒清:權力和金錢作為資本是聚攏人員、人心的發動機,文學圈里的一些人貌似清高,但難逃市儈。
可以說,現在許多作家、作品的聲名鵲起,很少能離開炒作,而且,越是有本事燒錢,就越能鬧出動靜來:動員媒體,邀請專家,組織研討,輿論轟炸,制造文化新聞,操縱網上“水軍”發貼打分,安排“粉絲”制造熱度,首發式上載歌載舞、人聲鼎沸……這一切都是緣于當事人、受益者的設計和投入,說白了就是權力或金錢在推波助瀾。
現如今,資本綁架劇本,錢權壓倒一切,其所到之處,豪氣干云,所向披靡,在文化領域里扮演越來越權威的角色。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跑馬圈地的牛人們,能讓業界領導、相關媒體以及他們所喜歡、所信任的那些居于各個階層的吹鼓手、抬轎夫等等,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地集結于自家的麾下,濟濟于殿堂。當然,免不了好吃好喝、推杯換盞,為的是之后的報刊輿論連番轟炸,為日后的評獎制造輿論、夯實基礎。
文學原本是一個高雅的事物、一個才華與智力的競賽場,勝出者是因為參賽者的才華和創造所致。現如今一些人卻在文學的名義下,在公正的名義下,進行著見不得陽光的關系疏通和運作;一些在文學江湖坐穩了艙位的權力者,打著文學的旗號,將經過偽裝了的荒誕與謬誤呈現在天真的作者和讀者眼前,精心上演著一幕幕《儒林外史》般的“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的諷刺鬧劇。
C
如今的文學江湖,儼然一個大炒鍋。作品研討會是炒作的載體之一。這些年,在研討會上,常能看到各種風格的發言者。這些發言者,都是主辦單位邀請來的,每人都有“兩把刷子”,都不是空有其名的尸位素餐者。然而,他們的表現卻是各有不同,其中有一種人,乃是打無準備之仗,臨時抱佛腳,現場草草瀏覽一下作品,隨便在紙頭上劃拉幾筆,即在眾目睽睽之下開評,高談闊論,云天霧地,言不及物,也不及義,看似侃侃而談,實乃賣弄口技。一次,在某作家作品的研討會上,一評論家弄巧成拙,明明被研討人的作品是傳統現實主義寫作,他卻說是 “現代主義手法的成功運用”。還有一次,另一評論家把一名慣于現代主義寫作的作家,說成是現實主義回歸。
現在的研討會過多、過濫,而且,越是高規格研討會,就越是“大呼隆”——半天時間,發言者可以多達三四十人,而專家發言時間非常短促,每人也就七八分鐘,根本無法對作品進行深入剖析充分評點。有關方面真的是把開研討會當成了“辦喜事”,用“冠蓋云集”形容可矣。再而且,現在的作品研討會,多是一片頌揚聲。即使出現難得的批評,媒體出于出版商、主辦方和作者等多方利益需要,往往采取過濾式報道,“好聽的”留下,“難聽的”芟夷,少有能做到將整體研討內容客觀完整地呈現。
現在的文學研討會,較之上世紀80年代的真誠、自由,已經嚴重變味。最觸目驚心的是行政化、“官場化”傾向。主辦方把官場會議的“游戲規則”完整復制,邀請領導出席,制定會議程序,精心排列座簽,安排發言次序,甚至事先寫好通稿,便于媒體宣傳。研討會例行的規矩是,第一板塊是領導講話,發言時間基本不限,往往時間耗去大半,研討還未入題;第二板塊的專家發言,也是從大到小依序進行,而發言時間則有所限定,又由于前面的領導講話已定下基調,專家只能簡略講自己的主要觀點,或臨時改變自己的見解,而不少打算發言的專家已沒有了機會;最后是作家本人談感受,他只能連說幾聲“謝謝了!”
謂予不信,不妨讀讀 《業已變味的文學研討會》(《文學自由談》,2010年第6期)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段崇軒提及他參加的一位作家作品研討會:主席臺很擁擠,有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的在職和離休領導,有數任省作協的主要負責人,有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等,密密匝匝有十多位,清一色的副廳級乃至副省級以上干部;而研討會的主角——小說作者,盡管當過省作協副主席,又是資深的一級作家,卻因不是副廳級,只得忝列主席臺末位,可大半個身子被擱在臺子之外。其實,在主席臺就坐的,有好幾位是該作家的晚輩,一直都尊稱他為“老師”,但此刻卻坐在上首——如此這般嚴格效仿“官場規則”的做法,是否有點不大合乎人情世理?是否有違“藝術民主”和“學術自由”?如此“官場化”的研討會,如此促狹的幾個小時,又能研討出什么來呢?
此種現象,借用人類學理論的表述,與其說是一種文學學術安排,毋寧說是一種典型的“身體政治”安排。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在這種“身體政治”秩序中,微觀權力早已潛移默化地滲透至活動參與者身體的每一個毛細血管,使身體全面籠罩在一個知識教化和權力干預的區域內。福柯的論述,向人們展示了社會當中的各種組織和制度都圍繞著身體展開爭斗,都對身體進行隨心所欲地規劃、擺弄。
近年來,這種散發著“身體政治”異味的文學作品研討會幾成常態,由此獲利者也不計其數,文壇儼然演變成了由主導者統治的按照一定方向發展的文學市場。君不見,某位因跑獎出名的詩人據說就是用銀子開路,用酒肉結交,從而搞定諸多專家學者,為其說好話,唱贊歌,相關作品研討會想啥時開,只消打一通電話即可安排停當。
深諳文學江湖上暗道機關的跑馬圈地者,甚至罔顧事實,有意遮蔽創作真相,東說成西,北講成南,壞說成好,好說成壞。何以如此?原因無他,就是他們手中掌握著一定的組織、管理、經費乃至話語等等權力。
與此同時,一些評論“大咖”們則時刻準備著,一旦有人召喚,他們就會樂此不疲,走南闖北。到了現場,匆匆掃上一眼作品,快速準備發言提綱,然后口若懸河如吐蓮花。一如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當有人把真實的東西當作虛幻的東西來看的時候,那虛假的東西甚至比真實的東西顯得更真實。反之亦然,把不存在的東西說成是存在的東西時,那捏造的事實甚至比存在的事實更顯得真實。所謂謊言重復一千遍也能變成真理,此之謂也。
D
如今的文學江湖,成了一個醬肉鋪。評獎標準的五花八門、混亂無序,變成供一些投機者伺機“割肉”的“問題秤”。各種各樣的評獎名目繁多,而近年來以魯迅名義命名的那個文學獎爭議不斷,詬病不輕,尤其是詩歌獎,什么羊羔體、仿古體、跑獎詩人等等,丑聞連連,疑影重重。
任何評獎,要讓所有人滿意是不可能的,絕對的公平也是難以做到的。但現在即便是相對公平,也如瞽目登山一般很難做到了。以相對嚴謹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為例,有評論者認為,它對“體制”的超越性是不夠的,沒有跨越年齡、閱歷、規則、美學表達上的全新力量。這些獲獎作家作品在消化和轉化大歷史與當代精神方面,其表現依舊是孱弱的。對格非和蘇童兩位先鋒文學代表作家的獲獎,似乎無甚異議;他們代表著一個時代,幾乎就是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言人,隨著他們的獲獎,可以說一個神話的時代結束——盡管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蘇童的《黃雀記》并非兩人作品中最出色的,但王蒙《這邊風景》的獲獎就不一樣了,爭議較大。何也?輒因《這邊風景》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年代的舊作,不僅不能體現作者的創作水平,甚至還帶有明顯“左”的硬傷——這樣的作品也能獲得“茅獎”,真不知道評委們是怎么想的?這就導出一個問題:向以嚴肅、莊重著稱的茅盾文學獎,它的標準是什么?難道不是以作品定乾坤嗎?難道是要看參評作家的資歷、作品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嗎?在我看來,與其讓《這邊風景》獲獎,不如把獎頒給同樣入圍的其他作品,比如龐貝的《無盡藏》。但何以口碑、影響俱佳的《無盡藏》,卻敵不過《這邊風景》這樣一部浩劫時期的“左”跡斑斑的舊作?人們有理由懷疑,那些曾經把最美好的評語給予《無盡藏》的評論家們,換一個場合就翻臉不認,把它剔出“茅獎”,這種做法,是否可用“虛偽”冠之?
茅盾文學獎這樣的大獎尚且如此,地方設立的各種名目的小獎就更奇葩。一次,有朋友告訴我,其所在的城市曾舉辦一個文學評獎活動,評委由該市作協各級有頭有臉的人物組成,加以省城乃至京城請來的幾名評論“大咖”。評選結果一公布,底下一片嘩然。何以故?卻原來,一等獎獲得者乃是本市一行政領導,二等獎獲得者兩名,一位是外省著名作家,另一位是作品寫得實在令人不敢恭維的初出茅廬的女作者。在之后不久的某個文學活動上,筆者無意中與一名文學雜志編輯同坐一桌,據該編輯透露,那名摘得二等獎的女作者寫作本領雖不大,但跑獎的本事不小,此人的能量,已然是“文學圈內人人皆知的半公開秘密”了。還有一事值得一提,某市有個政府機關的處長,也是個業余寫作者,一次該市文學評獎之前,這位“處座”為了能拿到獎,居然不厭其煩地逐個給每位他所能想到的有可能做評委的那些人打電話,請他們“多多關照”。后來,他果然獲得一等獎……
E
如今的文學江湖,幾成一個老虎機。一些作者辛辛苦苦寫稿應得的一點稿費,卻被不明不白地拖欠乃至“吃”掉,庶幾成為每一個作者都曾經歷過的糗事乃至噩夢。一般而論,一個“碼字工”的稿費收入,很難與企業家、藝人、權力者們相比。在此意義上,手中握有發稿權、出版權的媒體編輯及其負責人,理應將人文關懷給予那些“碼字工”群體——他們太不容易了。這些辛勤的作者,積年累月,日復一日,癡心不改,持之以恒地寫稿、著書,不管稿費是高是低,也不論稿費按時支付還是因故拖欠,甚至往往稿子見報、上雜志、被播出以后,有關媒體既不寄報刊,也不書面或口頭通知,更遑論寄來稿費。有些媒體編輯對待投稿作者的態度是,你的稿件我給你編發出來,就是很關照你了,你還指望我給你發通知、寄刊物、寄稿費?也太不知趣、太不識相了吧?
猶記得“讀研”期間,筆者不時寫點評論、小說之類,作品也偶見于報刊雜志。有一回,我有一篇八千字的評論發于一家地市級文學雜志。事后,我向責編詢問稿費,他說稿費已寄給你。我遍查不著,再問,人家就不高興了,說你再查。再查,確實沒有任何跡象可證他已將稿費寄出。于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編輯得罪他,又上門追問。當時他正在開會,為在單位領導部下一干人面前保住名譽和面子,老大不情愿地從衣袋掏出兩三張皺巴巴的十元鈔票,打發叫花子一樣,連連揮手說“快走快走,我再也不想見到你……”真是大白天見了活鬼,這話明明該我說。
還有一次,筆者一篇文章被某省雜志采用。還算不錯,雜志如期寄來,但稿費卻如泥牛入海。過約大半年,打長途電話詢問,對方答非所問道:“我父親病了。”筆者一愣,一時不知該說啥好,整個人像負罪似的:人家的父親病了,你還討什么稿費!你應趁機說上一句:稿費不要了,您就買點水果營養品,權當代表作者慰勞您的生病父親罷。但轉念一想,不對呀,明明是你當編輯的拖欠作者稿費,作者無奈之下厚著臉皮硬著頭皮向你討要,你卻搬出老爸生病這副擋箭牌,什么意思嘛?所以,筆者繼續追問:稿費到底寄出了沒有?那名編輯知道逃不掉了,只好乖乖地將稿費寄來。當然,我為此得罪下了這位編輯大人,以后再也沒有勇氣給他主政的雜志投稿。因為事情已經很清楚,再投肯定是石沉大海。
有個外省作者在一家報紙文藝副刊連載小說。小說連載結束之后近一年時間,作者都未收到稿費。懾于執行主編的發稿權,作者幾次三番小心翼翼地打電話詢問,得到的答復都是含糊其辭,最后執行主編干脆不接他的電話。作者一氣之下,將那名執行主編告到該報社紀檢監察部門,這才討回了那筆不菲的血汗錢,而那名執行主編也因此受到應得的行政處分。
實際上,作者被拖欠版稅或稿費之事由來已久,大有成為“頑疾”之勢。不少通過小型出版公司或書商出版過作品的作者,幾乎都有過“被拖欠”的經歷。深圳一作家就曾聲討北京某圖書公司拖欠其稿費,還曾就此事致信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北京市委宣傳部監察室、北京海淀區公安經偵隊、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并撰文介紹事件的來龍去脈,最終才將稿費全部追回。該作家追討稿費是通過輿論施壓途徑得以解決,但這樣例子畢竟是少數。
相比之下,有些作家為討要稿費和出版公司“對簿公堂”,則更加勞心勞力。作家閻連科幾年前也曾狀告某業務火爆的出版社,在當時引起轟動。閻連科稱,該出版社出版其長篇小說《丁莊夢》,不僅稿費遲遲未給,就連承諾捐贈艾滋病村的5萬元也沒兌現。閻連科討要稿費時,《丁莊夢》一書責編對不付款原因做出如是解釋:“(此書)題材敏感,影響到宣傳和發行。”閻連科一怒之下,委托律師向法院起訴了出版方。對于當時風頭正勁,拿下余華《兄弟》、《易中天品三國》等暢銷作品的該出版社而言,如此拖欠稿費,真是令人無語。
閻連科遭遇拖欠版稅的事件決非個案,其他一些作家也未能幸免,比如莫言、葉兆言、李銳、韓東等等,都曾有過被拖欠版稅或稿費的憋氣經歷。被拖欠稿費,幾成眾多作家“頭疼”的事情,作家魏微就說:“索債比寫作更辛苦!”
行文至此,就“江湖”一詞再啰嗦幾句。江湖,乃春秋時期道家發明的用詞,在中國文化中有多重引申含義。江湖的本意是指廣闊的江河湖泊,后衍生出與江河湖泊并無關系、亦非一個實際存在的場所。《莊子·大宗師》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指遠離朝廷與統治階層的民間,也泛指不接受當權者控制指揮和法律約束而適性所為的社會環境。在許多中國文學作品中,尤其武俠小說中,江湖則是俠客們與草莽英雄們的活動圈,有時甚至是黑社會的代稱。如今,江湖一詞已然演變成多義或特指的用語。
如今的文學江湖何以如此,真是個難解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