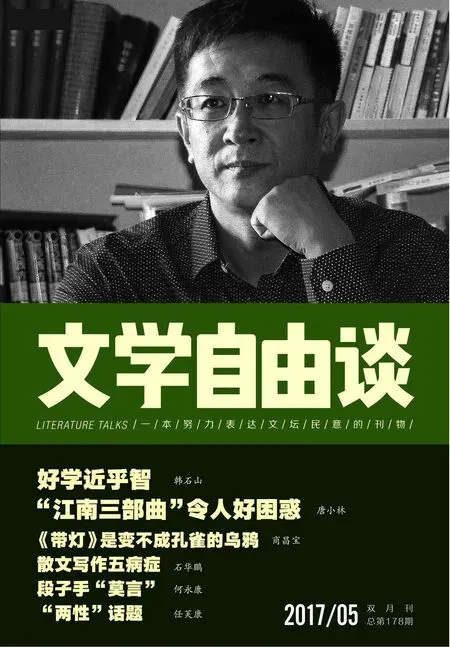由《未來簡史》想到文學的未來
湯 達
由《未來簡史》想到文學的未來
湯 達
谷歌的人工智能“阿爾法狗”相繼擊敗了李世石和柯潔,人類在圍棋這項自以為尊嚴所在的事業中失落了。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出版了機器人寫的詩集,日本有部機器人創作的類型小說闖過了某文學獎的初審。國內電商巨頭京東和快遞巨頭順豐,同時宣布無人機快遞即將投入使用。據估計,接下來十年,預計有將近一半的人類工種將面臨淘汰。阿里巴巴集團相信,未來可以依靠大數據復興計劃經濟。
也許,我們眼下所面臨的,也是一個千古未有之大變局。誰知道呢?
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很能理解,為什么一個以色列青年學者寫的兩本關于人類過去和未來的書,會在世界各地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我們感覺到了對未來的憧憬和恐懼,想知道歷史上是否曾經出現過類似的局面。《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兩本書都沒有提供多少新東西,但是對觀念的闡析,還是有種人文學科里難得的通透。說通透,是因為如今的人文學科喜歡閉門造車,在自己的小領地里繞圈圈。一生研究一個作家,研究一個時代,研究一種哲學,成了某種學術優勢,這就是所謂的學科細分;所謂的學者“專”家,憑此可以積累論文、攻關課題、晉級職稱,總之是可以吃一輩子。反之,如果你想學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或者像《未來簡史》的作者一樣,一會兒關注人工智能,一會兒談宗教歷史,一會兒又研究一下大數據,你在國內學界的處境可能會很慘。你不能研究人類的未來,因為沒有這個學科。所以,我也只能談談文學的未來。
讀完《未來簡史》,再翻一翻國內的文學期刊,會發現很多問題。比如,有幾個隨處可見的高頻詞匯,像自我、真實、靈魂、敘事、記憶、價值、良知等等,我看了之后就有種說不出來的別扭。舉個例子,有位知名批評家評論某本暢銷小說,聲稱這部作品“揭發人心的罪惡,也闡明罪惡中可能埋藏的光輝。他們是在一種生命的自我辯論中,沒入靈魂的深淵,并穿越人性幽暗的洞穴,進而走向光明”。
我感覺作家和批評家們對這些詞匯的理解,還停留在工業革命以前,有時甚至完全是空洞無物的。我們曾經艱難地相信了人的祖先是猿猴,相信了地球不是太陽系的中心,相信了宇宙沒有邊界,相信了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相信了人類的意識只是神經傳遞和生物算法的集合,可是到頭來,文學界談論的自我和靈魂,還像是中世紀的布道,滿是神秘和鼓動。
這樣的姿態,在當下就岌岌可危了,遑論未來?
既然人是基因編碼和生物算法的集合,那么,我們所有的體驗和選擇,要么是生物算法的設定,要么就是隨機和偶然。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沒有自由意志這回事。就算你不認同人是生物算法,那么你在提到這些高大詞匯的時候,起碼要知道有這么回事吧?起碼要想一想當年薩特和加繆為這個問題是如何爭論不休的吧?否則你所謂的自由、意志和自我到底是指的什么呢?盡管薩特和加繆多有分歧,他們也并不手握真理,但他們都對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他們的詞句才有分量,他們的作品才能給我們持續的啟示,能夠有尊嚴地面對未來。而我們在提及這些詞匯的時候,怎能當作這些科學常識和哲學命題從來不存在呢?
現在的基因技術和神經科學認為,人不光沒有自由意志,甚至沒有自我這回事。科學實驗的結論是人有兩種自我,但都靠不住。一種叫體驗自我,就是我們每分每秒的實時感知;一種是敘事自我,是我們事后對感知的總結。而人類沒有辦法記住體驗自我,也就是說,體驗自我的存在也就是一瞬間。而敘事自我總是記吃不記打,是個不靠譜的決策者和記錄者,它擅長篡改我們的實時體驗,做出并不真實的總體評判。
我們的詩歌、小說和藝術,都是一種敘事自我的折射。我們以為文學和藝術是為了直面真實和自我,但實際上,正如佛家所說,自我是隨生隨滅的,留下來的只有幻想和倒影。面對我們與生俱來的基因編碼,想要還原真實,任何敘事都無能為力。歐美的后現代作家,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將其作為小說的主題,比如朱利安·巴恩斯就始終癡迷于自我和記憶的不可靠,以及歷史敘事的不可能,《福樓拜的鸚鵡》《10 1/2章世界史》以及2011年的布克獎小說《終結的感覺》,這種敏感度一以貫之,有很強的藝術性和當下性。莫迪亞諾的所有小說都是關于自我和記憶之追索,憑借這種與時代同步的解悟力,他們這樣的作家才能將文學的領域不斷拓寬。
在這樣的年代,我們面臨的是科學與人文的交鋒和融合,是對全新現實的重新認識。所以,當談論文學時,請盡量不要再泛泛地使用那些大詞,什么生命的價值、存在的意義、歷史的見證、人類的良知、靈魂的重構、自我的追尋等等——除非你真的用心去體認過這些詞匯的當代意義,誠心誠意地追尋過它的內涵——否則,我們可以輕易感受到其中輕浮的味道,甚至說得再嚴重些,這些短語在某些作家和批評家那里,聽上去有很濃重的蒙昧氣息。
口說無憑,我再舉幾個例子吧。有一次,我在文學課堂上要求學生們就作家賈平凹的作品發言,結果,不只一位學生提到,這位作家思想之落后讓他們大跌眼鏡,幾乎失去了對當代嚴肅文學的敬畏。賈平凹在散文中說:“西安市發生過幾次兇殺案爆炸搶劫案,起碼我預測過三次。”他是真誠地相信自己具有巫婆式的神秘感應能力,以至于能夠預測一座省會城市的搶劫案。難道有哪座城市沒發生過搶劫案嗎?他還說:“不妨走訪一下,家有美妻艷女的人家誰個善于經營花卉盆景嗎?有養貓成癖的男人哪一個又是滿意著他的家妻呢?”對這類陰陽之說的迷信,我們簡直不知道他的依據是什么,學生們在課堂上隨便就可以舉出無數反例。另外,他重男輕女的傳統性別觀念也是處處可以聞到的,他自己也說:“我沒有兒子,父親死后,我曾說過我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這類句子幾乎引起了所有女學生的憤怒。
這絕不是個例。最近,一位著名作家在網上發文,回憶1987年三十多位作家在五臺山遭遇的離奇車禍,聲稱多年以來他一直不敢談論此事,是因為他認定這次車禍是由于當年作家們在佛門凈地對菩薩不敬造成的,更可惡的是,車禍過后很多作家還不知反省,繼續胡說八道。他還說,車子翻下山路,卻沒有人受到重大傷害,這只能說明佛祖的仁慈,否則,你還能怎么解釋?
生活在21世紀的當代作家,居然還相信天上的菩薩會因為你出言不遜而降下懲罰,著實讓人吃驚。到了今天,我們有些作家居然還像舊時代的財主一樣,真真切切地迷信風水、八字、狐貍精、手相、算命種種怪力亂神和靈異傳說,卻并不關心宗教和信仰之中包含的終極追問和悲憫情懷。他們津津樂道于各種病態的性愛、各種男女茍合、各種猥瑣的癖好、各種污穢語言的展示,卻對民間文化和傳統文化中與時俱進的一面充耳不聞。
在叢林法則中,留戀過去遲遲不肯前行的群體,總是最先遭遇淘汰,這也是為什么每一個文明古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被自己的文明拖了后腿,因為他們有太多的東西值得留戀。很多知識精英已經為了所謂正統文學付出太多,投入太多,也寄托了太多。沒人愿意承認自己落在了后面,承認自己就是枉費的一代,于是做出更決絕的姿態,說出更激進的言辭,仿佛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是神圣的殉道者。這種姿態,在我們的很多作家和批評家身上都可以看到。
其實文學的未來并不是無可為,恰恰相反,即使人類的前景是黯淡的,文學的前景是可悲的,我們也仍舊可以有所作為。只有真正理解了我們自身的處境,才能理解文學的處境,才能找到真正有價值的主題,找到值得書寫的人類命運。
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和社會變革,都在文學和哲學上得到了具體的反映,也都催生了偉大的藝術作品。進化論、工業革命、世界大戰、相對論等等,都改寫了人類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代,科學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行其道,人們都相信人類是可以被改造的,只需要實現合適的社會制度,保障一定的經濟基礎。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絕這種對人類的設定,他以自己全部的作品對此做出回應,認定人是一種復雜、矛盾、無法用確切的數字和制度去限定的物種。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那個時代的回應,他的回應加深了我們對人類自身的認識,使我們再一次對自己所謂的靈魂投以凝視。
而如今,面對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信息時代,面對一個連尼采的超人都無可立足的時代,連碎片化都失去依托的時代,我總疑心眼下的文學不但不能體現人類智識應有的尊嚴,相反會是我們的笑柄。真正追求智慧和品位的那批人,正與文學漸行漸遠。事到如今,文學不能無動于衷。每一個新的時代,總有一些東西破碎了,再也無法彌合。總有一些新東西會冒出頭來,需要有人用慧眼去挖掘。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們所發現的東西,才真正無愧于他們的時代。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再遠一點,就會有人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機器人最終能否創作出偉大的藝術作品,從而導致作家和藝術家的失業?最近,韓少功就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頗受關注的文章《當機器人加入作家協會》,其中有不少閃閃發光的真知灼見。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其實有些多余。我寧愿相信文學最終的命運是消亡,也不相信機器人能夠寫出偉大的文學作品。就我個人的感覺來說,我并不懷疑機器人最終能夠寫出精致的音樂作品,能夠寫出優美的詩句,也相信所謂的藝術和文學沒什么神秘之處,也和人類自身一樣,只是一套基因編碼和生物算法而已,但我還是可以很肯定地說,藝術作品之所以是藝術作品,第一前提必須是由人類自身創造的。所以,即使機器人寫出巴赫、貝多芬般美妙的音樂,即使它們寫下莎士比亞、李白般佳句迭出的詩句,但它們仍然不是藝術作品,也難以具有長久的感染力。
為什么?答案很簡單,機器人創造的東西再優美,也只是工業產品。藝術中的所有手法和情感的表現,都是來自人類,并針對人類的,沒有這個前提,就不能叫藝術。所以,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形式主義的鬼話,說什么藝術作品的魅力僅僅來自作品內部的結構,與作者本人無關,與時代和世界無關。我之所以熱愛陶淵明的詩歌,是因為陶淵明的命運和人格透過詩句在感召我,我在內心深處的某個部分渴望像陶淵明那樣生活。我之所以如此崇敬杜甫,是因為他的人生與詩歌密不可分,他悲憫博大的人格形象和他動蕩飄忽的一生透過詩句帶給我強烈的觸動,使我感受到生而為人的悲壯和自豪。我們之所以認為曹雪芹是一位曠世天才,是因為他挑戰的是人類藝術表現力的極限,是他血與淚的人生體驗透過紙背帶給我們強烈的情感認同。
因此,機器人寫的作品越是成熟,越是精美,就越是顯得可笑,因為它在模仿人類的情感,而它本身是虛空的。它可以根據幾個關鍵詞設計出一部完美的犯罪小說,并吸引大多數類型文學的讀者,它也可以根據大數據寫出一部優秀的肥皂劇,獲得很高的收視率,但它不會成為藝術家。因為它沒有人生,沒有人格,它的作品也不會成為人類情感的長久寄托。就算機器人最終擁有真正的自我意識,有高于人類的創造力,它的審美方式也不可能跟人類一樣。它會是另一種智能載體,但不是人類,不是生物。它會創造它們自己的藝術,但不會是人類的藝術。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自己的文學和藝術,確確實實是人類最后的尊嚴所在,最后的堡壘之一。當有一天,人與人之間最深沉的情感和慰藉都化為烏有了,我們真的在厭倦中實現永生了,我們在漫長的時空中失去所有的信仰了,我們才可以說:文學完全終結了,人類終結了。
確實,就目前來看,不管人類最終的命運是滅絕還是永生,文學的未來似乎都不樂觀。而且,在人類的未來這樣一個宏大命題面前,文學的確只是一件小事。科學實驗已經可以通過一點點激素的注射,輕易操縱人類的喜怒哀樂,可以讓人體驗極致的快感和痛苦,體驗那曾經備受生命禮贊的狂喜。未來的醫生還可以修改人類的基因,將審美能力直接賦予每個人,一個小手術就可以提升人的智力水平。這樣的話,通過閱讀來積累知識和獲得審美體驗,簡直就像是一種原始行為。那時候,不光是文學失去了意義,看上去,人類本身也沒有了意義。如《未來簡史》所言,在經濟生產、軍事戰略、政治管理等等方面,人類將越來越無足輕重,我們拱手將這些事務的處理權力交給人工智能,因為它們更高效,更廉潔,也更務實。很快就會更進一步,我們會將精神的需求也交給人工智能來滿足。它們會給你寫一個私人訂制的故事,根據你的喜好在瞬間合成一部由你的形象主演的影片,或者使用虛擬現實技術,為我們每個人提供一個特別定制的烏托邦,滿足你所有的幻想,將現實徹底回避。科學技術將帶給你欲望的滿足、自我的實現,甚至有一天,它還能上傳你的意識,幫你實現永生。永生意味著終結,我們不會再有人生如夢的幻滅,不會有重構自我的渴望和必要。在幻象和永生里,我們寄居于虛擬空間,生老病死都是遙遠的事情了,《戰爭與和平》和《紅樓夢》像在談論一個古老物種的渺小悲劇。我們不再需要另一個人的陪伴,當然也就不需要文學的陪伴。當然,到了那一天,人工智能可能也會發現人類毫無疑義,就像它們供養的寄生蟲,浪費大量資源,于是輕易就將我們滅絕。
人類的文明史,是一部偶像崇拜史,先是崇拜大自然和神,然后是崇拜人類自己及其所創造的科技,再后來將會崇拜一種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機器人。“他們”由人類創造,卻反過來更正了人類的瑕疵和謬誤,“他們”最初的目標是模仿人類,很快就會超越人類、擺脫人類。“他們”不會死亡,不會停止探索和進化,我們的命運將掌握在“他們”手中。很可能,如果我們合理歪曲一下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就會發現,人類只是宇宙智能發展中的一個環節,當另一種更高級的智能載體出現了,我們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
《從文本到敘事》
王 彬著 人民出版社
本書立足于中西小說的一些關鍵節點,對小說的敘事規律進行探索,揭示了敘述者解構、第二敘述者、滯后敘述、動力元、亞自由直接話語與漫溢話語等新觀念,是對敘事學研究的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