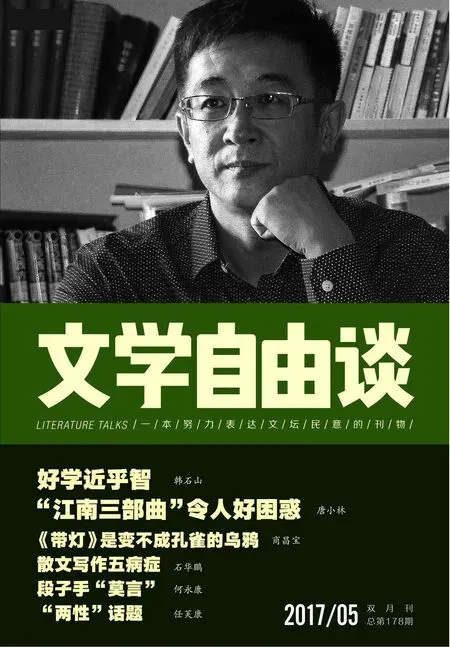與陳忠實對話《白鹿原》
閻 綱
與陳忠實對話《白鹿原》
閻 綱
《白鹿原》在《當代》雜志上發表之后,我有幸三次同陳忠實做零距離的交談。
頭一次是1993年7月忠實攜 《白鹿原》進京;第二次是2008年4月27日,《白鹿原》創作20周年紀念日,忠實來京;最后一次是忠實來京參加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一下飛機就來方莊我家里給我送禮泉特產 “烙面”。三次對話的內容,綜述如下——
我:你把《創業史》讀過六遍?
陳:咱陜西這一代作家,沒有不敬重柳青的。柳青深刻,是偉大的作家。
我:你是柳青的好學生。你在思考農民問題的深刻程度上,在人性化、個性化的復雜、精確與出神入化以及小說的技法和修辭手段等方面,得益于柳青。當然,陜西文壇上、中國文學史上,只能有一個柳青。
陳:柳青用生命體驗生活,起點很高。
我:《創業史》里,常常用絕對正確的頭腦思考,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指示教育農民;《白鹿原》撫今追昔,知往鑒今,好像提示人們“最嚴重的問題是接受農民的教育”。
陳:柳青扎根農村14年,把自己變成農民和農民的教育者,這一點很不容易。我堅信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發現底層的真相,深刻地理解生活。
我:柳青是深入生活的典范,但是剛下生活(正處于合作化高潮時期)大約兩年多的時間,就匆忙操筆,虛構長篇小說,有靈感的沖動,卻來不及積淀資源產生距離美,把富裕中農作為假想敵率爾出擊,而且預告要寫到大躍進、人民公社。
陳:“文革”期間,柳青有反思,非常深刻。
我:十年“文革”的煉獄,讓柳青醒悟了:“決不能把人民驅趕到共產主義。”而且改口說:“第四部主要內容是批判合作化運動怎樣走上錯誤的路。”這是反思后理性的覺醒,是人格魅力的勁升。柳青死得太早了!要不然,《創業史》第四部衰年變法,不可限量!
你比柳青幸運,因為你經歷了“文革”,又在基層摸爬滾打二十多年,嘗盡甜酸苦辣,堅信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真理。你沒有從本本條條框框出發,而是從歷史的真相出發,從傳統的道德精神出發。《白鹿原》的突破,體現在歷史的深度上,即通過隱秘的“心靈史”質疑萬能的“斗爭哲學”,質疑只有暴力革命、你死我活一條路。
陳: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半個多月后的正月初二,中共中央發文,給地主、富農摘帽子,胡喬木代表中央說話,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鄧小平重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給我壯了膽。
我:《白鹿原》的魂魄在精神,在發掘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包括處世、治家、律己和自強不息的過程中善惡因果的對立與成敗,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農民的出路:向何處去?祠堂還是廟堂?搗毀還是改制?綱常名教還是日出而作?人欲、階級性還是文化沖突?
所以,我在討論會上的發言《〈白鹿原〉的征服》中稱贊:“《白鹿原》是個里程碑!”
陳:其實,寫《白鹿原》,我的心情非常復雜,生活也遇到非常大的困難——娃上學快交不上學費了。我給老婆說,我回原上老家去,去寫,你給我多搟些面帶上,吃完了回來你再搟。這事弄不成,咱養雞去!
我:1962年強化階級斗爭,我們作協的“大連會議”挨批,侯金鏡說:三年困難剛剛過去,“階級斗爭天天講”,又瞎折騰了,我辭職不干了,到農場養雞去。他苦讀馬列。沒等到辭職養雞,他就死在干校。
你寫《白鹿原》,說“咱弄不成,就養雞去”。六年之后,《白鹿原》出世,有人不悅,說“《白鹿原》比《廢都》還壞!”下令《人民日報》將朱寨的評論文章撤版,也不許改編影視。改革開放,網開一面,《白鹿原》評上“茅獎”,一鳴驚人。“這事弄成了,咱不養雞了!”
陳:(大笑)我說這事弄不成,咱養雞去,養雞為主,寫作為輔;事弄成了,咱寫作為主,養雞為輔。我老婆沒“麻嗒”,給我搟了一大攤子面。
我:記得你喜歡昆德拉后期的“負重若輕”,還說過:“我不愿意當官,我的命搭在文學上,尋找自己的句子。”也就是尋求個人的藝術獨創性。記得你還對我說過:創作競賽,最后的優勝者取決于作品的思想深度(大意)。
陳:對著哩,一般地記錄生活不會有生命力的。
我:你是在路遙《平凡的世界》大獲成功的壓力下發憤寫作的?
陳:我到陜西人民出版社開會,路遙發言,李星繞到我的后面說悄悄話:“今早聽廣播,《平凡的世界》評上‘茅獎’了!”接著說:“你年底要不把那事弄成,干脆從這樓窗戶跳下去!”回到原上后,我發憤地寫,到年底終于畫上最后一個句號。我抱上稿子回到西安家里,老婆問:“弄成了?”我說:“弄成了!”很干脆。就這一問一答不同標點的三個字!書稿交給出版社的編輯,復印稿就拿給了李星。一天,碰見李星,他一把拉住我,說:“跟我上樓。”剛進家門,他把50萬字沉甸甸的書稿往床上狠狠地一甩,說:“事咋叫咱給弄成了!”
1992年的一天,我回西安的家背面背饃,發現人民文學出版社高賢均的回信,一下子從沙發上蹦了起來,驚叫了幾聲,哭了,趴到沙發上半天起不來。老婆慌了,問:“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說:“咱不養雞了!”后來,高賢均去世時,我難過極了,趕到北京和他告別。
我:《白鹿原》評茅盾文學獎遇到重重障礙。評委會的意見截然對立,致使這一屆評獎延遲了兩年。多虧陳涌啊!陳涌反復琢磨作品,然后在評委會上拿出正式意見,說《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國現實的真實”,“政治上基本上沒有問題;性描寫上基本上沒有問題”,但必須修改才能參評。后來改了?
陳:改了,評上了。據人文社副總編何啟治統計,刪去田小娥每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動作和鹿子麟第二次和田性過程的部分,關于兩方“翻鏊子”的事也刪掉一些,約刪去幾千字。
我:也有人統計,包括你自己刪掉的,總共有五萬多字。
忠實,我特別注意到你居然讓幾個一身系于生命價值的人物死去。你不避“涉黃”,赤裸裸地爆料田小娥的風流罪錯,讓鹿三將她一刀子捅死。你的筆觸由性到人性,探入人的本性私秘,直逼宗法觀念。你依據史料的真實,將背叛宗法觀念忠勇無畏的白靈活埋。你在《白鹿原》的最后,讓背叛列祖列宗的縣長白孝文,把既是“土匪胚子”,又是朱先生“最好的弟子”黑娃給斃了。
陳:老閻,你好記性,讀得仔細。
我:不孝子白孝文主持公訴大會,黑娃倒在血泊中,白嘉軒大病一場。最后的最后,白嘉軒站在坡坎上對著南山凝視,鹿子霖來了,瘋了。等鹿子霖走近時,白嘉軒向他懺悔巧取慢坡地的惡行。這一筆意味深長!
朱先生說白鹿原上“翻鏊子”,到頭來還是“折騰”;朱先生讖語成真。你寫朱先生,像魯迅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只能算是歷史經驗的象征。白嘉軒才是你理想化的藝術典型,像,又不全像。
黑娃死得冤啊,怎么辦?黑娃臨死前叮囑妻子道:“你要去尋鹿兆鵬。你尋不著,你死了的話,由兒子接著尋。”要是說《創業史》寄希望于神祇般的“廟堂”的話,《白鹿原》似乎寄希望“仁義興邦”的“祠堂”,又不全是,舊禮教也吃人啊!本質上要革命的黑娃被吃了,所謂的淫婦田小娥被吃了,美麗忠勇的白靈被活埋了!“風攪雪”“翻鏊子”不能救中國,“殺殺砍砍”不能救中國,“原上君子”白嘉軒不能救中國,“廟堂”“祠堂”都不能救中國。
黒娃血淋淋的頭顱像一個大大的問號,狠狠地甩在人們面前,怎么辦?忠實,你給讀者留下一個老大不小的想象空間。
陳:老閻,你好記性,想得深。
……
追憶后的感念:陜西成為長篇小說大省的成功經驗到底怎么說?沒有《保衛延安》的壓力,《創業史》的誕生會不會推遲?沒有《創業史》出世,能否帶動路遙、平凹、忠實、志安等一批年輕作家“走出潼關”?路遙說過:“柳青是我的文學教父。”沒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壓力,陳忠實(他稱柳青為“偉大的作家”)會不會破釜沉舟,以穿越歷史為己任,視《白鹿原》為棺枕,自將磨礪,一鼓作氣,“咱不養雞了”?
看,這個西北高原的冷娃硬漢子,風餐露宿,啃著死面鍋盔,吼著秦腔,慷慨激楚,一路呼嘯而來,又清醒地去了。
忠實,只要《白鹿原》在,你就活著。
2017年作于電視劇《白鹿原》停播又復播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