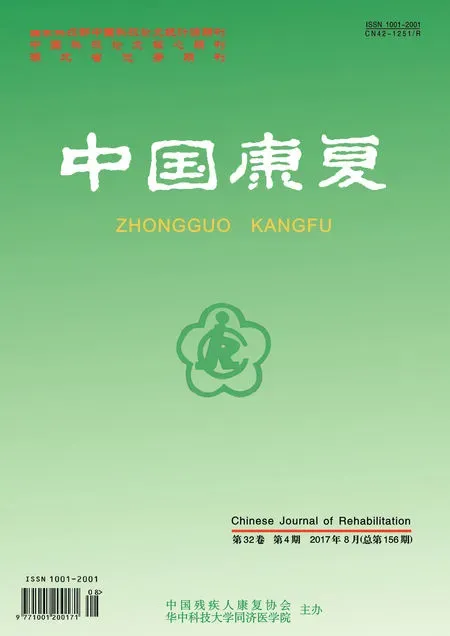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結合電刺激對腦卒中單側忽略的作用
范星月,徐若男,韓露,徐海鵬,王雪,劉波,孫婷婷
單側空間忽略(Unilateral Spatial Neglect,USN)是指對身體的一側不能感知,失去整合和利用來自于身體或環境一側的知覺的能力,常表現出對于腦損傷對側的聽覺、肢體運動、空間視覺,甚至嗅覺刺激的忽略[1-2]。此類患者甚至會在自己曾經熟悉的環境中走失,毫無防備的碰撞其忽略側的物體,有時也會對患者自身造成一定的傷害[3-5]。單側忽略是腦卒中患者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對患者的神經功能有明顯的消極影響[6-7],成為影響患者功能恢復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對入住本院康復科的60名腦卒中伴單側忽略的患者給予常規康復治療、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及反饋式功能性電刺激治療,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5年1月~2016年5月入住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康復科首次發病的60名腦卒中患者,經過凱瑟琳-波哥量表(Catherine Bergego Scale,CBS)、二等分線段、刪除試驗及臨摹圖形評定診斷伴有USN障礙,并符合以下納入標準:年齡>18歲;滿足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的最低關節活動度標準[8]:腕關節主動伸展>10°,拇指主動外展>10°,其余四指中至少兩個手指主動伸展>10°,上肢關節被動活動度肩關節屈曲/外展>90°、外旋>45°,肘關節伸展<30°,前臂旋后/前>45°;下肢功能≥BrunnstromⅢ期;站立平衡達到二級,可輔助步行10m;佩戴上夾板后能保持一定的平衡,站立位靜態平衡(可以手扶支撐物)至少維持2min,能夠自己獨立完成坐位到站立位和如廁的轉換動作,有基本的安全保證;確保有一名陪護人員,在CIMT治療期間能夠每天24h陪護;病情穩定;自愿簽訂治療協議書。排除標準:嚴重認知障礙、有藥物不能控制的問題及難于合作;肌肉嚴重萎縮;在視覺方面有明顯障礙,例如白內障、青光眼或偏盲。按隨機分組法將納入的研究對象分成2組各30例,①觀察組,男17例,女13例;年齡(53.45±2.18)歲;病程(25.05±3.56)d;腦梗死25例,腦出血5例;左側偏癱16例,右側14例。②對照組,男15例 ,女15例;年齡(52.05±2.52)歲;病程(23.85±4.08)d;腦梗死26例,腦出血4例;左側偏癱19例,右側11例。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方法 2組均給予對癥藥物支持治療及常規康復治療,對照組采用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CIMT)治療:患者的健側上肢佩戴一個舒適的夾板,以便將健側的前臂和手固定于休息位,以此來限制患者健側肢體的使用。每天清醒時帶夾板時間≥90%,每天有針對性的進行3~5個患側肢體的塑形動作訓練,塑形訓練前后、中間均進行5min的放松、牽拉活動。睡眠、洗漱或其他特殊情況時可摘下夾板。下肢CIMT訓練包括:平衡訓練、起坐訓練、單腿負重、運動平板訓練、上下樓梯等訓練。除此之外的時間都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針對性訓練,如進食、洗澡、上廁所、梳妝洗漱等日常活動。本研究采取的治療強度為2h/d,4次/周,連續6周,共48h。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增加肌電反饋式功能性電刺激(Electromyography-triggered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EMG-FES)治療:患者在接受上下肢訓練的同時進行相關肌肉的電刺激治療,主要刺激患肢的肌肉,有岡上肌、三角肌、腕背伸肌、脛骨前肌等。患者主動運動時,當檢測到的表面肌電值達到初始設定閾值時觸發1次電刺激,EMG-FES依據肌肉收縮的強度和持續的時間,實時準確地調節輸出電刺激脈沖的電流強弱和持續時間,幫助患肢完成最大程度的關節活動[9]。配合作業治療和運動療法的治療,上下肢各1次,20min/次,6d/周。
1.3 評定標準 由同一治療師分別于治療前、后對2組患者進行單側忽略程度、肢體運動功能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偏側忽略情況的評估。①單側空間忽略程度評測:采用二等分線段試驗、刪除試驗(Albert測驗)、臨摹圖形試驗,其中任何一項試驗陽性即歸為有單側空間忽略。二等分線段:3條長度不等(5cm、7.5cm、10cm)的直線,要求受試者目測標記出中點,計算平均偏離百分數,>10%為異常。刪除試驗(Albert測驗)[10]:40條線段隨機分布在B5紙上,要求受試者在所有線段上用筆畫一條刪除線,沒有被刪除掉的線段偏于一側則為異常。臨摹圖形試驗:臨摹幾何圖形,人像及空心十字等,未完成的部分偏向一側為異常。依照石合氏報道的確定單側忽略程度的方法[11],無忽略:以上3項測評試驗均為陰性;輕度忽略:僅1項為陽性;中度忽略:有2 項為陽性;重度忽略:3 項均為陽性。治療6周后,對兩組進行療效評估,以上3項均顯示陰性為痊愈, 3項均顯示有改善為顯效,1項或2項顯示改善為有效;3項均無改善為無效。②簡式Fugl-Meyer運動功能量表(Fugl-Meyer Motor Assessment,FMA):評定患者的運動功能。包括上肢運動功能評定(共66分)和下肢運動功能評定(共34分)。 ③凱瑟琳-波哥量表(Catherine Bergego Scale,CBS)[12]:用于腦卒中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偏側忽略情況的評估。CBS評分包括穿衣、洗漱、吃飯、交流、轉移等10個與日常生活活動密切相關的項目,每一項的評分用0~3分四個等級表示USN程度(0分:無;1分:輕度;2分:中度;3分:重度),總分30分。

2 結果
2.1 2組患者治療前后單側忽略程度比較 ①2組患者治療前、后單側忽略程度的比較:治療6周后,2組患者單側忽略程度較治療前均有所減輕(均P<0.05),且觀察組患者單側忽略癥狀改善程度較對照組顯著(P<0.05)。②2組患者的治療效果比較:治療6周后,觀察組總有效率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1,2。

表1 2組治療前后單側忽略程度比較 例(%)
2組與治療前比較,均P<0.05;治療后觀察組與對照組比較,P<0.05

表2 2組治療后USN療效比較 例(%)
與對照組比較,aP<0.05
2.2 2組患者治療前后上、下肢FMA評分比較 治療6周后,2組的FMA評分明顯優于治療前(均P<0.05,0.01),且觀察組的上下肢FMA評分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3。

表3 2組治療前后上、下肢FMA評分比較 分,
與治療前比較,aP<0.01,bP<0.05;與對照組比較,cP<0.05
2.3 2組患者治療前后CBS評分比較 治療6周后,2組的CBS評分明顯優于治療前(均P<0.01),且觀察組的CBS評分明顯優于對照組(均P<0.01)。見表4。

表4 2組治療前后CBS評分比較 分,
與治療前比較,aP<0.01;與對照組比較,bP<0.01
3 討論
USN是腦組織受損后在感覺性輸入和運動性輸出的緊密關系中產生的[13],是一種復雜的認識功能障礙,患者對一側空間或是有意義的刺激不能做出正確的反應和定向,其病因、病機目前尚無明確定論,在康復治療方面也面臨著諸多挑戰[14]。有研究表明,通過適度加強肢體感覺運動功能的參與可增強視覺的感受,患肢在忽略側空間主動運動,可以有效的緩解USN癥狀[15]。現有研究證實[13],單側忽略癥狀是可逆的,在康復訓練過程中,采用的主要措施是強化患側,即便患者基本的感覺已受損,但是當其注意力被吸引到忽略側,感受到外界的刺激時,便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CIMT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為的限制患者的健肢使用,強化和重復使用患肢的一種康復訓練方法,能夠促進患側肢體運動功能最大程度的恢復[16]。感覺和運動是人體兩項密不可分的重要功能,Valerie等[17]提出,限制健側肢體活動,重復和強化訓練忽略側肢體,可幫助喚醒患者對感覺刺激的反應,增強右側半球額葉的警覺性。有報道顯示,CIMT對改善單側忽略效果明顯[18],通過CIMT對單側忽略患者進行感覺運動一致可塑性主動刺激,和多種想象空間、感覺整合有關的大腦功能活動,可改善忽略癥狀且持續更長時間。單側忽略患者通過CIMT訓練,能夠將在康復訓練中所掌握的運動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并強化了患肢的使用意識,克服習得性廢用[19]。
EMG-FES在神經肌肉電刺激的基礎上,添加了實時肌電反饋刺激功能,依靠表面肌電采集生物反饋信號,讓治療者參與到自主控制的運動訓練模式[9],不僅強化了患側的肢體功能,同時也有利于大腦皮層運動區功能的修復與重建[20-21]。EMG-FES通過患者主動收縮肌肉產生的肌電信號激發電刺激,將自主運動、本體感覺反饋及電刺激三者有效結合[22],本體感覺反饋使患者意識到忽略側肢體肌肉的收縮,進而在電刺激的作用下完成動作,促進受抑制的神經通路的開通,挖掘部分殘留的神經肌肉組織的潛能,有利于忽略側軀體感覺功能重組,使患者的運動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復[23-24]。而且大腦獲得正確的關節運動感覺及肌肉收縮信號沖動反饋,同樣有利于激活被封閉的神經通路和腦功能的重建[25],促進腦卒中患者USN癥狀的改善,對腦卒中患者的康復治療起到了積極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患者經治療后USN評價、FMA評分均優于治療前(P<0.05),表明常規的康復治療結合CIMT能夠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肢體運動功能和改善USN癥狀。觀察組患者經治療后USN評價、FMA評分均明顯優于治療前(P<0.05),且優于對照組(P<0.05)。綜上所述,常規的康復治療結合強制性使用療法和肌電反饋式功能性電刺激治療腦卒中后單側忽略,不僅能有效提高患者主動參與的意識和康復信心,更有利于提高腦卒中偏癱患者的肢體運動功能、改善單側忽略癥狀及促進日常生活能力的進一步恢復。但本研究入選病例較少,未對發病部位、性質等進行分組研究,缺乏對長期療效的觀察,有待于繼續研究。
[1] 范虹, 馮玲. 針刺在腦卒中后單側空間忽略康復中的療效觀察[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5, 30(10): 1017-1020.
[2] Goldman Bennett. 王賢才譯. 西氏內科學神經系統疾病分冊[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3: 56-57.
[3] Bartolomeo P, Chokron S. Handbook of neuropsychology[M]. (2nd).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2001: 67-98.
[4] 王薌斌, 陳曉春, 宋為群. 經顱磁刺激技術治療偏側忽略的研究進展[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05, 20(9): 715-718.
[5] 徐倩, 霍速, 宋為群. 聽覺空間忽略研究進展[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08, 23(6): 574-576.
[6] Jehkonen M, Laihosalo M, Kettunen JE. Impact of neglect on functional outcome after stroke: a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recent research findings[J]. Restorative Neurology & Neuroscience, 2006, 24(4-6): 209-215.
[7] 林遠, 伊長松. 腦出血所致半側空間忽略對偏癱康復預后的影響[J]. 現代預防醫學, 2012, 39(7): 1696-1697.
[8] 甕長水, 王軍, 潘小燕. 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在最低上肢運動標準慢性腦卒中偏癱患者中的療效[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07, 22(9): 772-775.
[9] 宋小慧, 謝青. 肌電反饋功能性電刺激治療急性期腦梗死手功能障礙的臨床研究[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5, 30(6): 538-541.
[10]何靜杰, 王曉艷, 張小年. 重度半側空間忽略癥的臨床分析(附5例臨床病案分析)[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07, 13(4): 374-376.
[11]范虹, 馮玲. 針刺在腦卒中后單側空間忽略康復中的療效觀察[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5, 30(10): 1017-1020.
[12]范晶晶, 何婷, 胡迪群, 等. 腦卒中單側忽略功能性評定研究進展[J]. 華西醫學, 2015, 30(12): 2368-2372.
[13]張明明, 劉文平. 腦卒中后發生單側空間忽略的評測及康復干預[J]. 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6, 36(4): 857-858.
[14]季力, 崔曉. 腦卒中后單側忽略的康復治療進展[J]. 神經病學與神經康復學雜志, 2014, 11(2): 58-60.
[15]于兌生, 惲曉平. 運動療法與作業療法[M].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2: 408-409.
[16]劉永平, 王文清, 程子輝, 等. 改良和傳統強制性運動療法對腦卒中偏癱患者上肢運動功能療效的臨床觀察[J]. 臨床與實驗醫學雜志, 2011, 10(6): 404-406.
[17]Valerie B, Robin W, Chris G, et al. Limb activatio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unilateral neglect: evidence of task-spceific[J]. Neurocase, 1999, 5(2): 129-142.
[18]林克忠, 洪啟宗. 修正式強制性使用運動療法對中風病人功能恢復與皮質重組成效的隨機臨床試驗[C]. 2005國際作業治療研討會, 2005, 9, 31-32.
[19]楊雷, 朱潔, 王傳杰. 強制性運動療法結合電刺激對偏癱患者上肢功能的作用[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5, 30(3): 285-286.
[20]李明芬, 賈杰, 劉燁, 等. 神經反饋康復訓練對腦卒中患者上肢運動功能的作用[J]. 按摩與康復醫學, 2013, 11(1): 11-14.
[21]Steinle B, Corbaley J. 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a new horizon[J]. Missouri Medicine, 2011, 108(108): 284-288.
[22]Hara Y. Neurorehabilitation with new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or hemiparetic upper extremity in stroke patients[J]. Journal of Nippon Medical School, 2008, 75(1): 4-14.
[23]Doyle S, Fasoli SE, Mckenna KT. Interventions for sensory impairment in the upper limb after stroke[J].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0, 22(6): 702-716.
[24]Casadio M, Morasso P, Sanguineti V, et al. Minimallyassistiverobottrainingforproprioceptionenhancement[J]. ExpBrainRes, 2009, 194(2): 219-231.
[25]梁天佳, 吳小平, 莫明玉, 等. 上肢康復機器人在腦卒中單側空間忽略康復中的作用[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2, 18(4): 369-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