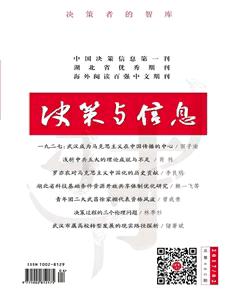羅亦農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貢獻
李良明
[摘 要] 1927年7月至1928年4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羅亦農在武漢工作,先后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中共長江局書記。雖然羅亦農在湖北武漢工作的時間不長,僅近10個月,但在這段時期,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批判共產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抵制“左”傾盲動主義,在黨內最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理論觀點,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 羅亦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武漢;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7)02-0032-12
羅亦農(1902-1928),湖南湘潭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7月17日,他接替張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8月7日,出席中共“八七”緊急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9日又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30日,羅亦農調任中共長江局書記。長江局管轄范圍為鄂、湘、豫、贛、川、皖、陜7省。1928年4月2日,任弼時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要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周恩來、黃平立即去莫斯科籌備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示。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出賣,羅亦農不幸在上海英租界被捕,4月21日,他英勇犧牲于上海龍華。
羅亦農在湖北武漢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僅近10個月,但在這段時期,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批判共產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抵制“左”傾盲動主義,在黨內最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理論觀點,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
繼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又在武漢實行“分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革命終歸失敗。“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1] 1036。為了挽救中國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
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看,這次會議的召開,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和決定的。“‘八七會議召開的真實原因,一是為了必須盡快糾正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錯誤,說明共產國際執委會方針的正確性;二是統一中共中央領導和全體黨員的思想,承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只能由中共中央前領導者陳獨秀負責,不能讓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承擔失敗的責任”[2]。
“八七”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首先作報告。會前,羅米那茲親自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并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所接受。這是大會的主要文件。他開門見山便打出共產國際的招牌,反復強調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指導“是正確的和毋庸置疑的”。在結論部分,羅米那茲更是強調指出:“共產國際嚴厲批評我們黨的中央客觀上出賣革命的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承認這一批評完全是應該的,并且承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于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最近的指示,給我們以發現這種過去指導錯誤之可能,救了我們的黨,是非常之好的。”[3]
羅米那茲還特別強調,討論中國大革命的問題,全黨及每一個黨員,都要“堅決的站在列寧主義及共產國際的理論上來分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及這封信(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筆者)便是討論的根據”[3]。這就為“八七”會議定了基本調子。
緊接著,瞿秋白代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報告。他在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時說,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我們的黨缺乏平民的精神”[4] 1。又說:“現在事實已經證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我們再不能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的。”[4] 1他強調:“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4] 3瞿秋白還批評了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明確指出:“羅易給電報與汪(精衛)看自然是錯誤的,給了汪以反臉的口實。”[4] 2
原來,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在決議送達中國前,先將4個要點電告駐中國代表羅易。即一、改造國民黨,使大批工農分子參加進去;二、把農民協會變成村政權;三、組織7萬軍隊,其中要包括2萬共產黨員;四、沒收土地,實行土地革命。這4點意見,反映了斯大林當時的思想。羅易收到電報后,未經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和共產國際其他代表同意,于6月5日即向汪精衛出示該指示,第二天又送給汪精衛一個電報副本。結果,這4點“五月指示”,成了汪精衛發動“分共”的“重要依據”[4] 5。
從《“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記錄》看,出席這次會議的兩個湖南人——毛澤東和羅亦農,在會上的發言相當精彩。
毛澤東在肯定羅米那茲的報告“全部是很重要的”后,重點講了4個問題:第一,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第二,農民問題;第三,軍事問題;第四,組織問題。尤其在講軍事問題時,毛澤東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5] 47。這句話,后來演變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武裝斗爭方面的重要創新理論。
羅亦農在“八七”會議上也發表了重要講話,充分展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第一,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與階級斗爭的理論,分析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批評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影射了聯共(布)與共產國際。
羅亦農在發言中指出:“中央對于各種運動無一堅定的策略。我時常有這樣一個感覺:中國共產黨無一堅決奪取政權的決心,我意黨的機會主義根本出發于此。第五次大會(指黨的‘五大——筆者)以前黨對大資產階級估量太高,大會時對小資產階級估量太高,所以對國民黨看得太高。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所以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6] 317“無一堅決奪取政權的決心”“對國民黨看得太高”、黨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批評得痛快、深刻,一語中的。從表面文字看,羅亦農是在批判陳獨秀,實際上影射的是聯共(布)與共產國際。因為正是聯共(布)與共產國際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的政策影響了中共中央,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正是來自共產國際。
第二,公開批評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錯誤指導。
這是最吸引讀者眼球的文字,體現了羅亦農堅持真理、尊重歷史的求實精神。他旗幟鮮明地說:“大家都說國際是無錯誤的,我要公開的批評國際:國際的政治指導不成問題,是對的,但在技術工作問題非常之壞。既認中國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時又派魏(維)金斯基、羅易來指導,他們都是無俄國革命經驗的。魏(維)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黨,我們在上海要暴動時他要反對,并且不幫助。至于羅易,誰也知道是國際犯了左派理論幼稚病的人,這種人如何能指導中國的革命。國際決議是好的,但派來的人不好,使人不滿意。這是國際要負責任的。”[6] 317-318
如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大多解密。現在看得很清楚,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有不少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揮……維經斯基后來承認:‘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鮑羅廷也認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未能集中力量打擊蔣介石,是‘當時我們在中國所犯的最致命的一個大錯誤”[7] 222。
在“八七”會議上,在羅米那茲要求中共中央和全體黨員承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于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討論中國大革命的問題只能以告全黨黨員書為根據的背景下,羅亦農居然“要公開的批評國際”。雖然他也肯定了國際的政治指導“不成問題,是對的”“決議是好的,但派來的人不好”。其實,維經斯基、羅易等都是在中國忠實執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路線的,遠在中國千里之外的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不了解中國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在莫斯科發出的許多指示,都是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維經斯基和羅易的錯誤,都來自聯共(布)與共產國際。羅亦農對他倆的批評,就是對聯共(布)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批評。這在當時是需要理論勇氣的,對于破除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迷信、解放思想、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第三,總結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
羅亦農說:“此外我還有一點意見,在告同志書中應加一點:指出過去黨是不能爭斗的,這是在組織上的錯誤。還有一個問題,即是黨的指導的問題……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說:要將群眾意識來作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領導,這是很好的。”[6] 318他在“八七”會議上提出這些寶貴意見不是偶然的。早在中共四大前后,包括羅亦農在內的一批中共早期領導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這個思想,包括對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以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革命動力、革命對象、革命任務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認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這些基本認識,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論述無產階級領導權時,羅亦農明確指出:“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非無產階級去指導不可。”他還說:“擔負國民革命的只有無產階級,故中國共產黨要積極指導國民黨。就是我們要利用現實的政治,以決定戰略,不能采取清高的政策。”[6] 31然而,由于聯共(布)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因此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根本無法實現。羅亦農在“八七”會議上指出黨的組織上“不能爭斗”“要將群眾意識來作為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領導”,其實質,就是強調要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來指導中國革命。
二
“八七”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確立了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開始了黨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1] 957。
這是一個需要英雄而又英雄輩出的年代。正是在“八七”會議精神的指引下,包括羅亦農在內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批精英,英勇無畏,心懷遠大理想,投入到新的戰斗中。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應該怎么走的問題這時還沒有解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至大革命失敗前,黨主要學習蘇聯的革命經驗,在城市領導工人運動,進行北伐戰爭,走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由于歷史的貫性作用,革命道路問題在“八七”會議上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羅亦農走馬上任挑起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的重擔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其時,在省委中工作的人只有50多個,黨的組織“非常之弱”[6] 320。1927年7月23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宣布國民黨容共政策之經過。羅亦農認為,汪精衛的用意是“以改良主義為根本,使C.P失掉一切群眾,然后進行殺戮C.P”。于是,“省委即決取進攻的政策”[6] 320,不僅預備了一個武漢工人總同盟罷工的計劃,還擬定了湖北秋收暴動計劃。這個計劃,確定湖北的秋收暴動,應以鄂北地區暴動為中心。
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強調湖北秋收暴動的任務,是從政治上擾亂武漢國民黨的統治,牽制其對江西的壓迫,在經濟上抗租、抗稅、抗捐、抗糧,加深武漢政府的經濟困難,使湘北與鄂南連成一片。中央的意圖很明顯,就是以湖北暴動策應南昌暴動并呼應湖南秋收暴動。根據中央指示精神,8月5日,湖北省委制定了《鄂南農民暴動計劃》,將湖北秋收暴動以鄂北為重點改為以鄂南為中心,并積極實施這一計劃。
《鄂南農民暴動計劃》確定在鄂南區域內蒲圻(現為赤壁——筆者)、咸寧、通城、崇陽、通山、嘉魚、武昌(城與郊在外)舉行暴動,“以蒲圻、咸寧兩縣為中心和發難地,創成整個鄂南的暴動局面”。暴動成功之后,各縣、市組織革命委員會行使政權職能。暴動隊伍的任務是:先取得蒲圻、咸寧兩座縣城,再取嘉魚、崇陽、通城、通山等4縣,在“客觀可能時,則須直接威嚇武漢,或進攻岳州,威嚇長沙”“如萬不得已時,亦須至通山、通城一帶上山”[8] 49-51。暴動日期定在9月1日至5日之間。這個暴動計劃,是符合“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策略精神的。按照中央的策略,“暴動以兩湖為中心(因為湖南的農運比較有基礎),暴動時先取得兩湖中心的武(昌)長(沙)鐵路,取得岳州,長沙,斷絕兩湖關系,動搖湖南政權,完成湖南暴動,再聯廣東取湖北”[6] 354。這表明,“八七”會議后,黨中央的指導思想的確存在盲動主義傾向,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羈絆。
1927年8月20日前后,羅亦農和湖北省委常委任旭到鄂南指導工作。他們召集鄂南各縣負責同志開展會議,加緊從各方面準備暴動。
在羅亦農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下,從1927年8月中旬開始,鄂南各縣的秋收暴動序幕便徐徐拉開。然而,由于敵人力量過于強大,鄂南暴動最終失敗。武漢八二總同盟罷工也受到慘重損失。
鄂南暴動和武漢八二總同盟罷工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在工農群眾中的影響力和組織力,但畢竟革命已轉入低潮。
羅亦農是位尊重實際、一切從革命實際出發的革命家。他從鄂南暴動和武漢八二總同盟罷工的失敗中認識到,全省總的暴動時期“已經暫時過去,目前的工作是準備最近的將來全省有組織的暴動”[6] 333。雖然這里仍有“暴動”的字眼,但其本意卻是強調暴動時期已經過去,革命形勢已轉入了低潮,應“準備”去迎接全省新的革命高潮。基于這種認識,在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時,羅亦農堅決反對左傾盲動主義,反對在南京政府討伐武漢唐生智的寧漢戰爭期間舉行武漢總暴動的計劃。
第一,正確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形勢。
羅亦農在《目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指出,廣州起義和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革命是永久的失敗了。革命如果永久失敗,必定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敵人的政權鞏固;第二,敵人能夠改良工農的生活”[6] 356。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權,在廣東、東南和兩湖,都是新軍閥、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統治,他們之間的矛盾更加激烈,使得工人失業、商店關門,工人工資減少,物價提高,農民破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任何人來都沒有辦法可以維持現狀,更說不上改良工農的生活”“這種情形,必然要使革命猛烈向前發展”[6] 357。這與毛澤東的認識完全一致。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之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9] 47因此,引起中國革命的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9] 48。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新的高潮快要到來。這說明這個時期羅亦農與毛澤東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制定了黨的正確革命策略。
羅亦農清醒地認識到,雖然中國革命的潮流必然繼續向前發展,黨的策略依舊是照著暴動的路上走,“但不是馬上暴動”。“對于如何暴動的問題,必須切實注意”[6] 357-358。因此,他堅定地說:“長江局認為目前本黨策略上主要的責任,是繼續廣東未失敗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積極領導工農以及一般的勞苦群眾反新軍閥戰爭,聚集與擴大工農群眾的力量,加緊一般的勞苦群眾的政治宣傳,加緊鄉村中土地革命之發展,創造一新的革命大潮,準備一奪取政權的總暴動,但目前絕非繼續總的暴動時期。”[6] 365根據這一革命的總策略,羅亦農規定了長江局的工作任務:“第一個最大任務便是堅決的發展土地革命……長江局必須領導所屬黨部堅決的執行這項工作,同時,并須特別努力建立與發展這項工作。”“第二個大的任務便是發展所屬范圍內之職工運動(特別是武漢三鎮)。目前主要的工作為:發展經濟斗爭,建立秘密工會與工農革命奪取政權之宣傳。”“第三個最大任務便是改造所屬各級黨部……長江局負責同志須不斷的巡行各地,實際指導各地工作。在黨的內部工作須特別注意黨內干部之培養與從黨員群眾中提拔負責同志工作。”[6] 329-330這是完全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實際的,是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在中國的具體化。
第三,制止了毫無勝利希望的武漢暴動。
1927年10月14日,羅亦農去湖南巡視工作。10月25日,他在長沙得知南京與武漢發生沖突,即國民黨新軍閥為爭奪中央權力和地盤,爆發了南京政府討伐武漢唐生智的寧漢戰爭。由于武漢內部空虛、力量薄弱,中共中央認為:“寧漢戰爭有第二次發動工農群眾整個的暴動奪取政權的可能。”于是指令兩湖省委“立即召集省委會議,仔細討論如何實現這一可能”,要“堅決的勇敢的準備”[10]。
26日,湖北省舉行第八次常委會,任旭、汪澤楷、林育南、劉昌群、黃五一等常委出席會議,一致認為唐生智的潰敗很快就會到來,整個湖北有由局部騷動達到武漢暴動奪取政權的可能。會上通過了《目前緊急斗爭決議案》,決定利用軍閥混亂的有利時機,立即發動城鄉特別是武漢三鎮的武裝暴動。團省委還向常委會提出了事先集中、補充、分配武裝,組織宣傳隊,趕印并頒發傳單等問題,省委也當即通過。此時“大部分武漢同志,莫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暴動的空氣極為深厚,并有認為馬上就要暴動的,省委各同志莫不竭盡全力準備大暴動的到來”[11] 38。
正當湖北省委緊鑼密鼓準備武漢暴動時,10月28日,羅亦農回到漢口。任旭、陳喬年馬上向羅亦農報告說:“有許多同志即主張舉行暴動,你的意見如何?”
羅亦農回答說:“現在情形尚不清晰,須情形熟悉與各同志談過之后,再開一次長江局會議,才能決定。”他還笑著說:“我離開漢口不過十多天,我們主觀的力量就可以武裝奪取政權嗎?”[6] 374
當晚8時,羅亦農主持召開湖北省委常委會。他根據巡視湖南的實際情況說:“黨的主觀力量和技術準備嚴重不足,現在首要的工作是切實加緊農村游擊戰爭和割據局面的部署、恢復城市工人組織、集聚和壯大革命力量,是準備暴動而不是立即暴動。”因此,對馬上舉行武漢暴動堅決反對。
共青團長江局書記劉昌群說:“黨應堅決的決定在唐生智倒臺時要群眾起來暴動奪取政權的政策,均應照這總的策略為出發點。”
羅亦農回答說:“我們不要過于把敵人的力量估量太低,我們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發生冒險主義的行動。”暴動不是開玩笑,不能隨便決定的。“是否馬上即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尚待討論”[6] 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