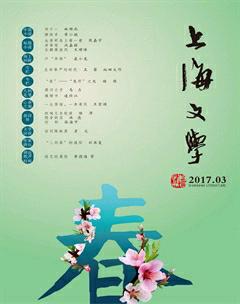盧“華僑”
裘小龍
回想起來,這是在我潛意識里糾纏了好多年的故事。從頭到底講出來,或許對自己也會有些幫助,就像人們去心理分析診所。
這故事講的是盧,我綽號叫“華僑”的朋友。盧原先住在延安路近盛澤路的拐角上,與他父母親一起擠在小閣樓里,離我家只有幾分鐘路,但他有時也去山東路靠近寧海路的寶康里,那是他姐姐家,也很近。
1966年,我的中學時代與“文革”同一年開始。我父親的階級成分是資本家,因而得接受革命大批判,脖子上還要掛一塊“牛鬼蛇神”的黑板。黑色的陰影也籠罩了整個家庭。在“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滾滾浪濤中,我喘不過氣來,幾乎都快被淹沒了。滿懷自卑情結,我低著頭進了躍進中學。那些日子里,我們盛澤居委中的同屆年輕人都去同一個中學,盧成了我同學,很快還成了朋友。
這也許是很自然的事。1949年前,我父親開香精廠,他父親經營皮貨店;1966年的夏天,在“紅衛兵”的抄“四舊”運動中,他家與我家都給“抄家”了。作為“狗崽子”,我們都在學校里受到歧視、欺負。一丘之貉吧。
我打算夾起尾巴老老實實做人,盧卻截然不同,他依舊把頭抬得高高的,頭發上還涂了亮錚錚的發油。人們叫他“狗崽子”,他卻挑釁似的“晃動尾巴”。他還逢人公開說,他來自“好人家”,驕傲地稱他父親——外國名字“路德威奇”——當年是上海灘的“白狐貍皮大王”。我可是做夢都不敢想去對人吹噓說我父親是滬上“第一鼻子”,雖然這外號在解放前好像還真流傳過,據我母親說,他鑒別香精成分的嗅覺能力相當出眾。更有甚者,盧居然還刻意培養“腐朽的資產階級趣味”,在家里煮咖啡,拌水果沙拉,上學時穿一件用他父親的舊西裝改的夾克衫,他更特地說明,這料子來自意大利。
他因此獲得了“華僑”綽號。那些日子里,“華僑”無疑是個負能量詞,通常用來說一個人不愛國,為了錢和享受居留國外,因此與西方世界的腐朽、奢侈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聯系到了一起。
在學校里,還有一件意外的事使他的綽號廣為流傳。我們那時的課本是《毛主席語錄》,其他書都屬于政治不正確。當時《人民日報》上有一篇報道,說著名作家郭沫若宣布他在“文革”前寫的書都是“毒草”,必須銷毀。難以計數的書在廣庭大眾中燒了,圖書館全都關門,不過,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卻仍難免對“毒草”感興趣,還想方設法地找來偷偷讀,有時甚至套著“毛選”的紅封套讀。
中學的第二年,我從我表哥那里搞到狄更斯的《艱難時世》。我通宵讀完了,借給盧,條件是他在一天之內必須還我。為此他那天逃學了。學校“工宣隊”的張師傅晚上意外地家訪,看到盧正在攤開的小說旁打瞌睡。盧看來難逃一劫,只能認罪,老實交代他怎樣得到了這本書。
但盧確實與眾不同,臨時滔滔不絕發揮了一通,“哦,我今天下午碰巧在廢品回收站看到這本書。我好奇地翻開譯者前言,讀到馬克思的一段話,說包括狄更斯在內的‘現代英國的一派出色的小說家,以他們那明白曉暢和令人感動的描寫,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作的還多。所以我想我也應該學習。”
張師傅把盧手指的馬克思語錄讀了兩三遍,什么話都說不上來。
“廢品回收站還有好幾本呢,”盧繼續說,“要是你現在趕過去,說不定還找得到。”
這也許是真的,但誰也無法保證現在還有書留在那里。
“但這本小說不是讓你讀的。你這無可救藥的‘華僑!”張師傅肯定也聽說過盧的綽號。
那天晚上,《艱難時世》被沒收了,但盧沒受到其他處罰。
那也救了我。我對盧表達感激之意,他絲毫沒有居功的樣子。
“要是我對張師傅說了實話,這給大家都會帶來災難。延安中學的一個學生碰到相同的情況只會哭,結果因‘非法地下交流禁書罪,被關了好幾天,連他家里人都要跟著寫檢討。”
在《艱難時世》事件后不久,全國開展了“上山下鄉”運動。人們在大街上敲鑼打鼓,慶祝這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運動。我們當時距初中畢業還有一年時間,也走上街頭,高呼口號歡送那些汽車里戴大紅花的知識青年,或涌入上海北火車站,向漸漸駛離的列車致敬,聽汽笛劃過在歡呼聲中抖動的天際……
盧又一次作出與眾不同的解讀,把一片小石子踢回鐵道路基。“知識青年?開什么國際玩笑!在學校里我們什么都沒學。貧下中農又能給什么再教育?”
又一個這樣的下午,我們目送一車知識青年駛向漸漸黯淡的地平線,沉默了。很快,我們自己也要像他們那樣離開上海。盧拖著腳步與我一起走出空寂下來的車站,咕噥著說了一聲,“走,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你說什么?”
“上海這許多好吃的東西,我們還能吃多久?”
他什么都不用多說了。在那些貧窮、落后的村莊里,知識青年每天甚至都吃不飽。盧的哥哥同慶一年多前去了安徽農村,按他的說法,他在公社的田里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到頭算下來只分到一堆紅薯干。盧因此要把握住所剩的時間,盡可能地享受這城市中的美好生活。
不過,我們口袋中的錢少得可憐,大多數時間只是在些老字號餐館的櫥窗外轉圈、想像,偶爾才踏進家便宜的小店。又一次,盧對我這唯一的聽眾開講他的盧氏學說,怎樣在舊日好時光的記憶中欣賞上海美食。他不辭辛苦地挖掘出那些餐館原先的名字。一家在南京路上的面包房在“文革”中叫“工農兵”,意思或許是面包房也首先要為勞動人民服務。但在盧看來,這樣一個名字絲毫都不能增加對店中食品的美好聯想。于是他大談特談這面包房在“文革”前的德國名字,“凱司令”,仿佛這樣一來就在口味上帶來本質上的不同。
兩三個星期后,我們另一個同學唐和盧還有我,一起雄心勃勃地去城隍廟,要在一天內“掃平”那里大約二十多家小吃店。我們事先籌劃討論再三,決定把錢湊在一起,分享老上海的每一種美味——每人只嘗一小口:雞鴨血湯、蘿卜糕、蝦肉餛飩、牛肉湯、小籠包、面筋百頁單檔……可這戰役沒進行到一半,“共同基金”就已告罄,我們只能黯然撤退。不知道什么原因,唐后來再不與我們來往,但城隍廟那次美食探險記憶卻從未褪色。
沒太久,果真就輪到我們自己去“上山下鄉”了。盡管盧在私底下埋怨,也只得離開上海去了安徽,與他哥哥同慶一起插隊落戶。
說不上是走運或不走運,我那時正患急性氣管炎,這給了我現成的借口,可以在城里留一段時間。自然,這只是等待分配,身體恢復健康后,還是要與其他人一樣去農村。于是我成了“待分配”——那個年代鑄造的又一個新詞。
困難而漫長的一段日子開始了。我不再去學校,卻沒有工作,同學和朋友都已離去,在遙遠的山上或鄉下。我孤身一人在上海,看不到那條等待的隧道的盡頭,看不到光。
可不到兩個月時間,盧卻回到了上海,皮膚稍顯曬黑,也瘦了些,但其他方面不見任何改變。
“真是荒誕,”盧對我說,手里捧一小袋從安徽帶回的花生,“一年到頭在田里拚死拚活地干,同慶的工分還掙不到兩麻袋紅薯干,你說這怎么讓人活?做夢吧。知青餓得肚子嘰嘰咕咕直響,只能靠他們上海家里每個月寄來的郵包或匯單硬撐下去。”
我父母親也在一旁,盧只能壓低了聲音作著他的自我辯解。他哥哥還留在安徽,與公社書記發展“非同尋常的關系”,盧因此得以溜回上海,給他姐姐帶孩子,可常來我這里聊天。他有時也會抱著他外甥路易一起來,“路易”的發音與外文中一樣,盧說起來還會故意帶一種法國腔。小路易挺聽話的,不怎么哭鬧,我們說話時,他就玩帶來的玩具,在他自己充滿幻想的世界里微笑。
就像在中學里的日子一樣,盧喜歡侃那些讓人流口水的美食——或許只在他想像中,但聊起來卻更繪聲繪色,如“清蒸佛首”——填在白葫蘆中的鴿子,鴿子中更填著鵪鶉,鵪鶉中還填著麻雀;如“乾隆炸魚”——把嘴里塞冰塊的鯉魚油炸一下就撈起,澆上汁,端上桌時盆子中的魚眼珠還在轉;如各種不同版本的“龍虎斗”,原材料可以自由發揮搭配,黃鱔或是蛇肉,貓肉或是狗肉,就看大廚的妙手應用……中國烹調傳統中有八個主要菜系,盧有足夠的材料供他發揮,雖說這些異想天開的名菜,他自己可能都沒嘗過。我琢磨他也只是通過道聽途說批發過來的。這對我來說沒什么區別。“待分配”是寂寞、暗黑的隧道,我有盧經常來串門,運氣應該還算不錯。
對盧來說,他來我這里,也是必要的透透氣。他與他父母擠在一起的小閣樓像雞籠。“文革”剛開始,他一家人就被“紅衛兵”從原來居住的“上只角”公寓中趕了出來。他父母與他搬進延安路拐角的閣樓,他姐姐家搬進寶康里的一間廂房。
要是我去看盧,我得在黑洞洞的樓梯下往上叫他的名字,先確定他在不在,再往上爬。在他家豆腐干一樣的小閣樓里,我都找不到坐的地方。盧晚上是在墻上挖出的一塊狹長空間中睡覺,他指給我看了,但臉色很尷尬。于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他來我這里。
我父母對他的頻繁到來開始感到不安,尤其是他對“以往的好日子”的贊嘆。這給聽的人都可能帶來麻煩。接著,我父母發現了令他們更不安的一個理由。
那是關于盧和我的“地下”書籍交換。盧有四五本“毒草”書;我一樣,手頭一本巴爾扎克,兩本狄更斯,一本歌德。但對我們來說,既不上學又不工作,一天有這么多小時在手上,我們自己的七八本書很快就看完了。所以我們必須“出擊”,擴大圈子,把借書還書變成日常的、不停的、上規模的運作。
盡管“文革”的紅口號響徹半空,有一些上海好人家還是把“黑書”藏了起來,還偷偷地在親友中傳閱。我們自己有這些書作資本,我們也得充分利用這資本。盧用自己在書友圈子中借書還書的例子,來說明怎樣能保持書的高速周轉。“舉個例子,我手中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可以換虹口區青冠的《俊友》,莫泊桑寫的,基本上是等價。莎士比亞經典,但莫泊桑的看起來更帶勁。就一個星期,一天都不能拖。青冠是靠得住的。”
但這其中就是奧妙所在。盧在一夜的時間里讀完《俊友》,然后把書給我;這還不夠,我又把書轉給我的書友,換塞克雷的《名利場》,而我的書同時也轉到盧的書友手中……我們在各自的圈子把這交換繼續進行下去——只要一星期到了的時候,《俊友》能完好地還到青冠的手里。這有風險,我們必須保證交換圈子的可靠,一定要小心通過安全、秘密的地下網絡。在一星期的時間里,一本書會轉上四五次手——到A那里換羅曼·羅蘭,到B那里換托馬斯·曼,到C那里換海明威。因此,盧頻繁地在我家出現。
盧的圈子大多由那些家庭背景與他相仿佛的人組成,但在我這一邊,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接觸對象。《基督山恩仇記》就來自一位黨員高干的女兒。他們本人對所謂的內部書不一定感興趣,可他們的孩子就不一樣了,有時還把書借給別人。
盧是我圈子的核心,四卷本的《基督山恩仇記》自然要借給他,但他也只能有兩天時間。盧按時把書還了回來,眼睛通紅地說,“我通宵讀,我姐姐上夜班,她白天讀。”
我們也開發出一些安全攜帶書本的技巧。我一般把書夾在腋下,外面披兩用衫。盧則把書藏在嬰兒包中,奶瓶露在外面。沒有人會懷疑他包里有書。
但還是有一次,一本《奧賽羅》意外地從嬰兒包中掉了出來,還偏偏落在我父母面前。雖然馬克思正面評價過莎士比亞,但他們交換著憂慮的目光,相信這樣的書也會捅婁子。那天夜里,我無意中聽到他們在討論,準備宣布盧在我們家是不受歡迎的人。
就在他們要著手干預前,另外一件事發生了。母親長病假在家,由于資本家家屬的身份,她在上海牙膏廠領的是“編外工資”。她工資不僅被大幅削減,“編外工資”一詞更標志出她的黑色階級成份。她上個月去廠里領工資,那位會計不知又對她說了什么,她羞憤交加,再不想去那里,用充滿罪惡感的筆在“編外工資”單上簽字。只是她那份收入,不管被扣了多少,對我們家還是不可缺少的。我父親患眼疾無法上班,他那份給全停了。他們商量下來的結果是要我去牙膏廠,為她代領“編外工資”。畢竟,牙膏廠的人不認識我。我卻猶豫了。那里,他們至少知道我是“狗崽子”。
“我也在給我父親代領工資,”盧插進來說,“在廠里不過兩三分鐘的事,拿出你母親的工作證,在工資單上簽字。沒人會說什么。你要是愿意的話,我可以陪你去。”
牙膏廠離家相當遠。去要坐公共汽車,再換無軌電車。母親覺察到我的不情愿,塞給我五毛錢車費——盧和我兩個人用還有多。她說盧能陪我去,讓她也放心多了。
其實,這每月一次的差使并沒有想像中那么糟。在牙膏廠廠門旁的一個小房間里,一個頭發花白的會計把我上下打量半分鐘,我低著頭說“母親病了”,她把裝“編外工資”的信封遞給了我。就這樣。
盧陪在我旁邊走出廠門,突然說,“聽說過擠在公共汽車里的扒手嗎?他們神通廣大。”
“怎么了?”
“我們還不如走回家去。”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點頭同意。我們反正有的是時間,可以慢慢走。那個下午,盧一路上都在展示他驚人的知識面。在上海這個城市,到處都能找到好吃的東西。盧其實也有他現實的一面,會把搜索集中在一些價廉物美的小店。靠近黃河路頭那端,一籠小籠包只要一毛兩分錢;云南路上的原汁三黃雞粥,撒上鮮醬油、蔥花、姜絲,一碗只要三分;再往東一點,五分錢的粢飯糕炸得金黃……
在隨后的日子里,我發現我父母對盧的來訪變得包容多了。再過些天,我又有一次偶然聽到他們在討論,說我有時候看上去神情迷茫,讀些書或許還不算太壞。
下一次去牙膏廠,我們干脆走路來回,省錢更多。盧建議改變路線,可以經過他推薦的小吃店。
“我知道一家生煎饅頭店,上海第一,”盧興高采烈地說,“如嘉上星期從香港回來,第二天就去了那家店。她說生煎饅頭里湯汁特別多,都不敢相信。”
關于如嘉,我只知道她是盧家的朋友,前幾年移居了香港。在盧的邏輯中,她的香港居住證似已為那點心店背書了。不管報上怎樣宣傳黨的艱苦樸素生活傳統,上海人還是有辦法享受生活的味道,同時還保持政治正確。點上一客生煎饅頭才一毛錢,算不上違背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我們那天省下的車錢,足夠點五客。
大約是我們第四或第五次走出上海牙膏廠,盧突然打著響指說,“今天我們去國際飯店。飯店大廳有一個柜臺賣正宗法國面包和蛋糕。這次我請客。”
“二十四層樓的國際飯店?”
“如今這年頭叫國際飯店。這名字實在莫名其妙。可那里的法國烘烤非同凡響。大廚在倫敦學過手藝。”
我不知道他從哪里得到這許多信息,不過聽說他姐姐給了他一點零花錢,他帶小路易確實帶得不錯。
于是我們繞路去了國際飯店,這是上海當時最高的建筑,在南京路北面俯瞰人民公園。我以前從未進去過,但盧信步走入飯店大廳,悠閑、自在,像回到了家中。他吹著口哨挑了根法國長棍面包,還要了瓶叫沙士的棕色飲料。
“味道像可口可樂。”他給我倒了半杯,自己接著從瓶子里喝了一口。
可口可樂聽上去可是遙遠的奇跡,美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征。事實上,我知道這飲料的存在,還是多虧那奇跡般的中文翻譯。我在一本舊雜志中讀到,譯文不僅僅意義是“滋味可口”、“可以享樂”,發音也與英文發音極接近。不過,盧推薦的沙士喝起來像咳嗽藥水,我幾乎都咽不下去。
幸虧我們不常去國際飯店這類場所。不過,我們也漸漸少去路邊的小攤。我們試著把省下的錢積起來,隔一段時間去些有特色但又不貴的店家,像“洪長興”的涮羊肉,“東海”的豬排,“小紹興”的三黃雞。一如既往,盧堅持要把這些“名特色”給我介紹、解釋一番。
在我們一次次的美食探險中,另外一場探險也一直在進行,在我們的地下書籍交換網中。
在盧借給我的書中,有一本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我讀了兩三遍。盧也喜歡這本書,尤其愛引用書中的一段描述,講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幾個粉絲,招待他吃了一頓法國南方大餐,精美的菜肴灑滿奶油味濃郁的醬汁。
“待分配”的第三個年頭開始時,我接受一個鄰居的建議,一清早去外灘公園學太極拳,據說對氣管炎有好處。在公園近江岸的一條綠色長凳上,我卻轉而開始學英語了。這一變化或許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對將來的憂慮;在另一條公園長凳上,偶爾能看到垂柳下一個讀書姑娘的倩影;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在腦海中還記憶猶新——他努力為自己拚出了一條路——可我自己呢?
盧無法與我一起去外灘公園,解釋說他早上要照看小路易。我向他說起,在我去公園后沒多久,那長凳上讀書的姑娘突然不見蹤影了。他對我的動機盡情調侃了一通。
不管盧和其他人怎么說,我在公園逗留的時間越來越長,有時會整整一上午。在江堤邊,白色的海鷗盤旋,似乎帶來綠葉中閃爍不定的信息。
那段日子里,盧回過安徽農村幾次。他哥哥同慶還在那里給他打點一切。盧去鄉下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給公社書記帶上海的禮品。手握大權的書記把盧的名字保持在公社工分冊上:盧身在上海,卻領安徽的工分,像其他的知青一樣,一年到頭在那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74年,我的“代分配”階段突告一段落。街道把我分配到了盛澤里弄生產組。我在縫紉機流水線加工勞動防護帽子和手套。盡管這是三班倒的工作,我還在繼續讀英文。只是,做其他事的時間卻越來越少了,包括與盧一起去外面吃一頓的機會。
對“文革”初期的“革命行動”,人們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也開始在小范圍討論賠償事宜。我卻遠沒有那么樂觀。按“革委會”的說法,那天夜里從我家抄走的東西,有一大半在半路上已失蹤了。更糟的是,賠償的數目是以當年特有的方式計算的。譬如首飾的價值,是按估計的總重量算——我家的首飾據說抓在手里正好一把,大約二十盎司,乘上當時黃金的價格一盎司九十九元。這樣,賠償的金額結果像是在開玩笑。盧卻顯得有信心得多。
政策最終得到落實。“要好好慶祝一番!”盧興高采烈地說。我沒有馬上回應。我家的賠償金額根本不值一提。但他家可能完全不同。他仿佛急于要證實這一點,請我去外灘的東風酒家。
“想當年,我父親與他生意伙伴一起,抽著古巴雪茄,喝著法國葡萄酒——那美好的老時光多燦爛輝煌!”
那幢紅磚的飯店委實選得不錯,至少就“美好的老時光”的記憶而言。盧把小路易也帶上了。再過幾年,路易就要上小學了,但他依然到處跟著盧,大眼睛里充滿期望。那天晚上,餐廳太鬧,也太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像樣的服務。我也沒看到那歷史上有名的亞洲最長吧臺,或許“文革”一開始就給人作為“四舊”移走了。我們坐在一張遍布醬油漬的桌子旁,點了幾道不太貴的菜,有一大碗黑胡椒鱖魚湯是路易選的。他眼睛不停向養活魚的水缸轉過去,等著看服務員怎樣把游魚撈出來,但他一直沒看到,很失望。
要好長一會兒后,魚湯才熱氣騰騰端上桌。盧立刻又開始發揮,向我傳授烹調魚湯的秘方。
“看這湯。絕對奶白!但其實容易。你得先在鍋里煎魚,加火腿雞湯,在小火上燉兩三個小時。等湯終于白了,你撒上一把胡椒和蔥花,就可以端上桌了。”
魚湯味道真好,魚肉潔白,映襯著綠蔥花與紅椒絲。我喝了一湯匙,匆忙把剛學到的秘方記在腦中,盧在旁邊打著滿意的飽嗝。
“我們還要聚一聚,”他信心十足地說。“更多的賠償金要發給我們這樣的好人家。還要辦一次慶祝晚宴——在更豪華的餐廳里。”
靠著想像中的賠償金能這樣揮霍多久,我還真說不上來。
那頓晚飯后不久,盧又去了一回安徽,他所承諾的請客沒有實現。也許他期望中的二度賠償沒出現,也許他未能找到家更豪華的飯店。
近1975年底,盧突然告訴我,他被分配去安徽國營船隊工作,在淮河上來回運輸的一條小貨輪上班,船偶爾也有機會駛進黃埔江。
“算不上是大船,”盧說,“上面只有三四個人,但工作性質是國營的,還有機會不花錢坐船回上海。我沒什么好挑剔了。”
這因此看來是個不錯的工作,甚至令人羨慕——與那些分配到當地社辦工廠或礦井的知識青年相比。
“我過些天請你免費浦江夜游,在船上喝咖啡,抽雪茄,看外灘建筑。”
但盧從未請我到他船上去。
我也始終無法把這兩個形象疊加起來:一個汗流浹背洗甲板的黑黝黝船員,一個在游艇上哼著小夜曲、攪動咖啡杯中幻想的“華僑”。
“文革”結束了,“不是嘭的一響,而是噓的一聲”,如艾略特在《空心人》一詩中所描繪的。許多事開始恢復到“文革”前的狀況。1977年,我通過高考進了華東師范大學——其中英語考分滿分,這還真多虧了外灘公園中的一個個早晨。半年后,我又“破格”考進了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卞之琳先生攻讀英美現代主義詩歌。在隨后的三年里,我只在寒假期間回上海。盧的駁船據說總那樣忙,停泊或運輸在遙遠的水域,至少這是我的印象。我們幾乎都見不上面。
大約是第三或第四次去他家,我依然沒碰見他。我通過他母親給他留了幾本書,她給了我一袋黃糖年糕,說是盧一定要她轉交給我的。年糕是按他私家食譜做成的,所用的糯米也是他從安徽特意帶回的。黃糖年糕很黏牙,除此之外,其實沒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
在北京畢業后,我被分配回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那些日子盧似乎也一樣忙,忙著要把自己調回上海來。1980年代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一筆勾銷了,大部分的知識青年獲準回到城里。相形之下,盧遠在安徽船上的工作再不值得一提。
盧當時正開始與一個普通家庭的女孩子談朋友。她在延安路上的一家糖果點心店上班,也沒什么學歷。但盧自己既無上海工作,又無上海房子,有個上海女朋友,也算給他臉上增了光。
1980年代的一個下午,我去看盧,帶著一本我翻譯的康拉德中篇集子,《秘密的分享者》。在翻譯過程中,《秘密的分享者》中主人公身旁神秘的“另一個”,不知怎么讓我想到了盧。那天,盧與他綽號叫“黃鶯”的女友在一起,擠在他姐姐家后間中隔出的一小間,沒有窗,相當黑,面積只夠放一張床。黃鶯是個很甜的女孩,把一碟冰糖核桃放在床上的康拉德上,手指上像有一點糖漬。
“這是我店里的,免費吃。”她說,她的微笑照亮后面斑駁的墻壁。
關于那個下午,我能想起的好像也就是這些了。我把《秘密的分享者》給他們留了下來,但壓根沒提書與盧的關系。盧和黃鶯什么也沒問。
1988年上半年,我聯系到福特基金會的一筆研究基金,可以去美國挑個地方做一年的訪問學者。出國前,我去寶康里看盧。那天早上,他正蹲在樓梯下那塊黑洞洞的地方,用一堆從里弄煤球供應站買來的便宜煤屑做煤餅。他光著膀子,臉上沾滿煤屑,看上去怎么都不像華僑。他徒勞地在灰圍裙上擦著手,匆匆把我帶到了樓上。黃鶯正在一個小爐子上做蛋餃,看上去真像個賢惠的妻子。他們不久前結婚了,就在那隔出來的小間里,算是臨時的新房。
房間像更擠了,都透不過氣來——當然這也許與小爐子的煤氣味有關。我們那天到底說了什么,我幾乎都想不起來了,除了他關于蛋餃的一番話。
“攤蛋餃皮需要高度耐心和技巧,把肉餡裹進去也得細心,不能破了。但吃起來,什么都比不上我這里的私房蛋餃——自己家里做的蛋餃皮加上拌肉皮凍的肉餡。還記得電影院后面那家生煎饅頭店嗎?黃鶯這蛋餃味道要好得多。你今天無論如何都得嘗嘗她手藝。”
“都是盧教我的,”她不好意思地說,眼里洋溢著對他的崇拜,“他知道這么多。”
蛋餃確實非同一般的鮮美。通常,蛋餃是放在湯里的,也就是三四只,作為色澤鮮亮的點綴,與蔬菜和粉絲一起。那天我卻吃了整整一碗,像是吃餃子,也許有二十多只。黃鶯緊張地看著,生怕我不喜歡。我硬塞了下去。
我終于站起身要告辭時,盧用低沉的聲音說,“別忘了我們。”
“這怎么可能?我一年就回來了。”
“好吧,我們走著瞧,”他說著,把手中的煙彈了彈,“‘華僑——”
那一年的夏天,我沒有選擇,只能在圣路易留下來,為保持在美居留的身份,在華盛頓大學讀博士課程。在隨后的五六年里,我太忙了,沒辦法回國去。我與許多老朋友失去了聯系,其中包括盧。在來自上海的寥寥無幾的家信中,妹妹也從未提過他。
但我還時常想起那些與盧一起的日子。也許像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所寫的,只有在經驗的回憶中,新的體會與意義才會浮現。
或許還因為我以前從未想到過的一個原因。在圣路易,大多數中國餐館其實都美國化了,這里的華人卻常開玩笑說,“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胃。”我開始嘗試在家里做菜,在鍋碗瓢盆中,那些關于盧的記憶更紛至沓來。
1996年,我第一次從美國圣路易回上海探親,向我妹妹問起盧。
“你離開后他從沒來過。一次都沒來過。”她語氣中有不加掩飾的不滿。“他可能搬走了。最后一次我見到他騎那老坦克自行車,搖搖晃晃經過山東路——我想一想,那大約是兩年以前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盧在延安路的家,但那老房子消失了,只看到正在建設中的一個地鐵口。我接著去他姐姐在寶康里的家。她還在那里,告訴我盧已回到上海,現住在楊浦區自己的房子里,在靠近西藏路的“杜五房”熟食店上班。
“噢,他現在是經理了。”她加了一句。
我轉過身,手拉著黑漆漆的樓梯檔摸索下去。還是那么陡,一步步都得小心,一瞬間仿佛又回到了過去。
在記憶中,“杜五房”是家老字號熟食店,以紅醬肉、熏魚、鹽水鴨膀等熟菜聞名。我不到十分鐘就來到那里,一眼瞅見臨街的玻璃柜臺。老牌子的醬肉依舊在午后陽光中紅油閃亮,但柜臺看上去小了許多。
我走進去,在熟食柜臺后看到一群衣衫不整的顧客在桌子上吃餛飩,用方言大聲談話哄笑。在墻上黑板菜單中,“薺菜鮮肉餛飩”列在最上面,價錢也相當親民。
盧在店堂里,穿一套油漬斑駁的工作服,拿一塊抹布正過來擦桌子。我脫口叫出他的外號,“盧‘華僑!”
“你——”他吃驚地轉過身,直眨眼,好一會兒才認出我,卻說不出一句話。
“這么多年了——”我一把抓住他在工作服上擦著的手,“我們要好好聊聊。走,找個安靜一點的餐廳,去國際飯店怎么樣?現在已快四點半了。”
“先在這里來一碗餛飩吧?”他有些猶豫地說,似乎不著急走的樣子。“我是下午當值經理。這班頭六點半才完。”
“也好,我們在這里先聊著,不過——”
盧把我帶到隔墻后的一張小桌子,離廚房很近,可能是為雇員們留出的一塊地方。我聽到廚房的大油鍋正噼噼啪啪在炸著什么,聞上去像是咸帶魚。
盧坐在桌子對面。他看上去變化不太大,但又實在不是我曾那么熟悉、想當然的盧了——在那些日子里,盧聽到去國際飯店,步子準定邁得比誰都快。作為一家國營熟食店的經理,偶爾與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一起提前走開一兩個小時,應該沒什么關系吧。
“最好的餛飩一碗,”盧大聲向廚房喊著,“給我從美國回來的老朋友。”
于是我們聊了起來,桌子上放著薺菜鮮肉餛飩,湯里還漂著姜絲和蛋絲,幾乎就與我們中學里的日子一樣。
只是,這些年在他身上發生的一切,似乎沒什么特別精彩的可以當故事來講。1990年代初,報刊上也承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了問題,因此那些已上調到當地工礦的知青,也獲準返城。
盧放棄他在船上的工作,終于回到上海,在這熟食店里找了份工作。在前面柜臺上干了幾年營業員后,他升了當班經理。“簡而言之,不在最上面,也不在最下面。說到底,不少人在上海甚至都沒工作呢。”
他的敘述不斷讓人打斷,一會兒是前面柜臺的營業員向他大聲提問,一會兒后面廚房的大廚因為給他煮了一碗“最好的餛飩”,問他要支煙抽。盧得時不時站起身,跑前跑后。這工作也夠讓盧忙的。
“‘杜五房是上海有名的老字號,”他說著,湯匙在餛飩湯里轉動著,像攪動著記憶,“在‘文革中,店名是‘東方紅——”
“對,你告訴過我那革命店名可能的起源:因為那醬肉也是紅紅的,我還記得。”
“真的?”他惘然注視著我,“但熟食店再不時興了,不管叫什么名字。”
“這怎么可能呢?”
“過去,上海主人會堅持要在家里請客人吃飯。因為食品供應緊張,因為飯店少得可憐,整條西藏路上也不過兩三家,人們就會來熟食店買幾個菜。可今天,大飯店小飯店到處可見,主人要是不請客人到外面去吃,就丟面子了。”
這就是為什么柜臺前顧客那么少,甚至像‘杜五房這樣的老店還得在后面供應餛飩,多少彌補一下前面失去的生意。我勺起一只餛飩,餡子中的薺菜綠得可愛,在我美國鄰居的后院中,薺菜是不能食用的野草。
“變了,全變了。”盧低頭說。店里哪個角落里的收音機正傳出一支流行歌曲。“昨日的夢已被風吹送/今日的風仍在夢朦朧……”
“你下班后,我們換個地方去坐坐。外灘東風飯店怎么樣?”我又想起了多年前那頓晚飯。我也可以在那里告訴他,他教我做的魚湯怎樣在美國大獲成功。
“東風飯店早沒有了,改成了肯德基。我前些天還經過外灘那個角。”
“為什么改了?”
“有些上海人認為肯德基時髦、高檔、全球聞名。個別喜歡出風頭的還把結婚筵席設在那里。”
“那你來挑家飯店吧。在上海,你一定知道好幾家。”
盧卻嘟噥著說晚上要陪他女兒做功課,開始用一片紙餐巾擦嘴。
我于是站起身告辭,隨著盧穿過幾張桌子,向門口走去。在那些顧客中,有一個還偏好老牌子熟食,桌子上有盆糟耳朵,顯然是從前面柜臺買來的。他可能有些醉了,但還在喝黃酒,自己哼著小曲。
“你聽到唐的故事了嗎?”盧突然轉過身問我。
“唐,什么故事?”
“他幾年前跳進一口枯井自殺。活活餓死的。兩三個星期后才讓人發現尸體。他當時去江西一個偏遠的村子插隊,駕駛的拖拉機翻進了溝里,大腦受了傷,從未恢復過。”
我想到了那個遙遠的午后,唐、盧和我一起在老城隍廟,在一家家小吃店中推進“美食戰役”。這是一場荒唐的經歷,但陽光灑進我們年少的笑聲……
在似曾經歷過的恍惚中,我抬頭瞧見西藏路對面的大世界。這曾是上海最有人氣的娛樂中心,現在看上去卻像給人遺棄了,年久失色、失修。在大世界前,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初起的日子,盧和我不止一次地站在這里向披紅戴綠的“知青汽車”揮手致意。在鐵鏈鎖起的大世界進口旁,我見到一家新開張的四川飯店,霓虹燈招牌投射出“醉江南”字樣,融入下午還殘剩的日光。驀然,一只孤零零的藍雀在耀眼光線中掠過。
“明天在醉江南吃午飯,好嗎?”我說,“你總有午餐休息時間吧。”“十二點,”他點頭答應,“我在餐館里等你。”
第二天中午,我在餐館里見到了盧。他筆挺地坐在近進口的一張桌子旁,身穿新的休閑西裝,胸前口袋還露一角白色絲手帕。一瞬間記憶中的華僑又回來了——可在那些穿仿靛藍花布裙裝、假冒四川口音的年輕女服務員中,他看上去奇怪地格格不入。
我剛坐下,他就把菜單給我推過來,“還是你點吧。現在你可是見過世面了!”
我們每人都點了一兩個菜,不算太貴或太怪,還相當傳統。麻辣牛筋、干鍋牛蛙、宮爆雞丁、麻婆豆腐,再加上一份紅辣椒油中的水煮鯰魚。最后這一道是盧推薦的,說是上海最新的流行。
魚真是出奇地嫩,白色的魚肉映著濃濃的紅湯,我們不停地用啤酒解辣。在小爐子上的小鍋子里,撒了枸杞的蛙腿令人食指大動,四川牛筋幾乎透明,嚼在嘴里又脆又辣。這些正宗的特色菜在美國難以想像。
我舀起一匙豆腐,開始講我在圣路易煮黃油魚湯的經歷。他喝一小口啤酒,撕下一片蛙腿,但眼中似有遙遠的茫然。
接下來輪到盧了,由他繼續上一天的故事,填補其中留下的一些空白。他剛回來時花了很長時間找工作,卻四處碰壁。在浪費了十年的時光后,他無法在求職表格中寫自己有什么學歷或特長,最后卻因為他在面試時說了平時喜歡做菜,讓他得到了熟食店的工作。他家在延安路上的閣樓在地鐵工程中給拆了,作為補償,他在楊浦區分到了房。
“這是老式的單居室,但我想辦法把房間隔了一下,也等于套間了。”他慢吞吞說著,把筷子捅進魚眼睛,將魚頭裂成兩半,就像演示那困難的裝修工程。
“你如今是貨真價實的華僑了,你懂的。”他聳聳肩說,又舀一匙魚湯,仿佛終于接受了命運的錯位。
我試著把我們的談話引回到我們那些年讀過的書。
“我們已經不再年輕了。”盧說,從湯里夾起最后一片魚。
我把啤酒一口干了。
吃完飯,盧靜靜坐著讓我買單,點起一支煙,沒有把賬單搶來搶去。
那天分手時,我忘了問他要電話號碼。但我想沒關系,我們肯定還要見面的。熟食店離我家就十分鐘路。
但那次回國,我卻沒再見到他。因為一個翻譯項目,我匆匆趕回了美國。要到三年后,我才有機會又一次回中國。那次我住進一家離大世界不遠的賓館。第二天下午,我徑直去了“杜五房”熟食店。我不知道盧是不是正在班上,但那沒關系,如果不在,我就買個熏魚頭到賓館作宵夜,倒時差得有好幾天睡不好。在那熟食店的原址,我卻驚訝地看到一家新漆的門面——賣美國炸雞,類似肯德基,門面上也有英文標志,雖然這標志我在美國從未看到過。
盧不在店里。一個女營業員忙著在柜臺里擺炸雞腿。柜臺看上去還挺熟悉的。我向她問起盧。
“盧不在這里了。”她簡單地說,舉手揮走一只不屈不撓繞著柜臺嗡嗡飛的蒼蠅。
“但‘杜五房——”
“熟食店賣掉了。現在是‘美國炸雞。我是老店唯一留下來的。”
“盧去了哪里呢?”
“回家,但他還有‘雙保。”
“雙保什么意思?”
“他現在沒有工作了,但到退休年齡,政府還保證他有社保和醫保福利。”
“那么現在他也沒有工資收入了?“
“沒有了。只剩兩三百元最低生活費吧。沒辦法,他得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話說回來,他是雄心勃勃的人,你知道。老話說得好,小廟里容不下大菩薩。他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地開創自己的大事業。”她聲音充滿挖苦,手中的塑料蠅拍一揚,“啪”一聲拍死了蒼蠅。
我對她的嘲諷并不太驚訝。盧就是這樣,喜歡夸夸其談。我習慣了,但對這位女營業員,可能是另一回事。
“你有他家里電話號碼嗎?”
“沒有。”
“什么?!”
我想當然地以為我總能找到他。這實在是我的錯。
我轉身趕向寶康里,但這條弄堂也消失了。一座高層建筑正在那塊地皮上興建,暮色中,一臺塔式起重機似在向陌生的天際打著問號。
我妹妹小紅告訴我,寶康里的居民都搬走了。盧的姐姐去了哪里,她沒聽說。我又去找了幾個老同學。其中一個說大約兩年前,他有一次看到盧在店門口叫賣蘿卜糕——可能是盧在為挽救老字號熟食店所做的最后努力。只是盧似乎故意立刻轉過身,兩人都沒有打上招呼。或許不難理解。這不是盧感到臉上有光的工作。他無意見老同學。
但到了最后,連這樣一份工作,他也丟掉了。
我努力從我們在醉江南飯店的談話中找出頭緒。唯一能想得起的線索是他在楊浦區的房子。但那區域太大了,我查遍了電話白頁,沒找到他名字。他家里甚至都可能沒裝電話。
在他年輕的時候,盧堅持不跟時代的潮流走,但他能堅持多久呢?最終,他改弦易轍,準備與其他人一樣安分守己過日子。只是時代在變,改了道的水流卻又讓他擱淺了。這也可以歸咎于他的運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僑”這個詞的含義又變了,至少聽上去不再令人羨慕。在“美麗新世界”里,中國國內的暴發戶炫富擺闊,讓海外的華僑都要瞠目結舌。甚至有了又一個新詞“海歸”——從海外歸來到國內尋找新的商機賺錢。也有人在談“中國綠卡”了。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