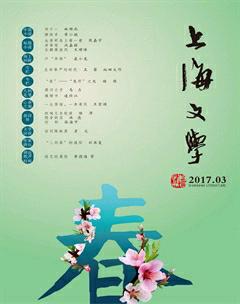“三劍客”的通信
劉再復
胡風、蕭軍、聶紺弩三人的通信集,肯定會受歡迎。因為這三個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三劍客”。以往出現過許多“武俠小說”,但少有“文俠小說”,而這三位作家,都是名副其實的“文俠”,滿身都是俠氣、正義與豪氣,其傳奇故事很值得作家書寫。
關于胡風,因為他于1949年后成了反面的“風云人物”,被全民共討之,全國共誅之,但也因此變得家喻戶曉,以致達到“滿村爭說蔡中郎”。其實,胡風是一位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奮不顧身、一路吶喊過來的“左翼”作家。明明是革命派,卻被視為反動派,“歷史”在他身上完全顛倒了。他和蕭軍、聶紺弩能成為朋友,完全是因為他是“左翼”先鋒,擁有刊物和思想,而且都是追隨魯迅的“革命文藝戰士”。只是生性太耿直,詩人氣質太濃,有話藏不住,給新國家領袖上了三十萬言意見書,結果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還殃及了千百位很有才華的朋友。胡風冤案,是當代典型的文字獄。我個人在1980年代與周揚關系較為密切,與胡風則毫無瓜葛,但私下倒是認真閱讀《胡風文學評論集》等書,非常欽佩胡風的文學見識,認定他是“五四”啟蒙精神和寫實主義文學新傳統的真正傳承者,也是魯迅精神薪火的真正接力者。他所倡導的作家“主觀戰斗精神”,乃是激發作家擁抱客觀現實社會時所必須持有的啟蒙態度與能動態度。我的“主體論”強調作家的“超越”,胡風的“主觀論”則強調“擁抱”,其實,殊途同歸,都是希望作家不要陷入蒼白的“客觀主義”泥潭,要敢于反思我們正在進行的“現實生活”:我們的生活在何處迷失了?我們的精神在何處麻木了?我們的精神出路在哪里?胡風用詩情的語言提醒勞苦大眾(當然也提醒作家)要抹掉“精神奴役的創傷”(說得何等深刻!)。唯有抹掉這種創傷,才能走出奴隸狀態和平庸狀態。然而,胡風太書生氣了。他竟然忽略了革命領袖已經提出了一種新的精神綱領和精神方向,那就是作家的使命不是啟蒙大眾,而應當接受大眾的啟蒙與教育。工農大眾既已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當然也應是時代精神的啟蒙者。胡風沒有意識到其理論的方向與革命主流的思想方向正好相反,堅持下去就是“對著干”。由于性格的過分剛烈和理念的過分執著,他終于倒塌在自己的“意見書”上。接著,政治完全“不容”他,即政治完全壓倒文學,意識形態完全壓倒理論探索。胡風,這位身兼詩人的現代杰出文學理論家完全被政治邏輯所吞沒。它的合理的具有真知灼見的文學見解也被政治完全埋葬了。從通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蕭軍、聶紺弩等耿介作家對胡風都極為尊重,極為愛戴。
聶紺弩曾寫過二十首贈予胡風的古體詩,“三十萬言三十年”,他不僅替胡風鳴不平,而且為中國文學界失去這樣一位有思想有才能的領袖人物而深深痛惜。聶紺弩是我的忘年之交,他為人極為慈悲善良,一生都在蒙冤蒙難。他的古體現代詩寫到無人可以企及的巔峰;他的雜文寫到可以“亂真魯迅”(夏衍的評價)的地步;他的《紅樓夢》研究寫到讓紅學界全然失色。這位像春蠶吐絲的“左翼”作家,受胡風的牽連,被打成“胡風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又因對江青甚有微詞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牢十多年。然而,不管歷經多少苦難,他對胡風的敬仰始終不移不遷,“胡頌”一直寫到最后一息。聶紺弩先生曾在拙著《魯迅美學思想論稿》的扉頁題簽,寫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行。斯為真,斯為善,斯為美。斯為文人行。”聶紺弩正是這樣一位至真至善、知行合一的文學家。
我與晚年聶紺弩交往甚密。在他身上,悟到一條真理:文學是美妙的,但文學也是殘酷的,它可以把一個作家詩人的心血全部吸干。我初見聶紺弩時,他已是皮包骨,身上完全沒有肉,但他靠在床上仍然顫巍巍地不斷書寫。以往的苦難,他沒有時間去咀嚼,今天贏得一點殘存的心力,只能用于進行精神價值創造,或寫詩,或寫雜文,或寫閱讀古典名著的心得,他都投以全生命、全靈魂。他那種獻身于文學的精神品格,給我們以極大的教育。
胡風、聶紺弩身上有“俠氣”,蕭軍更是典型的“文俠”、在文學圈子里,一提起蕭軍,人們總是說起他與蕭紅的關系,而且總是說他有負于蕭紅,且文學成就遠不如蕭紅。我不愿重復這種簡單化的說法,但想接著說,蕭軍雖是一個作家,其主要成就卻不在于他的文學語言,而是他的實踐語言,即他的生命行為語言和記載生命行為的書面語言,這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思想語言。而這些語言塑造了一個人、一條漢子、一位俠客,一個耿直、正直、憨直的知識分子。蕭軍的可愛之處正在這里。
在與蕭紅交往之初,他是一位“名士”,魯迅看了他的文章后,就說他的文章名士氣重。之后他到了延安,投入革命潮流,從“名士”變成“戰士”。然而,他雖然真誠地支持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事業,但總是不被革命組織視為“自己人”,而是被視為“同路人”。盡管他與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云、彭真等共產黨高級干部均有交情,但還是被視為“異端”和“局外人”,甚至被視為“反黨分子”。這也難怪,他總是那樣正直,那么不安分。黨內有不公正之處,他就要批評,社會有不光明的地方,他總要說話。黨要他規矩一些,他偏不屈服,偏要獨立不移。于是,他不像“戰士”,更像“俠士”。在一個紀律嚴明的大組織內,俠士總是讓人覺得不太“靠譜”,但他本人則對革命事業“不離不棄”,把共產黨視為中國人民解放的希望。于是,他雖然生活在中國現代文化“左翼”的范疇內,卻總是讓人覺得與革命潮流不太相宜。于是,一種特異的生命現象就此發生:一方面,他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反抗中國的黑暗,不屈不撓;一方面,則被推到勝利者之外,甚至被勝利者送入“黑窩”、“牛棚”,乃至“牢房”,不明不白。一方面他寫著廣義的革命文學,一方面又不斷寫著“檢查”與“交代”,并出版了一本《我的文革檢查》。這種書本沒有什么文學價值,但因為蕭軍的檢查、交代也寫得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換句話說,也寫得有理有據,有正氣有剛氣有豪氣,因此也精彩非常,不僅有人格價值,而且有史料價值。連在“黑窩”里書寫交代材料也有剛正之氣,也不扭曲自己,更勿論牢房牛棚之外了。蕭軍正是以他這種不同凡響的生命行為語言告訴人們,在不正直的時代里也可做正直之人,在扭曲的環境中也可以挺立自己的靈魂與脊梁。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確實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蕭軍在自己的“檢查”中說,他既“無求”也“無懼”,這是真話。但我要補充說,蕭軍不止無求無懼,他還“無私無待”。敢說敢寫敢抗爭,乃是因為“無私”。說他“無待”,則是他雖然追求群體事業,卻不依不附,不讓自己緊貼上哪一個黨派的“皮”,獨立不依。在任何環境中他都自立自強,人格精神總是飛揚在時代的高峰上。總之,蕭軍“做文”(寫作論學)雖不屬第一流,但“做人”則是第一流,其生命實踐語言也屬第一流。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很難找到像蕭軍這種獨立人格的漂亮生命語言了。無論是他的日記(從《延安日記》到《東北日記》),也無論是他的書信(無論是與蕭紅的通信還是與胡風、聶紺弩的通信)都給中國留下現當代歷史重要的一筆。具有慧眼的讀者,只要閱讀他的生命“豐彩”就夠了,不會苛求他的“文采”。換言之,領略蕭軍實踐語言的詩意就夠了,欣賞他的律詩和其他文學作品倒在其次。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最了解“人的精彩”比“文的精彩”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