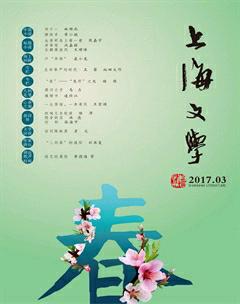生命尊嚴的時代
王蒙+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我的恩師戶田城圣先生經常說:“人生取決于最后幾年幸不幸福。此前的途中如同做夢,不管此前多么艱辛,如果最后幸福,那就是幸福的人生。”
不可能有不吃苦的人生建設。無論有什么都不屈服,活著要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且,怎樣度過總結人生的老年期,在進入老齡社會的現代越來越重要。
王蒙:您剛才講的戶田先生的話深深打動我的心。那天正好是我八十歲生日(2014年10月15日)的前一天。聽到戶田的話,這是我的命運贈給我的最好的生日禮物。池田先生,謝謝!
我更有理由相信,我的人生是幸福的,幸運的。我必須感謝此生,感謝師友,感謝我的家國故鄉,還必須感謝您與戶田先生。
池田大作:我才要衷心地感謝能夠有機會和王蒙先生交談,學習。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學》中寫道:“老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老年有克服很多苦惱、長久活過來贏得的經驗和智慧,有將其有價值地利用就能為人們和社會做貢獻的優點。
日本愈發成為老齡社會,中國也有老齡化傾向,老年人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數量也在擴大。
您怎么看老年人對社區、對青年應該發揮的作用呢?
王蒙:老齡只不過是上了歲數。就我自身來說,明年我也許衰老,但今年還充滿能量。只要有能量,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些有益于鄰居、家鄉、眾人之事。
中國和日本有敬老的傳統,我現在還不至于嗟嘆被當作老朽。
如果明年終于年老力衰,對大家沒有用了,那也是一種境界,可以笑瞇瞇,樂呵呵,漸漸地淡出,那也是人生最高的成就。
老年人愿意留下自己的經驗,得到年輕人尊重,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強加于人。因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環境和關注,與上一代有所不同。
許多年以前我注意到,經驗可以談,也可以聽,也可供參考,卻不能復制。老年人應該相信年輕人。他們有自己的麻煩,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責任和能力。
老人應該盡到自己的責任,卻無法分擔或減輕青年一代的責任。
池田大作:確實,人生有各個世代的使命與責任。同時,再沒有比覺得自己在社會上無用,或者找不到活的目的、使命更痛苦,寂寞的了。可以說,正因為是現代這樣的社會,才需要去掉老年人和中年、青年一代之間的隔閡,進行心心相印的交流。
老年人接觸青年的氣息,自己的心也變得年輕。對于青年來說,前輩跨越苦難風雪的人生經驗和智慧必定會成為巨大的鼓勵。
日本也越來越有人指出加深這種老年人和青年的交流,互相觸發之重要。
尤其是緊要關頭互相扶助的精神等,繼承這種活在庶民中間的良好風氣是使社會更向上的基礎。
王蒙:1998 年我在訪問挪威的時候與一位女出版人談過生命問題。她說,人類的生存好像一棵樹,每個人是樹上的一葉、一花、一果,遲早都散落到地上消失。但具有生命的那棵樹本身繼續生存、成長。她的比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生命之樹的繼承與繼續不就可以說是包括了文化傳承的含義嗎?青年人要是尊重人類已有的經驗及其積累,那當然就變成對老人的敬意與照拂。《論語》有“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原意是祭祀祖先誠心誠意,但“慎終追遠”四個字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德,它表現了對時間的擴展與延伸的責任感。思念祖先,則馳思子孫萬代。這是追思事物之源,也考慮未來的結果的度量與責任感。
池田大作:向過去學習,思考未來,活在今天,這將使人生更可靠。
王蒙先生總是在思考“事物的根源”,這和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究問也相通。
“我們人從哪來呢?我們人是什么呢?我們人往哪里去呢?這些問題就是根本問題。”
柏格森的哲學我在年輕時也烙印在心里。
這種究問,誰都會面臨吧。
關于“事物的根源”,我還想起的是唐代畫家張璪說的藝術原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里教示的是,為了偉大的價值創造,應該從自身以外的現象學習,同時磨礪、凈化自身之內的心,開啟創造力的源泉。
不要忘記,文化的繼承也不只是理論方面或外形方面,精神方面的繼承、化為血肉也很重要。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學》中還說:“人老了,應該成為一個哲學家。”
隨著年老,不能不或多或少面對體力衰弱或疾病,與早晚必來的死相對。
我想起釋尊出家的逸話“四門游觀”——釋尊是王子時,出王城東門遇見“老人”,出南門遇見“病人”,出西門遇見“死人”。覺悟人活著,“老病死”的苦惱不可避免。出北門遇見出家的圣人,決意出家。
克服人的根本苦惱生老病死是佛法的出發點。這是誰都要經歷的苦惱,所以誰都會注視自身的生老病死,探求真正的人生幸福的哲學家、宗教家。探求深刻的時期尤其是老年。
《法華經·見寶塔品》里,用金、銀、珍珠等七寶裝飾的、大如地球的寶塔出現在大地上。
門下問寶塔的意義,日蓮大圣人回答:那就是人本身的生命。即“持《法華經》之男女,身外無寶塔”,明示生命的無限尊嚴性。又說:“以生老病死四相莊嚴我等一身之寶塔。”遵循永遠常住之法時,連生老病死也燦然輝耀自身的生命寶塔,使之莊嚴。這是佛法的真髓,信仰的目的。
我青年時代拜讀日蓮大圣人這句御文,被佛法的深邃法理大為打動。現在,經過長時期的信仰實踐,以及看見很多跨越考驗與宿命的人所走的尊貴人生軌跡及總結人生的體驗,深深理解了正是如此,確信不疑。
王蒙:我有一個觀點,未必能講清楚。那就是宗教與無神論并不是勢不兩立的。
神學的意義在于終極關懷。宗教的終極是佛,是主,是佛的世界、神的世界。無神論者的終極是“無”,老子說“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是信仰,無對于無神論者是最高、最大,而且最遙遠、最古老、最年輕。無還是本源,是歸結,是起點是終點。萬事萬物的根源是無,那么,無神就是終極的“無”,無神成了神性洋溢的終極。而且“無”作為“無”的結果當然是“有”,所以“無”是無神論者的皈依,也就是無神論者的“無神之神”——富有神性的“無”——“神”的概念。中國老子的哲學叫做“有無相生”,銀河系、太陽系、宇宙,原來是無,后來成了有,有還要成為無,無還要成為有,恩格斯也是這樣說的。
這也是《波羅密多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理解的延伸之一個方面。
這還是質量守恒定律與能量守恒定律的聯想。守恒并不是沒有成住壞空,而是認識到壞與空同樣可以向著成與住變化發展,承認有會滅亡成無,而無中必然生有。
在這個意義上,樂觀與悲觀的差別也可以超越,生與死的觀念也可能進入新境地。
死是生的完成,滅是發展的結果。死是生的極致,死是向生的死。如果說人的悲哀在于“向死而生”,我們不就同樣可以相信并期待嗎?死是走向生的死。
不然的話,這大千世界從哪里來的呢?你和我,以及他、她們,還有萬物,從哪里來的呢?假如太陽已進入中年,假如再有幾十億年太陽系將毀滅,那么我們不是可以相信毀滅之后再生嗎?毀滅是再生的開始。
死如果不存在,就不會感覺生,需要生,體驗生。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醫學、科學,什么都不存在。
我們當然惜生愛生,同時死能夠使邪惡的人們安定,平靜地面對寂寞。我們面對生命的全過程只有拈花微笑(不說話,以心傳心)。
池田大作:自古中國思想真摯地面對生與死,反復考察。
譬如《莊子》告訴我們,生與死連續,把生與死分開,討厭死,是不正確的。“善夭善老,善始善終”,“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這里指向超越生死的永遠性。
凝視人死這一根本條件而考察生,關系到人性、精神性的復蘇。
近代文明被稱作“忘記死的文明”,科學技術發展而醫療進步,另一方面,有一種死本身可惡而掉頭不顧之感。而且,在科學文明進步的20世紀,人類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死亡、虐殺,這也是重大的歷史教訓。
法國思想家蒙田反復考察了死的意義。有點長,但想在此引用一下。
“死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能有假面。……但是,死和我們之間上演的最后的戲劇已經沒什么裝飾。……所以,我們一生的其他一切行為必須以這個最后的行為為試金石來檢驗。這是最重要的日子,是審判其他一切日子的日子。”
“判斷他人的一生時,我常常看他最后怎么樣。我畢生努力的主要目的也是最后能善終,那就是平和而安靜。”
說永遠生命的佛法也明確教導,活著時的行動將是決定死以及死后的狀態。
世界著名的心臟外科醫生、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翁格爾院長說過:可以說,滿懷自信地走過充實人生的人以良好的生命狀態死去。
在死亡面前,什么樣的當權者、富豪都一律平等。只將評價你是怎么活下來的。總之,能否跨越人生的苦難,為人、為社會盡力,充滿出自心底的感謝與幸福。而且要以朝氣蓬勃的心來總結充實的人生,我認為這比什么都重要。
王蒙:一位媒體人問我,您是否有記憶力減退、文思枯竭、體力下降的老年人的悲哀呢?我的回答是,現在還沒有,明年可能有吧。
2013年我寫過一篇小說,題目是“明年我將衰老”。
生老病死是苦惱,也是契機,是得到的恩賜,又是思索與覺悟的機會。活得不那么短促,就可能多多回味與概括,無限地接近人生的真諦與真味。
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老邁,有健康就有疾病。有死所以有生,生生不已。“大德曰生”。因為有衰老,所以才涌起對青春的回憶與珍惜的心情。那還觸及生命的漫漫路程,也是贊美。患病就會想健康的日子和健康的人們,感到對健康過的感謝與滿足,得到更全面、更豐富的生命體驗。
中國話把“死”也叫“大限”。有終于大限,亦即無限,乃歸于零,歸于空,也就是色即是空的體驗。又得到零與無窮相結合的信念,還有空即色的信念。
還得到陶淵明的詩句“托體同山阿”的豁達大度。
生命易逝,即視為悲哀流不盡眼淚,那種悲也將關系到覺悟,得以升華。化為審美力、思想的智慧大放光明。
我喜歡佛法說的“大悲”這個詞。遼寧省海城市和四川省南充市有大悲寺。這個名字令我感動。同樣,北京的古老地名有叫“大光明境”的胡同,這也是非常好的名稱。
大悲與無悲。大悲的另一面、另一端就是佛法常說的歡喜。有了歡喜心與大悲心就是佛心了吧?大悲是一種視角,是悲的無窮化。人死了才無窮。無窮,人就成為零。零與無窮相結合,那就是全,又不是全。那是道,是佛,是永劫,是悟,還是淚,淚干又是笑,笑也會消失,得大歡喜。
關心自己的健康,希望長壽,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準備,準備安穩地去旅行。完成生命的全過程,走上新的期待與可能的道路。
池田大作:人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千差萬別的生老病死的情形。看看周圍,有人因疾病或事故等夭折,有人雖長壽但總是疾病纏身,有人衰老而安詳地死去。一生是充實的,即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感受到確實的幸福,還是被苦惱與煩悶糾纏著結束,人必須深思人生的過去。
日蓮大圣人一語道破:“見生死而厭離是云迷”,“知見本有之生死是云悟”。所謂“本有之生死”是說生、死都本然具備于永遠的生命中。
因此,在變化接著變化的諸行無常的現實社會,具有堅定的生死觀而生,或者說確立不動的自身,構筑牢固的幸福境界,我們為此天天堅持信仰實踐。
我從青春時代就喜愛的詩人惠特曼曾高歌:
“喜悅,(想著高興到靈魂深處,我吶喊)我們的生結束,我們的生開始。”
“要歌唱,以充滿歡喜、鼓漲活力的全體為目標,以‘死的意義為目標,與生一樣再接受‘死,人歡歡喜喜進入‘死。”
像以前說過的那樣,徹底凝視生命的詩人和作家的志向與佛法說的“生也歡喜”、“死也歡喜”的生死觀相通。
鼓舞人們提升到超越生死的歡喜境界,是文學與宗教的深刻的存在意義,是使命。
生命尊嚴具有無上的價值
池田大作:關于人生的價值,王蒙先生也這么說。
“人生一世,總有個追求,有個盼望,有個讓自己珍視,讓自己向往,讓自己護衛,愿意為之活一遭,乃至愿意為之獻身的東西,這就是價值了。”
把什么當作至高無上的價值,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觀,人的生活方式或人生的方向因之而大不相同。
在此我想再次提起“生命價值”這個主題。
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對談的最后一章里,我說過:“把最高價值置于生命尊嚴,這必須作為普遍的價值基準。”“生命是尊嚴的,不可能有在它之上的價值。”
博士回應:“正如您所言,生命的尊嚴才是普遍的、絕對的基準。”我們的看法完全一致。
博士和我對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話共鳴:
“有價格的東西都能被其他什么等價物置換,但與之相反,一切超越價格的東西,即無價的東西,所以又絕不容許等價物的東西,具有尊嚴。”
就是說,“生命的價值”就是不能換算成價格的、其他任何東西都不能替代的尊嚴。
尊重多樣的價值觀,同時其基礎上不能沒有“生命尊嚴”這一絕對的價值。
說生命絕對尊嚴的《法華經》在萬人生命中看出佛性。日蓮大圣人說明此重要法門,認為生命的價值比宇宙的一切財寶更可貴。
王蒙先生認為應該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擴大生命的價值呢?
王蒙:池田先生講得非常好。
中華傳統文化同樣尊重生命的尊嚴。“大德曰生”,“生生不息”,這些都見于《周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出自《尚書》。
孔子重視祭祀,重視喪事,這也當然是對于生命尊嚴的強調。“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是王羲之在《蘭亭集》中引用的古訓,中國從遙遠古昔就這么說。
生命尊嚴的問題并非不過是一個觀念,牽扯到很多具體事項,例如安樂死的問題,是疾病對生命尊嚴的嚴峻挑戰。這些該怎么辦?饑餓與貧困也剝奪生命的尊嚴。與饑餓、貧困的斗爭到達解決的目標還需要遙遠的路程。還有人本身發展的課題,接受教育、享受文化果實的權利。我們總稱為“人權”,這也是生命尊嚴不可或缺的。
為了生命的尊嚴,我們還有很多該做的事情,再苦也要繼續戰斗。必須有為了生命尊嚴該入地獄就入地獄的氣概。
池田大作:您的話令我感動。必須使21世紀成為“生命的世紀”、“生命尊嚴的時代”。醫學、文學、教育、宗教為此必須齊心合力。
政治、經濟、科學本來目的應在于此。把生命當作手段,當作犧牲,是本末倒置。
把超過生命的價值置于生命以外的東西,就必然還會成為戰爭、糾紛、暴力的元兇。
為起草《世界人權宣言》作出貢獻的巴西文學院阿塔伊德總裁對我說過:
“人的內心若沒有看圣物的視點,人的尊嚴這種思想就不能生根。從這一意義,我對佛法的觀點極有共鳴。”
我相信,指明誰都有尊極的佛生命的佛法思想必然有助于世界人權的確立,而且在現實上用以開啟人內在的智慧、力量與可能性。
關于人的賦權
池田大作:“人”本身,“生命”本身就是今后時代的焦點。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書不只是收入,而且公布了綜合測算各國豐富度的“人類發展指數”。
“人類發展報告”的指針是“人是國家之寶”這句話。
而且,“人類發展”的核心不就是“賦權”嗎?
人以及人所擁有的力量就是國寶,這種觀點讓人想起《史記》的故事——魏惠王把照很遠的徑寸之珠當作國寶,而齊威王把守護國家、支撐國家的優秀人才當作國寶。
基于這個故事,日本佛教家傳教大師最澄認為:“國寶為何物?寶乃道心。有道心之人,名為國寶。”進而舉出中國古人的格言“口能行之,身能言之,國寶也”。這是唐代佛教家妙樂大師也注目的話。
中國和日本的傳統文化中具有人文主義的思想潮流,把人的崇高生活方式或人所具有的偉大力量當作國家和社會的最大寶貝。
身邊的社區、社會也好,組織、團體也好,國家、世界也好,永續的繁榮即在于人本身的力量開發。
我對談過的羅馬俱樂部創始人佩切伊博士說:“人,每一個人身上都蘊藏著豐富的理解力、想像力和獨創力,而且還豐富地具備尚未被發揮、甚至為別顧及的道德資質。”
這里啟示了21世紀人類應行進的道路。人相信自己,引出自己的力量,加以發揮,為此而需要什么呢?這一點,應該讓文學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也請您談一談。
王蒙:人的能力需要培養、開發,同時也需要平臺。中國是人口大國,由于人口多,人們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平臺更為困難。
發展與開放大大有利于人的能力發揮。中國有個說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還記起以前說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對這類號召應抱有希望。
另一方面,發揮每個人的能力會推動全體的發展與尊嚴的實現。
我最感動的是人心中確實有的善良與愛心,關懷與同情。中國話里有“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的觀點,其實踐需要宗教與文學的啟發。
例如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米里哀神父對于冉阿讓的善待,無人不為之感動。冉阿讓偷了神父的東西,結果神父還保護他。我上小學時讀的,太震動了。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人呀,如果世界多幾個好人,那壞事也就沒了。我真是吃驚,這樣的好人世界上有嗎?
《論語》不是宗教的經典,但孔子的地位是準宗教的“圣人”,他總是相信人的善性,而且把對父母的孝行和愛護兄弟姊妹的心升華為忠、恕、仁、德的思想,也令人感動。
文學注意探討與表現善性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臺灣證嚴法師的慈善活動也非常好。
文學對人所具有的惡的可能性也傾注全力。同樣在《悲慘世界》里,警探沙威在恪盡職守的外衣下窮兇極惡也令人難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出現的那種絞肉機式的人際關系也富有教訓。中國文學中,把善惡、悲喜、正邪表現到極致的是《紅樓夢》。
現在,表現惡毒、殘虐的文學形成一個潮流。我也不怕寫惡,但不單是陳列夸大地表現惡,而是要為人、為人類探求出路。回到善與愛,回到同情與惻隱、尊嚴與幸福。我們應該敢于面對惡,進而跨越惡,喚起善。
池田大作:完全同意。
作為人的賦權的重要支柱,今后尤其應該更促進女性的賦權。
《法華經》是堪為女性賦權之先驅的思想。
已經談過了一點,《法華經》以前,各種思想或佛教經典也是對女性歧視不斷。
但是,《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說龍女成佛,指明所有女性達至幸福境界的道路。《法華經》是顯示男女都成佛的平等的教法,其中有堪稱女性人權宣言的思想。
日本平安時代紫式部《源氏物語》等女流文學興隆,其中濃重地反映了《法華經》思想、佛教思想。
譬如,與紫式部并稱的清少納言在《枕草子》里寫道:“(寶貴的)經典里,《法華經》那是不用說的了。”而且,花與實同時具備,寫到不染淤泥地開花的“蓮”包含在《妙法蓮華經》中,贊嘆:“蓮比其他任何草木都更美。”可見,清少納言的豐富感性也受到《法華經》熏陶。
翻閱同時代女歌人赤染衛門的和歌等也反映了佛教思想,如《法華經》所說的“不輕”,即絕不輕視有佛性的生命的生活方式,被認為這位歌人所作的《榮花物語》也表現了“佛”、“凈土”都在人心中的佛教思想。
這樣,很多女性也受《法華經》思想、佛教思想啟發,汲取智慧,創造文學。
基于《法華經》的哲理,日蓮大圣人鼓勵女弟子:“持此經之女人勝于一切女人,甚至勝于一切男子。”
這是教導,憑《法華經》信仰,女性發揮剛強而清純的生命之力,把濁世變成更好的社會的使命。
德國文豪歌德在《浮士德》的結尾處謳歌“永遠的女性/把我們引向高處”。
回顧以往的歷史,何其多的女性被戕害,生命的戰爭或暴力虐待啊。今后必須構筑使屬于女性的美好特質的撫育生命的愛情、企求和平的心、對他人的關懷以及開朗等充分發揮的社會。
那也可說是女性幸福起來、大顯身手的“女性世紀”。
我們以《法華經》的生命尊嚴哲學為根干的和平、文化、教育運動在世界各地生氣勃勃發揮領導作用的也是女性。
王蒙:中國大陸也說慣了男女平等,那是一種婦女半邊天的觀點。
雖說男女平等,但不是說男性和女性應該完全一樣。軍隊和警察里女性也有,但畢竟男性多。男性有男性的特征,女性有女性的特征。所以池田先生說的十分重要,特別令我感動。
畢竟男權社會有著太長的歷史與覆蓋面,現在,仍然有明顯地歧視女性的地方,至于心目中的歧視女性的想法說法更是無處不有。看看一個人物一個VIP對女性的態度,包括一個寫作人或者一個社會活動家對女性的態度,我覺得就看到了他的內心,他的靈魂。歧視女性,這就是腐朽、自私、齷齪、低級趣味的表現。
池田大作:全球化,在所有層面人員來往都很活躍,女性所具有的聯結人、圓滿推進人際關系的交流能力令人矚目。
在這一點上,我想起了經常交談的作家有吉佐和子先生,她開朗、和藹可親、勇敢的性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位在日中友好的黎明時代也和周恩來總理等中國領導人交流的女性。
有吉有一部小說以17世紀的出云阿國為主人公,這個女性傳說是歌舞伎的創始人。
小說里高聲宣揚音樂舞蹈在人的心里喚醒的快樂與喜悅。
另一方面,描述勤勤懇懇的農業勞動,即播種、育苗、收獲果實以支撐人命的可貴。而且,發現農業勞動的動作節奏和歌唱的民謠中有精彩的音樂舞蹈。
在農村、漁村,在城市,女性扎根在當地活動,支撐大家。照亮這樣的女性背后的辛苦,贊頌其偉大,我認為也是文學藝術的溫馨目光。
可以說,女性是生命的守護人、文化的創造者。
完成了日本俳諧文學的是江戶時代,那個時代產生了很多女俳人,留下了優秀作品。也有不少女俳人年輕時死去丈夫,日常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心情寄托于俳句,使之升華。其一是加賀千代女,她吟詠:
“什么是財寶/今日燦爛生命啊/櫻花初綻開”。
可見對越過嚴冬終于開花的櫻花生命的深深共鳴。
只有養育生命的女性才具有的敏銳感性若得到發揮,生命文化、和平文化不就更扎根于社會嗎?
王蒙:太好了。有吉佐和子是我最喜愛的日本女作家之一。這也是緣份啊,您在這里提到了有吉佐和子!